|
(七)人道救助呼吁书与人权呼吁书
自93年下半年以来,丁与难友们的寻访、救助活动逐渐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丁提供有关“六四”受难者的线索,这对当时的寻访活动的迅速扩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94年1月21日,丁以个人名义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了《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中,丁回顾了这些年来寻访活动的历程,介绍了当时“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基本情况。据统计,截止当年1月已寻访到死难者亲属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约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人(户)。在60多家遇难亲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老人者27户,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另有3户有病困老人,一户为特困户。在伤残者40多人中,重残者25人,其中7人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5人仍在治疗中。
在这份呼吁书中,丁作了如下声明:“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均属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同时声明,“在目前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的情况下,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救援事宜,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亲属及伤残者。”
上述呼吁书公布后,得到了海外人士的广泛响应。除了全美学自联II
FC按计划转来捐款外,94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以及圣·路易斯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等学校通过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转来了“六四”后募集的捐款,丁与张先玲女士把这些捐款按捐款方定下的标准,分送给了一些有困难的死难亲属和伤残者,每户200、400美圆不等。此外,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大赦国际、法国的玛丽·侯芷明,美国的STING夫人,英、德、法、日、澳、加、泰等国的留学生组织和一些个人,以及港、台地区的一些个人也都转来了数量不等的人道救助捐款。由此,用于对“六四”难属人道救助的款项得到了基本的保证。
自93年中国政府因申奥需要相继释放王丹、徐文立、魏京生之后,国内政治气氛一度有所放松。这年秋冬之交,秦永敏、周国强、刘念春等一批异议人士发表《和平宪章》,但是,尽管《和平宪章》的基调极其温和,却仍然遭到政府当局的严厉打压。一时间,国内政治气氛骤然收紧,北京、上海及一些省区的民间人士相继因思想、言论遭到当局拘捕或拘询,尤其是刚释放不久的魏京生再度失去了自由。
鉴于国内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丁蒋与许良英先生一起提议发表一封致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信,呼吁政府当局停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经商议,决定由许先生负责公开信的起草,并分头征集签名。3月11日,一封由许先生牵头,有刘辽、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以及诗人邵燕祥、作家张抗抗等七人联署的、题为《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公开信在海外媒体正式发表。
这份公开信指出:“最近发生的多起因思想言论而遭到当局拘捕、拘询的事件,使国际舆论哗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有志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并深感不安和忧虑。”
公开信同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并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理应率先恪守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而不应因国内的人权侵犯记录而成为国际舆论谴责的对象。”
公开信表示:“只有尊重人权,确保公民各项应有的权利,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否则,只会激化矛盾,诱发动乱,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公开信最后呼吁当局果敢地结束我国几千年来因思想、言论、文字治罪的历史,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而被关押的人员。
这是自“六四”事件以来第一次由国内知识界人士联署的人权呼吁书,也是丁蒋以“六四”死难亲属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加入国内人权运动的开始。这封公开信发表后,有海外媒体称之为“七君子”上书,但也有人批评此举为“挟洋自重”。
(八)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由于此次上书,丁蒋和许良英先生都受到了政府当局的打压和监控。3月10日,在丁蒋的住所(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周围出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警察和监视车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6日,丁蒋受到便衣警察的24小时全天候监控,遂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完全被隔绝。这是丁蒋自91年5月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以来第一次被剥夺人身自由。
同日下午,台湾《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先生、大赦国际工作人员史雯女士(瑞典)先后来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下午2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人民大学的治保人员以及家属委员会的“小脚侦缉队”约20余人,突然包围了丁蒋的住宅。下午3点半,他们的住宅电话被切断,失去了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当日下午四点,便衣警察强行绑架了刚离开丁蒋家的台湾《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先生,审讯达三小时。随后离开丁蒋家的大赦国际史雯女士同样遭到便衣警察的扣押、审问。
这天夜半,丁心脏病发作,因电话被切断无法向校医呼救,仅靠吸氧缓解。
此后几天,便衣警察始终未曾间断对丁蒋的监视,甚至在校园里当众辱骂丁蒋为“汉奸”、“卖国贼”。与此同时,在丁蒋家门口频繁地发生绑架、扣押、盘问来访者的事件。
为此,丁蒋多次通过人民大学校方向国家安全部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便衣警察的监视、骚扰和辱骂;要求恢复被切断的住宅电话;要求不受干扰地去校外医院治病(此前丁定期去医院治腰椎病);要求停止对来访者的绑架、扣押、盘问……。然而有关方面对丁蒋的抗议始终置之不理。
94年是“六四”惨案五周年。这一年,是中共执政当局在对待丁蒋的态度和政策方面作出根本性改变的一年。在这之前,执政当局对丁蒋的打压和惩处,一般通过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行政系统来实施;而在这之后,则改为由国家“专政机器”——国家安全部门直接实施。
3月26日上午8点30分至下午4点30分,美籍自由制片人卡玛(中文名韩倞[Liang],韩的父亲为中共老朋友、美国农业专家韩丁)与其丈夫、自由摄影师高富贵(中文名)以及录音师等一行五人由江棋生陪同来丁蒋家里拍摄电影《天安门》(当时未定名)。
在这次拍摄中,丁谈了“六四”五年后的心情、感想,回顾了五年来走过的路程:从儿子的遇难谈到自己最初的抗争;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注谈到对“六四”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寻访、救助……。其间,丁以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为实例,讲述了五年来死难亲属所遭受的痛苦与煎熬。这是丁五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系统、完整地披露“六四”受难者群体的详细情况。
这次拍摄行动引起了北京市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摄影师高富贵以及陪同他离开人民大学的江棋生遭到了便衣警察的长时间跟踪,追逐,险遭拘捕。
在此期间,丁还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CNN)、美国华盛顿邮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媒体的电视录像采访,内容除了谈及“六四”后个人的经历、遭遇,还谈及几年来所从事的寻访和救助活动。
3月29日,丁收到美国纽约一家公司销售经理的来信。信上说他从纽约一份中文报纸上读到了有关丁子霖教授对“六四”难属和伤残者从事救援活动的报道,他愿意把有关情况介绍给美国的民众,让大家来帮助这些受难者,只要不涉及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条件允许,他本人愿意认养一个儿童(遗孤),尽他自己的一份心愿。后经多次联系,商定由死难者刘燕生的女儿作为认养对象。
此项个案援助计划自94年开始后持续了很多年,使受援者得以顺利地读完小学、中学并考上大学。
尽管自3月以来,丁蒋不断受到便衣警察的监控,给他们所从事的寻访救助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这项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间隙,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带来新的发现的线索,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与每一位确知其下落的死难亲属和伤残者取得联系。有时,丁因受监控而无法出门,就由张先玲女士等其他难友分担寻访工作。
这一年是国家安全部门对丁蒋实行严密监控的一年,但也是他们与难友们的寻访活动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
自这一年年初以来,人大哲学系博士生江棋生曾协助丁做了一些寻访和救助方面的事情,由此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4月5日上午9点,江棋生在本市建国门立交桥外交公寓附近遭到国安部门的便衣警察的无端殴打,并辱骂他为“汉奸”。
为此,江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公安方面对他所施之的暴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公安方面却始终不予理睬。
这年4、5月间,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否继续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美国朝野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海内外中国异议人士也就此事纷纷敦促克林顿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此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来华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政府磋商时,其助手夏塔克曾与魏京生有过接触。
5月27日,“美联社”就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丁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丁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尊重美国总统的决定。但是,“人权”具有普遍性,它是世界大家庭范围的事情,美国政府作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其他国家、推动其他国家改善人权状况,正如中国这个有着12
亿人口的大国,也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如果将来中国的人权状况真正得到了全面、普遍的改善,那么它也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帮助世界上人权状况不好的其他地区或国家,推动改善他们国家的人权状况。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对任何来自国际社会的对于我国人权状况的关注,都表示欢迎。”
在这次采访中,丁列举并谴责了最近时期中国有关当局粗暴践踏人权的一系列恶劣记录,同时批评了克林顿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姑息态度。基于当时的情况,丁对克林顿总统决定“无条件”延长的做法表示遗憾,她说:“如果问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的耻辱,历史将证明克林顿是错误的。”
这次采访在海外媒体广播后,丁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刘亚平”的天津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在信中辱骂丁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卖国求荣的现代汉奸”等等。为此,丁专门写信给这位大学生就他的一些观点、看法进行了讨论。丁指出:“来信对我在采访中谴责政府当局的“六四”屠杀事件和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暴行不置一词,而竟以所谓‘爱国者’自居,站在杀戮者的立场,肆意辱骂与之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如果这也算‘爱国’,也算‘中国人的良知’,那么,就让这样的‘爱国’,这样的‘良知’见鬼去吧!”
丁的这封回信按来信的邮编、地址及姓名寄出几天后却被退了回来,回条上写着“经查无此地址”,原来是一封署了假名的匿名信。
此后几天,丁蒋又多次接到内容类似的匿名骚扰电话,据称他(她)们都是“爱国”的大学生。
5月28日晚,江棋生来人大看望丁蒋。当他离开丁蒋家后却遭到公安人员的跟踪、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遭到无理关押,历时45天。
5月29日,丁蒋在忍无可忍之下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抗议3月以来国安部“便衣警察”对他们的监视、骚扰甚至辱骂和威胁。
公开信表示:“在我们儿子的生日和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把我们住宅周围的便衣警察和监视车辆撤走,恢复我们的人身自由。”
公开信指出:“我们谴责89‘六四’政府对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我们为在那场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人们作名誉辩护,这是履行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以一己之绵薄,寻访‘六四’受害者及其亲属,旨在互助互慰,呼吁人道救助。对于这个受害群体的痛苦和困难,政府不管,难道也不让我们同命运者自己来管!我们多次声明,对受难者的援助纯属人道性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难道为‘六四’受难亲属接受并转达此项援助就成了‘汉奸’、‘卖国’!”
最后,公开信重申:“政府当局应立即停止对我们住宅的监视和骚扰,立即恢复我们的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从6月2日儿子出生的时刻开始至6月4日,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绝食抗议,以告慰亡灵于九泉。”
这是五年来丁蒋以个人名义第一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九)“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6月1日,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出版、发行了一本书名为《“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名单》的英文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由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管理的一个基金会提供经费和部分资料。小册子刊登有丁的《“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的“序言”、96位“六四”死难者和49位伤残者的名单,以及丁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书》。小册子同时还配发了有关照片。最后,小册子呼吁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捐助,并作如下声明:鉴于丁在国内受到严密监控,该法国基金会表示愿意代为收转海外人道捐款。
同日,纽约《世界日报》刊登丁《“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一个“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并不想给已经过于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涂抹上些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咀巴,我却不能。
“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擦乾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
从同一天起,《世界日报》开始连载《寻访实录》,每日一篇,共10篇。另,香港《联合报》刊登了另外的10篇。《寻访实录》发表后,受到海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专题播出了其中5篇,美国和香港许多报刊发表了评论。
6月2日,纽约《世界日报》又刊登了蒋撰写的“六四”五周年感言:《不能让受害者再一次被杀害》。该文详细叙述了他这五年来的心路历程。在文章的开头蒋写道:“这五年来,我终于有了自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该文告诫所有的同胞:“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但愿饱经忧患和苦难的中国人能记住这一点。”这是
“六四”后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
6月2日,丁蒋为亡儿过22岁生日;3日,为亡儿做罹难五周年祭奠。丁蒋按29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所作之承诺,于6月2日晨6点25分儿子出生的时刻开始至4日晚在自己家里进行了为时48小时绝食抗议。
这次绝食抗争,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声援。
晚8时半,时任全美学自联主席的林长胜先生来电告知丁蒋,他与其他5位人士于5月20日至6月4日在华盛顿白宫外面举行绝食抗议。林于6月1日在绝食现场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丁蒋表示声援,并在给丁电话里念了信的全文。
6月3日,丁蒋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伙北京人”的恐吓信,信中辱骂丁蒋为“汉奸”、“卖国贼”,说他们儿子的死是受父母指使的结果,因此是活该。该匿名信还声称:“共产党对你们实在太仁慈了,要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时代,你们早没有命了!”
6月5日,据《美国之音》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六四”前夕发表声明,向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献出了生命的人致敬。
晚8点,五个旅美华人组织于华盛顿时间6月4日下午两点钟,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六四”事件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钱卫作了现场报导。全美学自联主席林长胜先生在发言中说:“五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专制统治,在国内,他们变本加厉逮捕了大量的民运人士和不同政见者,同时他们对很多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骚扰。两天前我曾经给丁子霖女士打过一个电话,她于两天前进行了绝食,来抗议中共当局对他们的骚扰,侵犯他们夫妇俩的人身自由,第二天中共就把他们的电话切断,我们失去了联系。”
6月25日,瑞典“六四”联合会授予丁子霖人权奖。
6月28日,丁蒋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在信中说:“我是一名大学生,曾经是。虽然我未能拜师门下,但我听到过你们,知道你们及有关你们的……
“我是在这个制度下出生的,并且受它的教育而成长。我隐约觉得,这种教育使我和我的同龄人中的大多数无法追求、表达真正的自我。
“我想说什么?我内在化了的恐惧使我不能说:丁先生,你真苦啊!蒋先生,你终于清醒了!我知道,真正使你们痛苦的是无数人的、像麦田(里的麦苗)一样多的人们的沉默!民族已处于失语状态,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人们的自由和同情、人性和人情已从内心被驱除了。”
这封信摘录了北岛的以下诗句: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弥补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的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充满血泪而不展现欢容
最后他写道:“这个世界上,也许谁也没有错,谁也不该受到责难。也许,这是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已注定的劫难。让逝去的永远安息吧!如果那外在者、那全能者果然存在,我只想和你们一同祷告:请给我们能使我们有尊严地存在着的自由的祖国吧!”
7月23日,“六四”伤残者方政去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方这次从海南来京,原为代表海南省残疾人参赛团参加体育集训,以为9月4日将在北京举行的“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作准备。但方来京后被告知,他参加的项目已被取消,让他返回海南,而真实原因则是中国的体育官员发觉了方的“六四”伤残者身份,他被剥夺了参赛的资格。这天下午5点,方由吴蓓女士陪同来到丁蒋家里,晚饭后9点离开。丁蒋送方出校门时,方的轮椅周围聚集着一大群“便衣警察”,可谓戒备森严;至学校东大门,更是岗哨林立,警察随便驱散路人,直至方政登车离去。三天后方政被遣送回海南他谋生的地方。
 在“远南”运动会开幕前夕(9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先生约见丁蒋。邰向丁详细询问了有关方政的情况,丁把此前所写《“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中有关方政的一篇(其中写到取消方政参赛一事)给了邰,另外给了一张丁与方政的合影。第二天,邰飞往海南采访了方政。9月8日,《纽约时报》〉以整版篇幅对方政在“六四”事件中的遭遇、“六四”后的生活以及此次被取消“远南”运动会参赛资格等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在“远南”运动会开幕前夕(9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先生约见丁蒋。邰向丁详细询问了有关方政的情况,丁把此前所写《“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中有关方政的一篇(其中写到取消方政参赛一事)给了邰,另外给了一张丁与方政的合影。第二天,邰飞往海南采访了方政。9月8日,《纽约时报》〉以整版篇幅对方政在“六四”事件中的遭遇、“六四”后的生活以及此次被取消“远南”运动会参赛资格等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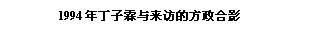 7月28日,丁收到日本89岁退休老人吉田美和子女士委托《读卖新闻》驻华记者转来的一封信。信件的大意为:前几天,读了《读卖新闻》有关您寻找“六四”受难亲属并给予人道帮助的报道,非常感动,想尽一点微力。花了很多天,才与《读卖新闻》报社联系上。今天,我委托分社的人,希望他们将东西直接送到您处,只是一点点金额。这是我及老伴的养老金中的积蓄。希望这些钱能对遇难家庭派上用场。 7月28日,丁收到日本89岁退休老人吉田美和子女士委托《读卖新闻》驻华记者转来的一封信。信件的大意为:前几天,读了《读卖新闻》有关您寻找“六四”受难亲属并给予人道帮助的报道,非常感动,想尽一点微力。花了很多天,才与《读卖新闻》报社联系上。今天,我委托分社的人,希望他们将东西直接送到您处,只是一点点金额。这是我及老伴的养老金中的积蓄。希望这些钱能对遇难家庭派上用场。
吉田美和子女士捐款20万日圆,丁和张先玲女士赶在当年中秋节前把这笔捐款分转给了一些最困难的死难亲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