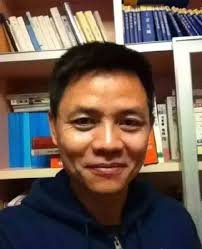 自由微信:张雪忠 | 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
自由微信:张雪忠 | 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张雪忠说:“国⺠性之类的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所进⾏的所谓国⺠性批判,都是知识不⾜的产物,是因为有些⼈尚未掌握必要的⽅法和知识,就试图去解释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
张雪忠的这段话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国民性这个概念是知识不足的产物,如果知识足够就不会有这个产物,也就是说,国民性是杜撰出来的伪概念;第二个意思是,国民性批判也是知识不足的产物,这个意思由于张雪忠表达得不够清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国民性批判也是伪概念,不存在的;另一种理解是,国民性批判不是伪概念,但有些人的国民性批判是知识不足产生的。张雪忠后面说“国⺠性批判的根本缺陷,在于逻辑和⽅法上的错误”,那意思就是说,如果逻辑和方法没有错误,那么国民性批判就没有缺陷,那也就是说,国民性批判是可以有的,只要逻辑和方法没有错误就行了。既然国民性批判是可以有的,那么国民性也是存在的,如果国民性不存在,又哪来国民性批判呢?这就与其前面说的“国⺠性之类的概念……是知识不⾜的产物”,是“伪概念”相矛盾了。由此看出张雪忠的逻辑是混乱的。
那么,国民性这个事物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再来看看张雪忠的这段话:
“鲁迅观察和描述的现象,其实是⼈们在权⼒关系中的不同⾏为模式(这些权⼒关系既可能是制度性的,也可能是事实性的):强者专横跋扈;弱者卑怯顺从。在⼈际交往中,如果⼀⽅掌握着可以宰制对⽅命运和福利的专断权⼒,就会表现得傲慢骄横,相对的⼀⽅则会表现得卑贱软弱,这显然是⼈类社会普遍的,⽽不是中国⼈特有的⾏为模式。从托克维尔等⼈对⼤⾰命之前法国社会的描述来看,在专制皇权和等级制度下的法国⼈,有权势者的骄横和⽆权势者的卑怯,与鲁迅等⼈笔下的中国⼈可以说毫⽆⼆致。这⼀点在别的国家也并⽆不同。”
从上面这段话来看,张雪忠是承认中国人确实存在鲁迅所描述的那些品性的,只不过他认为那些品性是在特定权力关系下的表现,也并非中国人独有。即便那是在特定权力关系下的表现,即便那并非中国人独有,总之中国人当前是有那样一种品性。既然中国人当前有那样一种品性,为什么不能把它称为国民性呢?非得要是独有的才能叫国民性吗?难道当我们要把中国人的某种品性称为国民性的时候,先要到全世界看看其他国家有没有这种品性?这不是扯蛋吗?如果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也有这种品性,它就不能称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那该叫什么呢?不管它叫什么,都会有人去揭示它、批判它。
鲁迅以及很多人把鲁迅笔下描述的那些品性说成是中国人独有的,这只是他们对其他国家没有了解而已。你可以说“中国人独有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那些品性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独不独有都不妨碍把那些品性称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果别的国家也有这种现象,那么也可以把它称为那个国家的国民性,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性是一样的,这有什么问题呢?难不成国民性还成了一种专利了?
由此可见,国民性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杜撰出来的伪概念。
既然中国人有那么一种品性,并且是不好的,那为什么不能批判呢?
诚然,有些人批判国民性是如张雪忠所说的“去解释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但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事实上很多人批判国民性就只是纯粹的批判,并没有“试图去解释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只揭露现实,让人们去思考。艺术作品如果在揭示现实的基础上去追究原因、得出结论,那是画蛇添足,限制了读者、观赏者的思维,也会出现偏颇,从而有损于作品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在言论不自由的社会里,如果把国民性与制度联系起来,会遭到统治者的打压,所以艺术家们往往都只能是止步于揭露现实,而揭露现实本身往往就是一种批判。所以,启蒙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播真相。当然,揭露现实这种批判通常还是需要通过一些情绪的表达、渲染等手法来体现。也有些揭露现实并不是批判,例如那些美化苦难、鼓励人们安于苦难的揭露现实就是别有用心的。
对社会现象的揭示如果得到很多人的认同,那么它就是真实的。但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推理式的批判则不一定是对的,不同的人的看法可能是不一样的。对的你就说它是对的,错的你就说它是错的,这是可以讨论、辩论的,辩论有利于探明真理。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整体否定国民性批判这个东西,那就不对了。
张雪忠说:“鲁迅的最⼤错误,是他对上述现象所进⾏的解释,即将它们归咎于中国⼈特有的诸如‘奴性’、‘专制性’之类的所谓国⺠性。这其实是毫⽆意义的循环解释。”
这怎么是循环解释呢?什么叫循环?由A到B再由B到A这就叫循环。循环解释就是用A来解释B,然后又用B来解释A。鲁迅的解释显然不是这样的循环,那明明是一种归纳总结嘛。先列举各种现象,然后进行归纳,作出总结,最后再进一步探究其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科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套路。当然,鲁迅是止步于归纳总结了,并没有再进一步探究更深层的原因,你可以说他认识得不够彻底、研究工作做得不够系统化,但你不能说他的归纳总结是循环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循环解释,张雪忠后面又举了科学研究上的例子,说“亚⾥⼠多德就曾认为,有些物体之所以会往地上掉,是因为它们具有⼀种叫作“重性”的属性,另⼀些物体之所以会往天上飘,是因为它们具有⼀种叫作“轻性”的属性。”亚里士多德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一种归纳总结啊,这有什么循环的?事实上,“轻”、“重”的概念就是由此而产生的。难道“轻”、“重”的概念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吗?当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搞清楚“轻”、“重”的更深层的原因,这是他认识的局限,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能够作出这种归纳总结就已经很不错了,正因为有了他的这种归纳总结,后人才在此基础上对“重性”、“轻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是质量、比重的原因,再后来搞清楚是分子、原子内部结构、微粒子的构成的原因。这就是认识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怎么能说亚里士多德“对物理学的发展产⽣过极⼤的阻碍作⽤”呢?
张雪忠说“奴颜和专制本来都是描述性的词语,⽤来形容权⼒关系中强者和弱者的不同⾏为模式,鲁迅等⼈却将这些形容词加以名词化,并⽤来指称他们眼⾥的中国⼈特有的属性。在这些⼈看来,中国⼈之所以奴颜婢膝,是因为他们有⼀种叫作‘奴性’的属性,⽽中国⼈之所以⼜专横跋扈,则是因为他们还有⼀种叫作‘专制性’的属性。”
把形容词名词化这个有问题吗?这是语文、文学中的一个基本手法吔。当然,有些形容词的名词化是不恰当的,但你不能笼统地否定“形容词名词化”这种做法,不能把“形容词名词化”一概视为一种错误。再说,“奴颜”原本也并不是形容词啊,它的词性跟“笑脸”这个词一样,“笑脸”是形容词吗?实际上,奴颜婢膝恰恰是一个名词形容词化的成语。真不知道你的语文是怎么学的。
国民性就是对国民现象的一种总结,一般是指不好的现象。“奴颜婢膝”、“专横跋扈”这些都是国民较为普遍的现象,把这些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奴性”、“专制性”这些属性并称之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有什么问题?这就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步骤、方法,看来你是不懂这个。
当然,事物的原因可能是多层次的,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你可以说鲁迅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没能揭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根本原因,但你不能否认中国人确实有那些属性,更不能说不能对那些属性进行批判。
张雪忠把柏杨的比喻手法也说成是循环解释,更是乱用概念了,比喻怎么是循环解释呢?张雪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循环,硬生生地把“循环解释”的概念套在鲁迅和柏杨的头上,根本就说不通。
张雪忠说:“柏杨把中国传统⽂化⽐作⼀个‘酱缸’,⽽中国⼈之所以会有他所厌恶的种种⾏为习惯,则是受到了这个酱缸的污染”,他认为这是不对的。
张雪忠的这个看法倒也不是错的,但是对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批判中国人品性的书和文章,如果仅仅只是抱着这样的观点看待,那就是肤浅的、狭隘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受到了专制制度的巨大影响,已经沦为了专制制度的帮凶。作为个人,既受到专制制度的压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两方面的影响都有,有的人受专制制度的影响大一些,有的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大一些。专制制度的影响具有不可避免、不可抗拒性,而传统文化的影响则是可以避免、抗拒的,只要明白了它的危害,想做就可以做到,例如不让孩子上官办学校就是一种避免、抗拒,不看官办电视尤其是新闻联播也是。当然,传统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完全避免、抗拒是不可能的。说传统文化是个大酱缸,个人的品性完全是由其造成的,这固然是偏颇的,但是,柏杨这种夸大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做法无非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让人们明白传统文化的危害性,从而去避免、抗拒其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作品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他并没有明确否定专制制度的影响,更没有说专制制度是好的。你可以说他没有揭示、批判专制制度的危害,有不足之处,你也可以另外写一本书去专门揭示、批判专制制度的危害,但是不应该完全否定柏杨的作品及其“酱缸”说。
从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危害性再到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性,这个转变很容易实现,很多时候是一句话就点醒了。所以先让人们认识传统文化的危害性不仅没有坏处,甚至可能效果更好。而认识到了专制制度的危害性的人,不一定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危害性,或者认识得很不够,要他再去认识传统文化的危害性,相对麻烦一些,甚至不一定能做到。很多反专制的人并不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好的,应该继承发扬。当然,多数反专制人士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既有糟粕也有精华,但有的认为糟粕多于精华,有的认为精华多于糟粕,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怎么看那是个人的事,不管怎么样,柏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有其价值、意义的。
对于龙应台,张雪忠认为“《中国⼈,你为什么不⽣⽓》⼀⽂,最能体现所谓国⺠性批判对公共讨论的毒害: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中所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当时国⺠党威权政治的恶果:由于政府缺乏可问责性,⺠众的诉求⽆法得到及时的回应,⺠众的权益⽆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应台不将她批判的⽭头指向威权政治,反⽽指向被剥夺了政治和公⺠权利的台湾⺠众。”
张雪忠的这段话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其实也是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首先,龙应台并不是“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而是认为,各种政府治理危机的解决需要民众的呼声,如果民众不生气,没有态度,不发出声音,政府就不会重视,不会理睬,光是几个文人的批判有个屁用啊。事实上龙应台对政府、制度可没少批判,只是在这篇文章中她的着重点是放在呼吁民众上。龙应台认为中国人应该生气,为什么要生气呢?就是因为政府做得不好呗。可是很多中国人面对政府做得不好的情况却不敢发声、不愿发声,所以问题就常常得不到解决。只有民众起来了,表现出对政府不满意的态度,对政府施加压力,问题才可能会得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当然是在政府那边,但是解决问题不能指望政府自动解决或听了几个文人的批判就会解决,解决问题的源动力在老百姓这边。老百姓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即便龙应台所列举的事例是个人的事情,当事人也应该勇敢地表现出其对政府不满意的态度,积极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争取个人的权利就是争取大家的权利。你为自己的事情表现出了对政府不满意的态度,必然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声援,因为这样的事情既然会发生在你身上,就肯定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所以,龙应台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鼓动大家都要发声、敢于表明态度。由于她所列举的那些事例具有典型性、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所以能引起很大共鸣、得到广泛认可,她因该文章获奖那是理所当然的。难不成那么多读者包括那些评奖的专家都是傻瓜?加起来都抵不上你张雪忠一个人?
张雪忠对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的批判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认为他们应该批判政府、制度,而不应该批判老百姓即所谓国民性。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只不过张雪忠的一些看似新鲜的(其实是错误的)说法让一些人觉得很新鲜。
制度不好、政府做得不好当然应该批判,但并非国民性就不能批判、不应该批判。对政府、制度的批判和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两者不是相悖的,它们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相互配合。当你批判政府、制度的时候,除了说理,还得要有具体事实吧?具体事实有哪些呢?除了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没保障等等,也包括社会风气不好、国民素质低、品性恶劣,而且这些更能反映出政府、制度的恶劣,这也就是说,批判国民性本身也是在为批判政府、制度提供佐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政府、制度的坏。大家都不批判国民性,就都不知道国民素质如何低、品性怎样恶劣,对政府、制度的坏也就了解得不够深刻、具体。所以,国民性批判是需要的。
国民性与民族劣根性不是一回事,所谓民族劣根性,是指一个民族由基因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劣质;国民性则只是指当前国民的一些不好的品性,当然它可能是具有较长的历史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批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改变,如果不可改变,那还批判它干嘛呢?所以,我不赞同民族的劣根性这种说法。
就某个人来说,或就某一篇文章、某一本书来说,对于政府、制度与国民性,只批判其中一个,这一点问题都没有,都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为什么要对一个人、一篇文章、一本书求全责备呢?他或它能发挥一点点对社会进步有益的作用就是好的。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当然最好是既有人批判政府、制度,也有人批判国民性。如果你发现没有人批判政府、制度,或者觉得批判得不够,那么你就去批判好了,补上这一空缺,你肯定会得到大家的赞赏,你干嘛要去指责别人没有批判政府、制度呢?打横炮很过瘾吗?很安全吧?这样就能显得你比别人高一筹?我看这就是国民性中的一种表现。
张雪忠把热衷于国民性批判的人都视为是素质论者,这是不恰当的。
所谓素质论,就是认为只有提高民众素质才能使得社会进步,在民众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实行民主是行不通的。孔子就是素质论的鼻祖,老是要人们做君子、教人们如何做君子。素质论者没能认识到恶劣的制度是造就大量低素质人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压制了人们素质的提高。制度不改变,国民整体素质很难提高。
恶劣的制度造就低素质的国民,低素质国民则维护、复制那种恶劣的制度,恶劣的制度又继续造就、固化低素质国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与素质论对应的是制度论,即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制度改变了后国民素质自然就会提高。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都是反对启蒙的。这种观点其实是有点简单化、理想化。
如果你承认国民素质低是有利于维护恶劣制度的(这就是专制统治者要造就低素质国民的原因),那么反过来就应该承认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反推。
要打破恶劣制度与国民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关键是要改变制度,但不能一味地只想着改变制度而不去做提高国民素质的工作。国民素质提高一些,或者说素质高的国民多一些,制度转型成功的概率也就高一些。
中国几千年来无数次的推翻旧王朝,都没能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这当然就是所有人的素质都低的原因。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本来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的,但却失败了,没能成功转型,这不能说跟当时国民素质普遍较低没有关系。当然,到底要有多高的国民素质,或者说到底要有多少高素质的人,才能确保制度转型成功,这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更多高素质的公民总归是对社会进步、对制度转型有利的。既然是有利的,为什么不去做呢?你自己不做倒也无妨,但不应该反对别人去做嘛。尽管很多时候启蒙工作的收效不大,也不能气馁、完全放弃,大不了换个对象。
这里说的提高国民素质,主要是指三观、个人品性。
张雪忠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难道不就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素质吗?只可惜由于其认识的不足,适得其反。
一个不能反省的民族是不可能进步的,否定国民性和国民性批判,就是拒绝反省。
2023.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