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7月4日,宣告北美洲十三块英属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宣言》(The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由第二次大陆会议(SecondContinentalCongress)于费城批准。这个由著名的自然神论者杰斐逊(ThomasJefferson起草而经更多建国者(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认可并公布于世的“宣言”的序言,这样宣称: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段话第一句,还原成英文就是,“Weholdthesetruthstobeself-evident,thatallmenarecreatedequal,thattheyareendowedbytheirCreatorwithcertainunalienablerights,thatamongthesearelife,libertyandthepursuitofhappiness”。其中的“allmenarecreatedequal”,在中文世界,长期以来被错误地翻译为“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受造而平等,美国立宪价值观的基础共识
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根据祂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每个人与上帝都有直接的关系。在上帝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中介,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被造物,可以作为这样的中介。因为所有一切无不在上帝的主权下,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让人类屈膝,可以宣称以另外的依据统治我们。正是上帝,赋予了人不折不扣必须被尊重的权利,并且让人有机会认识到这一点。正如加尔文所说,“人总是全然败坏的、自以为公义和圣洁的;除非谦卑地仰望神的面,否则人不可能认识自己”。因此,allmenarecreatedequal理应合乎其原文式地被翻译成“人人受造而平等”。
人人平等,几乎是近代最响亮的口号。但口号背后,却依托着不同的根基。
一种把人的平等建立在人自身的伟大之上,认为人的意志高于万物,这是自然的法则。正如法国大革命所宣言的,既然人的意志是最高的主宰,人的意志就可以汇合,于是数人头就成为政治中的最高原则。同时,既然人的权利,只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也就意味着这权利是可以被转让的,人可以“自由”地把自己卖为一个奴隶。
所以,必要时把个人的权利,打包转让给国家或最高领袖,也是自然的事了。以至于那些打着社会契约幌子的共和,最终也无非是把个人的权利,转交给一个或一群人罢了。
另一种平等,则把以上帝主权、基督十字架救恩为根基。人与人的一切差异,都伏在其下,都不再是人间不平等的根据了。从进化论不可能引申出政治哲学上的平等,只有从创世论才能引申出人间的平等和真正的平等。
既然所有人都由上帝创造,那么我之为人的依据,就不在地上。我之为人的权利,就不是私有财产,不是私相授受的,当然也不是任何人或组织所能剥夺的。同时,也是不可转让出售的。既然我的灵魂,直接向上帝负责,那么任何其他人,就都没有支配我思想的权利。
---------------------------------------------------------------------------------------------------------------------------

人人受造平等而立法的典范是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
英国玛丽一世(Mary I)1553年即位后,因残酷迫害宗教改革家,烧死新教徒达300多人,而获得了“血腥玛丽”的称谓。1603年,詹姆斯一世掀起了对清教徒的又一轮迫害。于是1620年9月,搭乘“五月花号”的100位清教徒在即将豋陆北美新大陆船上订立了《五月花号公约》。条约签订时,全船一共有乘客102名,其中分离派教徒35名,其余为工匠、渔民、贫苦农民及14名契约奴,带领者为牧师布莱斯特。公约载明他们愿意在新大陆建立小区,服从其中的法律: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信仰和我们祖国与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于右。
链接:纪录片《我们:美国的故事》(12集,美国,2010年)
---------------------------------------------------------------------------------------------------------------------------
由此可见,当我们谈论权利,谈论平等自由时,请不要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以及基督十字架的舍己之爱。罪破坏了我们的良善,使这个世界全然败坏。一个诚实的人,会承认他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无时无刻不在罪的诱惑中,无时无刻不在贪图着他人财产、身体、妻子、房屋、名声和一切。
因为“罪”,政府权力当时刻被警醒而受限
由于罪,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混乱的,就如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无法继续我们的生活,除非有一种新的宇宙秩序、心灵秩序的建立,然后才可能带来一种自由的社会秩序的更新。
这种自由秩序的建立,不是在人的契约论下,把人的权利转让给国家。也不是为一个人或某个组织的利益。一个良善的社会秩序,应当为每个人身上从上帝而来的形象、尊严和权利,免于他人的破坏,同时阻止人群在公共生活中走向专制。因为人人都有罪性,不存在没有罪性的人,不论总统或任何人,都在这个秩序的管辖之下,都因着遵守这个秩序而得着自由。也因为人都有罪性,所以需要法治。
这样,国家提供法治,约束人群中的堕落;教会仰望恩典,使人从堕落的本性中得自由。一个管理身体,一个医治灵魂,政教分立 ,其实也是政教分工与合作。
基于律法在人类政治中实际而有的强制性,政府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恶”。这恶源于人的堕落。人的良心丧失了自我管理的能力。外在的法治秩序,就把个人自由圈在里面。为了防止法治秩序侵犯个人的自由,限制这个秩序的能力大小和所调控的范围,也就是宪政主义,于是成为必要。政府只能管辖公共领域,不能管辖个人的私密空间;只能管辖人的行为方式,不能管辖人的信仰、思想和言论自由。
这样,在一个“有教堂的开放社会”的社会体系和“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文明范式当中,对上帝的敬虔(宗教),才是对个人自由最至关重要的保障。
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在“我”和上帝的关系中,“我”隐秘地管理我的一切,外在法治秩序,只是保障“我”和上帝的关系能够在地上顺利地表达。在“我”对上帝的崇拜中,我的个体意识时刻都被确认。“我敬拜,故我在”。这种意识也不断提升、激励着“我”以一个个的个体的方式,而活在他人的面前。也因此,一切的自由教育,也必须以信仰的教育为支撑,否则就落入极其荒谬的结局。
从神学史来看,在奥古斯丁那儿,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的体认,奠定了其“双城论”的基础。这既是源于西方悲情哲学的传统——它有些过于希腊化,也是对罗马帝国被毁灭的现实回应。每个人诞生于这个世界,就分属于两个大的体系,且分担了各自的公共责任。政府是法治秩序的提供者,它当保护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自由不受干涉。
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基督徒也有义务顺服政府权柄。但是,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立法者。国家不能决定人应该怎么生活。决定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并指导政府完成其本分的,乃是教会所发挥的正当的社会功能。所有信徒都有义务以自己信仰生活的见证,来帮助教会完成这一社会功能。而不是督促政府将这种独立社会的功能国有化,进而侵蚀民间社会和信仰自由的健康活力。
在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神学中,上帝荣耀的主权占据着核心位置。世上所有发生或未发生的一切,无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政府的权力依然来自上帝的委任,否则就是乱政。所以我们基于对上帝的敬畏,也会对政府权柄表示最大的尊重。因为凡是权力,都从上面来的。
正如耶稣对罗马总督彼拉多所言的,若没有父赐给你的权力,你什么都不能。我们顺服法律,也顺服法律确认的公民权利,我不是顺服任何人,也不当顺服任何人。但我们顺服符合上帝旨意的法律,也顺服执行这法律的任何人。正义和道德的标准,始终在上帝那里,不在人这里,但人怀着敬畏的心,却可以了解。由此,一切的国家崇拜、政党崇拜和集体崇拜、权威崇拜就被否定了,真正的宪政主义在福音的支配下,才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觉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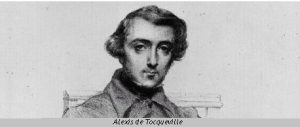
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
托克维尔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之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就以实证性的历史、社会学角度,分别叙述了法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
---------------------------------------------------------------------------------------------------------------------------
由此,在世俗法律无法约束政府权力泛滥的时候,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始终有一个道德性的仲裁者,一个先知般的声音和一个公民社会中的力量主体。那就是由自由的基督徒们所组成的那个社会实体。所以,加尔文所做的就是重新回到、阐释和捍卫基督徒的基于上帝话语的自由。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社会性的个人自由,都只能在一个“有教堂的开放社会”和“基督教正义一元论”中,透过从真理到生命、从生命到伦理、从伦理到法治的转变,才会实现。
自由宪政主义的产生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架构。就连写了《理性时代》的潘恩,也不得不承认“宪法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这一基本的基督教化的立宪观。
拒绝“口号政治”,全方位认识北美殖民地的立宪政治
看看美国宪法的描述,再比较一下圣经中的盟约,我们看到太多的“不要……”,因为这里列举了人常犯的错误,但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基督徒,或天生是义人,反而在始祖堕落之后,生性为恶。上帝通过律法来使人们感到恐惧,使得他们心里的恶,不过分表现为行动。新约中的《罗马书》、《加拉太书》因此确定律法的功效是:教导人认识罪,承认罪,使人谦卑,以至愿意在基督里领受恩惠和信心。
同样,人间的宪法和法律里,第一件要告诫人们的事,就是人是有限的,政府更是有限的。政府必须认识、承认自己的界限。因为宪法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而宪法的道德性,是依据上帝的正义而来的。否则,所有的平等、自由都只流于形式,只会导致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局面。
这种思维,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认识构成冲击,就是认为近代的自由政体,是由无神论色彩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塑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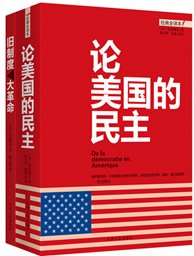
事实上,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的三次革命,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产生了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截然不同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君主专制和国家主义,而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却产生了宪法保障下的个人自由政体。
自由、平等、博爱、宪政、民主,这些美好价值从来不是知识分子喊口号的结果,而是每个人在认识到自己的罪性、有限和无力之后,走向自我克制,相互宽容、接受约束而建立起来的。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持守纯正信仰的基督教会为着信仰自由、政教分立和神的公义,行在地上争战不停。
很大程度上,这一股力量与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力量一起,塑造了近代文明。但宪政主义的真精神的核心,却从来不是启蒙主义的,而是基督教的一种法治的保守主义精神。自由政体的崛起,与这一精神血肉相连。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精神却未曾积累,也不被珍惜,甚至在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历程中,反而被人文知识分子们给予轻率的忽视和妖魔化。不能不说这是近代中国在知识认知方面巨大的损失。
当然,我们对欧美宪政应当有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更加实证的考察。美国的建国事业,不仅有加尔文改革宗清教徒的参与,还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的参与,甚至还有自然神论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基督徒的参与。例如,华盛顿、富兰克林、杰弗逊等,确切地说,都不是基督徒。
用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所叙述的话说,美国革命综合了法国的自然神论的精神气质。1620年的“五月花号”事件作为大规模的移民而成全的殖民地宪政,清教徒抗争的是圣公会的基督徒,也因此,在1787年前后,与这群清教徒在政治上合作的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自然神论者。
亦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美国历史三卷本之一《美国人:殖民地历程》所叙,在基督教的自治精神影响下,立法和司法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对殖民地宪政民主与开放社会有着同样惊人的促进。无论是抵制了乌托邦诱惑的马萨诸塞海湾的清教徒及放弃正义而强调神圣之爱的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还是试图建立福利制度的佐治亚的移民,还有强调宗教自由却同样不乏宗教热情的弗吉尼亚人。这实际上说,美国这里的基督教,是“泛基督教”,而不是具体某个教派。
不过,“泛基督教”,并非说明当时的美国没有一个主导型的教派,而不是说明对美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析理当拒绝一个最合宜的分析方式。“泛基督教”的事实,绝非说对基督教真理和对《圣经》的解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泛基督教”仅仅是说,一个自称教会的共同体中,是由各种各样的组成的:信的,不信的,自以为信实际上仍为不信的;敬虔的,软弱的,甚至还有“背道者”。
自然神论和正统基督教的隐性的、公开的辩论
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在当时“自然神论”的影响特别大。由于自然神论者总是躲藏在具体的教会里,默默地拒绝十字架救恩,且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基督教会共享一套“创造论”的话语,所以除非“属灵的人”没有多少人能够辨明。
所谓自然神论(Deism),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欧,主要是英国和法国。这一体系系统了回应牛顿机械力学对传统神学世界观的冲击。这个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及其运行规则,此后“上帝”并不再对世界产生影响,任其自生自灭。就此而言,自然神论在很多方面与印度婆罗门教对梵天的解释相仿。
早起的法国和英美,自然神论的主要来源是具有闪米特一神教背景、并受其影响的西方唯一神教派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在十字架上受死而承担了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到了后来,自然神论发展为具有多神教背景的泛自然神论,也就是“泛神论”的一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拒绝“设立国教”的条款,起因在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英国宗教专制的警惕。即便自然神论者以此默默反对“咄咄逼人”的正统基督教,自然神论和正统基督教的辩论是美国早期总统大选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自然神论者并不以宪法修正案做正当性辩论,而是公开声称其敬虔程度,以吸取更多(不明真相的)选民的支持。当时杰斐逊的竞选策略就是如此;直到今日亦如是。
1796年,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宣布第二届任期满后将会退休。在次年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他警告党派偏见的不良影响,并呼吁人们抛弃党派之争。但在其第二任期内,美国已分野成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两大阵营。前者由亚当斯(JohnAdams)和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带头,后者领袖则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这三人成为1796年美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总统竞选的主角。

亚当斯和杰斐逊长期竞争,他们却在同一天先后去世
关于杰弗逊的“自然神论”观点
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年),《独立宣言》起草人,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年─1809年),民主共和党创始人。在其任期间内,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使美国领土近乎增加了一倍。其代表作品有《弗吉尼亚日记》、《弗吉尼亚自由宗教法案》等。
杰斐逊喜好使用自然宗教式之字汇描述“上帝”。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使用的便是诸如“造者”("Creator")、“自然界之造物主”("Nature'sGod")等词句。
在殖民地时期,杰弗逊所执政的弗吉尼亚,英国国教派为维吉尼亚唯一由政府资助的教派。杰斐逊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明,大致上同意其友、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JosephPriestley,1733-1804年)之“上帝一位论”。
拒绝“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二性”,意味着拒绝承认“因信称义”。
杰斐逊不相信耶稣之神性,却自称十分尊崇耶稣之道德教诲。一如众自然神论者,杰斐逊不相信神迹。他自制的简要版福音书中,大部分仅有他所认可之耶稣之道德哲学(例如“登山宝训”)。这本杰斐逊版圣经于其身故后发行。
然后,在四福音书中,耶稣一再认真地自称为神,是基督,是受膏者,是造物主、是创始者、更是救赎者。这样,单单承认耶稣的道德完美却拒绝承认耶稣是神,只要严格推理,要么认为耶稣是“疯子”,要么认为耶稣是“骗子”。
若杰斐逊是正确的,欧美自然神论所寄生于其中的正统基督教则必然崩溃。例如“复活”是神迹,正如《哥林多前书》15-19所云,“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在当代社会,严重的事实或许还是,声称认可“自然神论”,由于实际生活中没有多少人愿意与“自然神论”共享一套意思形态话语,基于实用主义的生活处事原则,中国特色的自然神论将不得不转化为承认中国儒家所云之“差序格局”者。
“差序格局”一词由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旨在描述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请参考: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3-36、102页。)
在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很多基督徒的想象中,美国国父都是道德高洁的彬彬君子。从情感上说,他们无法接受一个靠谩骂对手和信仰指责而上位的总统。但事实上,杰斐逊与亚当斯的竞争并不缺乏火药味。杰斐逊派攻击亚当斯,说他是个亲英的保皇派,企图把总统之位传给儿子,开创亚当斯王朝。亚当斯派则抓住杰斐逊的信仰问题不放,声称杰斐逊是个无神论者。
事隔四年,1800年,亚当斯与杰斐逊再度为总统之位对决。杰斐逊仍然因为其宗教信仰饱受攻击。纽约的里恩(WilliamRiehen)牧师的批评尤为引人注目。在一本名为《关于总统选举的几点严肃思考》的小册子里,里恩质问道:“杰斐逊去过教会吗?每个主日他是如何度过的?他与哪个教派的基督徒一起做过礼拜吗?”他继续说:“假如我们的总统公开表明他不信教,那么围绕在他身边的都将是异教徒。……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不敬虔将成为家常便饭,而接踵而来的是普遍的淫乱。”
这同样意味着,美国社会后来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自由国度的崛起”那一刻,已经被显明出来。这个国家后来难免出现的“投机”和“背叛”,是“罪”的必然。
余论:一个开放的议题,实证考察美国基督教社会自由民主的崛起
无论如何,对比法国等天主教为传统的国家,对比更多的国家,美国已经表现出了其鲜明的“民族大熔炉”之开放社会特色。美国宪政,可谓得天独厚。
在总结有助于美国奠定和维护自由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之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列举了三项因素:“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而且特别强调这三项因素是“我一直认为”的。托克维尔进一步认为,地理环境没有法制重要,法制没有基督教背景的民情来得重要。
这种立体考察的结果是,我们承认必须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欧美宪政的形成,而不是单单从基督徒的信仰宣告等角度来确认。《圣经》的逻辑也是,被赞美的是又真又活的三一神,祂的创造、祂的救赎、祂的护理和祂的审判,而不是基督徒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的信仰,更不是基督徒的各种“信仰政治”。
用给《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美国修订版)写序的康来昌牧师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美国“五月花号”讲述的是“正确而美好的分离”的圣徒故事。美国后来的福分是耶稣基督“恩赐”的结果。面对这位“恩赐”而非“祝福”的神,我们应当感恩,而不是与“世界”联合、任凭撒旦试探以致肉体犯罪引来神的震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