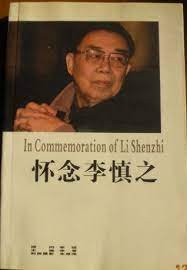 民主中国资料图片
民主中国资料图片李慎之有篇信体文章,题目叫《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收在《李慎之文集》上卷。看这套文集通例,这篇信体文章在李慎之生前包括在文集出版时并没有公开发表过,否则会在页下标注。
信的开头就称赞胡绩伟:“你是当今中国最敢直言的人。我向你致敬!”这应该是李慎之的心里话,也充分表明了温文尔雅的李慎之对敢于直言的向往。你看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又何不是“当今中国最敢直言的人”呢,甚至,他的直言和勇气完全可与胡绩伟媲美。
一个人打内心称赞什么或向往什么,多半会在言行中表现出来。李慎之称赞和向往“直言”,并且在他心中,有胡绩伟这样的榜样在,也就不难理解他晚年的直言和勇气了。
说起来很做过几篇类似“李慎之读后感”的稿子,都是些随笔、评论。可待有一天读闵家胤先生《从慎之先生游》,忽然觉得,好像自己从来没做过有关李慎之的文章似的。
为何会有这种错觉?想了想,可能与我这个作者给读者“提供”的都是大家已听过看过却并没什么新鲜东西有关。而《从慎之先生游》就不同。作者文章中许多都是“独家”,也就是说,作者不说出来,绝大多数读者不知道,甚至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就有价值了。
比如,有次作者搭李慎之车外出,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转的时候,李慎之指着社科院大楼说:“这座楼是1978年邓小平亲自批一个亿盖起来的,同时下令把学部提升为社会科学院,立刻建研究生院,招你们‘黄埔一期’四百人进来。那时他认为,自己搞改革开放,要同四人帮那伙人辩论十年,可是自己没有理论阵地,两报一刊全在人家手里头。”停了一会儿李慎之又说:“可是后来邓发明了‘不辩论’,搞特区,让事实来说话。”邓小平为什么不辩论了,当然有“让事实来说话”的借口,可真要辩论起来,会不会引火烧身,他不能不想。另外,这时的邓小平好像还没有大权在握,否则是不会允许“两报一刊全在人家手里头”的。
再比如,李慎之对他那届院领导颇为得意,多次讲:“我们那届个个是专家学者,不像后来。你看,胡绳是党史专家,丁伟志是历史学家,刘国光是经济学家,汝信是美学家,钱钟书更是学问大家。”然而,对胡乔木却明显有微词:“跟胡乔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懂得什么是‘胆小如鼠’。”可就是这么一个“胆小如鼠”者,却管控着偌大一个国家的舆论宣传(虽然他要听伟大领袖的)。此外,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致胡绩伟的那封信中,李慎之说胡乔木其实“是一个尴尬人”,而且“一辈子都是”;还说“胡的‘右派思想’也不少”。
还有1989年“六四”后即1990年春天,闵家胤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加“多种文化的星球”项目,负责撰写“汉字文化圈”,要到巴黎赴会,就是李慎之批准的;而这很可能是李慎之被解职前批准的最后一个外事项目。
作者这样写道:“在我向他汇报过这个项目而他也表达了兴趣所在之后,他说:‘你从巴黎回来之后,再到我这儿来一次,讲讲详细情况。’我问:‘到哪儿?还到这间办公室来吗?’他说:‘不要到这儿来了,马上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可能是我批的最后一个外事项目。到我家去吧。’接着,他就把家庭地址和电话都写给了我。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他笑了一声说:‘我已经被解职了。看吧,这是刚送来的解职令’。”
李慎之犯了什么错?原来,当年学生运动起来后,他鼓动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丁伟志一道起草一份文件,并说服院长和其他几位副院长都在上面签名,向中央施压。特别是在大军进城后,中央召集副部级以上干部开会,他竟然说“我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并拒绝出席会议。
你说这还了得。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这是多么难得哦!当年有几个官员有勇气像他这样说话?在读闵家胤这篇纪念文章前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从慎之先生游》作者说他当时“吃惊地接过解职令一看:刚打印出来,深蓝色油墨未干,寒光熠熠,字里行间似有刀光剑影在晃动”。
解职令是怎么说的呢?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不应该还那么敏感,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吧:“1989年夏天,北京的学生运动起来了。李慎之说:‘民气可用,社科院要表态。’于是鼓动常务副院长丁伟志,一道起草了一份文件,说服院长和其他几位副院长都在上面签名,向中央施压。大军进城后,中央召集副部级以上干部开会。李慎之说:‘我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并拒绝出席会议。鉴于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的恶劣表现,经院务会议和党组研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从即日起,正式解除李慎之担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两项职务。”
作者紧接着这段话下面是这么说的:“这段话,我之所以敢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一辈子就只有一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读的时候又胆战心惊,全神贯注,所以读一遍内容就全记住了;可是,肯定不敢保证一字不差。”即便如此,做为读者,也要感谢闵家胤先生。若不是他当年看到并用心记下,在纪念文章中又讲述出来,我等哪里晓得。先前在李慎之送别钱钟书先生的《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一文中读到“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时就觉得李先生已经很勇敢了,想不到当年他还有更勇敢的表现。
看完解职令后闵家胤不解地问:“您真说过‘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啊?’”李慎之“呵呵一笑,说:‘你不知道啊?这是我李慎之的名言。美国之音不断广播,早已传遍全球了!’神色流露真实豪情。”本人孤陋寡闻,估计当年很多人通过美国之音听到过李先生那句“名言”,但我觉得,只有读了《从慎之先生游》,才能最后确认!
一个敢于直言者,即使碍于形势,碍于身份,有些“直言”不便作文公开发表,也还是会在私下“忍不住”吐出一些。而李慎之到了晚年,做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面自由主义的旗帜,即使在他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能看到在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作品中看不到的直言。这一点,有《李慎之文集》佐证,不用赘述。公开尚能直言,非公开或私下,李慎之的“直言”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了。这方面,在读《从慎之先生游》时感受尤深。
在纪念文章中,作者说他回想起李慎之与他曾多次谈话,并在文章中记述了几条“很有价值而值得记录下来的内容”,这里容录一二。
李慎之有次跟闵家胤谈起毛泽东,李慎之“他满腔激愤地说”:“毛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中讲,中国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这段话是大错特错了,中国恰恰是世界上最不白的那张纸,最黑最脏的那张纸。”
闵家胤紧接着发了几句感慨:“细想,慎之先生说的对呀!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李泽厚称是‘积淀’,柏杨说是‘酱缸’;至今中国还是死人拉着活人,传统阻碍着现代,哪来一张白纸?倘若建国之初美国的华盛顿说‘北美新大陆是一张白纸’,那还差不多。”
又一次,在李慎之家中他们谈起邓小平,期间李慎之说:“邓小平搞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他应当继续搞‘中国特色的多党议会民主制’。”
这后一句的意思,李慎之后来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再也不想压抑着,而是勇敢地公开说出来了,且显然是带着极大的不满说出来的:“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这可是恩格斯的主张啊!”
今天可以说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后的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大倒退,与邓小平生前因害怕否定自己或者害怕“中国动乱”没有实行政治改革有极大关系。赵紫阳朋友王扬生2004年7月拜访赵时,赵就告诉他,邓小平不喜欢权力分散。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邓给赵紫阳打电话,特别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
此外,当年邓小平为什么要那样大讲特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还要强调“一百年不动摇”?这与他后来有些公开说法很矛盾!比如,1990年1月,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香港地产商李嘉诚时,说香港制度不仅保持五十年不变,而且五十年后不用变了。“不用变了”是什么意思,只要不是傻子都听得出,就是说到那时,中国内地与香港实行的是同样的社会制度,即自由民主。既然是同样的制度,五十年后香港的社会制度还用变吗?
比起常人来,李慎之无疑要算一个伟大的思想者,特别是读他晚年发表的那些文章,即使称其为“当代思想家”也不为过。闵家胤纪念文章中说李慎之晚年每年只写两三篇文章,而这两三篇文章在当时都难以公开发表。然而,就是这难以发表的文章,在且不说尚未出现微博微信,而就是互联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要算生疏的年月却能不胫而走,并为作者带来巨大声誉,由此可以想象李慎之文章的魅力。
对此,闵家胤在文章中是这么说的:“慎之先生赋闲之后,从九十年代初起,不多不少,每年都写两三篇文章,也只写两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以少量打印稿形式散发;可是,全都在京城不胫而走,回响士林,并令作者成了无冕王者。”
这些文章在李慎之去世后不久,很快就被搜集并出版了《李慎之文集》,虽然不是什么正规出版社,也非豪华装帧,但只要能印刷,能出版,能正常阅读就行。
原以为李慎之的“重要思想”都在那套《李慎之文集》中了,可当读了《从慎之先生游》才意识到,除了一套《李慎之文集》,李先生一定还有更想说的话,只是觉得不宜用文章或没有来得及用文章表达,仅仅跟朋友或信得过的下属以闲聊的方式表达出来。想想,如果中国有西方那种言论自由的环境氛围,李慎之未必不会把他那些像“零金碎玉”(李慎之对钱钟书零散文字的比喻)的思想化成文字,饱读者眼福,给中国思想界带来进步。
说到这儿,不免悲从中来。几千年不说,单说1949年后,由于一党专政,特别是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没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浪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多少聪明才智!而这么多人的聪明才智,且不说对个人,就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多么巨大的财富!统治者们并非意识不到,而是缘于他们把维护统治政权看得高于一切!中华民族何其不幸矣!
一位曾在美国与李慎之见过几面的海外人士杨力宇,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李慎之对中共的沉痛忠言——怀念一位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文末告诉我们:“与其他反对、批判中共人士迥异,李慎之拒绝流亡海外,坚持返回大陆,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奋斗。”如何看李慎之拒绝流亡海外,我的理解,或许李先生觉得他留在国内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这比跑到万里之外而人身也肯定比较安全的民主国家讲些真话显然更需要勇气。
2023.10.15,后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