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文革”运动已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由“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大搞打、砸、抢、烧“破四旧”的阶段。我在雅安,被单位列为第四类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难保,“天兵天将”们又几次上门查书收书,隨身带来的一箱书籍也已被收缴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陈墨却偏在此時突然从成都给我寄来一包书,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艺书籍。其中有一本残破的民国時期出版的《北极风情话》,显然是一本禁书。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陈墨一生喜书,无奈家贫,藏书寥寥,忽地将其全部“家当”给我寄来,肯定处境比我更糟,但他这样做于他是损,于我可是祸呀!我无計可施,只得将这包书付之一炬。
转眼到了是年的12月中旬,全国各地各路“造反大軍”纷纷出笼,扭转了前期专整群众的局面,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成了批斗的对象,一般平民百姓方从人人自危的厄运中找到一点揚眉吐气的机会。我妹到雅安来探望我,住在我的单位上,代我收到陈墨用一张废纸写来的信(托楊枫寄发),无头无尾,只有草草几个字:“姓邓的,把书还来!”我猜陈墨也被“运动”整疯了,仅有的一点点“家产”寄给了我,肯定几个月寝食难安,今天下大乱,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发令收回。但我却是“坑灰未冷”,书魂难招了。
我諒解陈墨,小小貧民一个,衣食无着,居无定所,尚成惊弓之鳥;名重一時,藏书丰富的老舍之流不投湖自尽,怎对得起毛泽東发起的这场“大革文化命”?
1967年5月,全国武斗兴起且愈演愈烈,在成都发生了几场震惊全国的大血案和“成都就要爆炸”声中,雅安也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我像难民一样背包打伞回到了成都,躲在号称“解放区”的東郊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即現电子科技大学),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一天,陈墨匆匆从“国统区”的城南穿过一号桥“封锁线”溜到我家,说想在東郊租一间住房。我说:“成电墙外沙河边的松柏村许多农民都有空房出租,是前几年成电占地后赔修给农民的砖瓦平房,房新树多环境不錯,我陪你去问问。”租房很顺利,我们仅找了一家农妇就达成了租房协议:租房一间,约10平方米,每月租金5元等等。陈墨预付了一个月的租金,我俩便将屋內外打扫了一番,约定第二天就搬家具来。
第二天,我早早地从成电后门到了松柏村,守着“铁将軍”发呆。等到日上三竿,方見陈墨和一个小伙子汗流浃背地拉着架架車来了,車上捆着床、柜、桌、凳等居家之物。小伙子拉着空车离去后,我和陈墨开始收拾。床是一张西式床,这東西只有大户人家才有;衣柜带鏡,非一般家庭之物;写字桌带抽屉,俨然有办公的派头;更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书籍往几个书架上一放,整个房间顿時大放异彩!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臥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現实。陈墨一脸得意,说:“上头抢权,下头抢书,各革各的命!”好一个嗜书如命的陈墨!我无“贼”胆,“傍”上这样的“富家”,何愁无书可读?
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对胡适先生开创中国新诗以来特別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新诗坛的详细资料知之甚少,偶有所得如获至宝,立即相互传抄以供借鉴。1966年5月我在名山县参加单位技术“培训”,休息時在一家小书铺淘得一本50年代出版的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竟如发現新大陆一般兴奋。眼下陈墨“暴富”,“忽如一夜春風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红卫兵们忙着“玩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成了李金发笔下的“弃妇”,也成了陈墨们翻墙撬窗窃取的目标;而在春熙路“黑书市”上,陈墨独具慧眼,专挑有关中国新诗的史料用其他小说交换。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時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視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天黄昏。那天,我和陈墨从上午抄写到下午,黄昏時约出去散散步。我俩沿府青路的法国梧桐林荫道漫步到刃具厂,又从刃具厂漫步到40信箱。夕陽西下,我俩一路上边走边谈“新月派”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地位,“現代派”的成就等等。在这路上往返走了几个来回,终于有些疲累了,决定在府青路沙河桥边的草地上坐一会。
刚坐下不久,20多个持长枪短枪的“造反派战士”突然围了上来。10多人散开作包围开枪状,4个大汉跃身猛扑,两个抱一个地将我和陈墨按在地上。搜了全身,发現没有武器,方松开询问我们。称他们发現我们在这路上走来走去,形迹很可疑。我说:“我刚从雅安回来,住在成电,他是我同学,来看我的。”说着,我将一張证明给他们看。我算没事了,他们便问陈墨是干什么的?陈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就是不说。我想帮着解释,这群人推开我,不要我开口。其中有人对陈墨嚷道:“你不说,就把你拉到总部去,关几天看你说不说!”我知道陈墨身上有一个护身符“红成派”的证件,并从这群人是经成电方向沿沙河过来的情况判断他们肯定属于“红成派”,就大着胆子对他们说:“都是一家人,不要误会,他是‘红成派’的!”一个人强行从陈墨的裤袋里搜出了证件,一看,说:“你这人怎么不说呢?”陈墨说:“我担心你们是‘兵团’的!”另一个大约是负责人,看了证件,说:“一家人,一家人!误会,误会!”我立即拿出一包劣质香烟,说:“众兄弟辛苦了!来来来,抽支烟!”“负责人”很客气,说:“我们是刃具厂的‘八路軍’,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烟也没抽,带着一群人沿沙河回去了。事后陈墨说,他当時之所以不敢亮明身份,是发現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很像“兵团”的,若是真碰上“兵团”的,他就死定了。
《野草》这批人一直是书卷气不足,绿林味太重,那是整个社会环境太恶劣和这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造成的。
当時,“发配”到会東的徐坯,“发配”到攀枝花(当時称渡口)的何归,“发配”到云南开远的明輝,“发配”到喜德的張基,“发配”到宜宾的罗鹤,“发配”到乐山的九九,“发配”到甘孜的白水,“发配”到资陽的蔡楚、谢庄等,都已先后“逃”回了成都,加之稳坐成都的吴鸿、楊楓、冯里、万一、樵夫、兰成、乐加等人,一张被“诗”牵着的网撒在了成都的各个角落,相互之间抄诗、写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也为我们日后搞《中国新诗选》,搞《空山诗选》乃至搞《野草诗选》等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陈墨搞了一本《中国新诗大概选》;
徐坯在冯里的大力支持下搞了一本一千多首的《外国诗选》;我搞了三本《中国新诗选》,另外还请张基帮我代抄了两本诗选;陈墨和我甚至还把自已的诗以徐志摩、卞之琳、陈梦家的名义私塞了进去,鱼目居然混成了珍珠,使不少诗友受到蒙蔽。受害最深的当属蔡楚,他在1975年前后从吴鸿处抄到《久别的微笑》等诗,直到1980年3月才弄清楚诗作者不是陈梦家而是我。当時,为了混淆視听,大家还乱七八糟地取了各种笔名。陈墨除了取有陈硯冰、秋小叶这些很雅的笔名外,还有夕瓦、何必、何苦、黑乌鸦等筆名;徐坯当時常用的笔名有敏铁、曾秋、未了等;我的筆名除了常用的雪梦、野鸣外,还有龚盾、刘恋等。之所以如此,用陈墨的话说:“聊以禳祸耳”。这些当年的手抄本能幸存至今,实在是苍天有眼为了证明我輩在险恶的环境下是怎样“偷食”人类文明供果的!
如果说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只有宗教上的意义,那么我们当時认定用各种办法搞来的这些禁书就是我们的“最后的晚餐”,则是文学意义上的对出卖文学的偽文人和践踏文学的暴政的直接反抗!
第 二 章 南 “诗 愁” 之 路
“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爷爷”被赶下了乡,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网”也越收越紧。我已是成家之人,不得不四处找临時工做,只要有活干,脏累都不怕,能挣钱养家糊口就行。我曾去木材防腐厂扛枕木,挑最小的都扛不起,坚持了3天,累得吐血,自己溜掉。也曾去蜂窝煤厂打煤,负责给打煤机的传送带上煤,开始一阵还跟得上,渐渐手酸腿軟,打煤机“吐”不出煤来,老友熊焰赶来帮忙,我累得一铲子撞在他的腿上,我的工钱未挣到,还得让老友自付药钱。那日子真的过得暗无天日。
陈墨属无业闲杂,东飘西蕩,总感覚被“网”住了,决意邀九九一起到西昌盐源县插队落户。1970年3月1日晚,是一个“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日子,我和徐坯、罗鹤、冯里、楊楓、云朗、黎明、祖祥、伯劳等10多人,聚在浆洗街办事处安排的武侯祠大街一家旅馆里,为即将上山下乡的陈墨、九九送行。大家挤在一个房間内,分坐在两架床上,亮灯夜叙,或慷慨高谈,或激昂阔論,或轻声叮嘱,或掩面暗泣,坐待天明。3月2日晨,一大群人浩浩蕩蕩从旅馆出来,步行到浆洗街办事处大门外,送陈墨、九九等二十余人登上一辆带篷的解放牌货車。汽車开始启动,陈墨忽然从車内人丛中挤到車后挡板前,大声地向送别的诸友揮手说:“再見了!”一声未了,他已是淚流满面。送行诸友受其感染,竟哭声大起,响成一片,“哭声直上干云霄”,尘埃不見万里桥。我于当天一气吟成一首诗《送友人赴山中》,又于第二天写了一首诗《似水离愁》。
据考证,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条由成都出发,经邛崃、雅安、荥经、西昌进入云南而至南亚诸国的南丝绸之路。谁曾想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条路上撒下的不再是丝绸而是“诗愁”?
我曾在这条路上荷锄淹留,何归曾在这条路上凄然回首,白水曾在这条路上临风吟走,谢庄曾在这条路上访我停车问候,張基曾在这条路上与我桥头夜游,徐坯曾在这条路上与我巧遇握手……而今,陈墨和九九,也踏上了这条路,似乎不走这条路,这群人就少了一种缘,更少了严道古镇上的一群诗友!
说来也怪,我于1969年中秋,娶了一位荥经县的知青,了我一生姻缘,竟也因此另结了一份诗缘!
我妻子有一位荥经女友,名叫何东平,与我妻一样,喜读杂书。1970年春节,何东平带了一本小说《阿列霞》来我家探望我夫妻,我竟在该书扉页上看見一首题诗《读〈阿列霞〉》,惊问作者,东平道:“是荥经的一位农民写的。”这还了得,我随即信口说:“明年我回荥经探亲,一定要会会这位农民!”谁知东平当了真,回荥经后即将此口信带给了“农民”阿宁、启邦(峦鸣)、长虹等人,而我却忘了。
1970年9月的一天黄昏,我从二号桥畔的日用化工厂(烘盘香)下班回家,一位满脸络腮短须的青年正在我家等候,自我介绍说:“我叫楊启邦,荥经县人,是何东平的朋友。听东平介绍,你很喜欢诗,我和荥经的几个朋友也很喜欢,特不揣冒昧登门求教”云云。
我听得云里雾里。他又说:“我今天上午11点钟就到了成电,在宿舍区一幢一幢地问,因不知令尊大人的名字,又不知你住几幢几号,只知你的名字,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下午5点过,有人指着你住的这幢楼说:‘2单元有一家姓邓的,你去问问看’,我这才找到你父母。”我简直感动得无地自容!世上真有这等执着寻找一个“带言者说”的人,而且终于在近万人的一个学府里找到了我这个与学府不相干的外人,这只能说是一种缘,一种一見便永远砍不断的诗缘!
1971年春节期间,我到了荥经拜見岳父母及探望妻女后,挤時间去了楊启邦的家。他家在严道镇西街,进一条房与房之间形成的狭窄甬道,深处的一个独立小院落就是,一溜瓦屋前有一个小晒坝。,我被启邦热情地引领进一間生着火炉的屋内,一张靠木壁的木长凳上坐着两位青年,经启邦介绍一个名叫阿宁,家住六合乡下;另一个名叫长虹(石章辉),是知青,两人均是启邦的诗友。
启邦的母亲以一种我永远难忘的微笑欢迎我,说:“山野之家,幸勿見笑。”我惊得一愣一愣的。这哪里是农民的语言?果然,楊老伯母原系古蔺一书香门第,至今还能随口将吴芳吉的那首长诗《婉容词》背诵完,唐詩宋词更是信手拈来,不能不令人粛然起敬。
家有知书达理之母,乃子女之幸。然楊氏一家4个子女,皆因大饥荒年代其父饿死后各自逃生,方捡得一条活路(大飢荒年代,荥经全县十多万人,饿死大半)。楊老伯母忙着为我们准备夜宵,我和几位诗友围坐火炉谈起了诗。很明显,阿宁是这几位中学识最渊博,诗也写得最好的一位。他的一首《活着为什么》就把我“镇”住了(他的代表作是写于1973年的《鹰嘴岩》);长虹的《故园》也写得十分生动形象(他的代表作是写于1973年的《老黑哥》)……品诗論诗总令人特別兴奋。我将临時抄写的几位成都朋友的诗拿了出来也请阿宁等人指教,他们也是一惊一诧的,说去年启邦从成都抄回这些诗他们还不太相信云云。三更時分,楊老伯母亲手做的湯圓端上了桌,岂只我赞不绝口,连阿宁都至今难忘,你说大名鼎鼎的“赖湯圓”算什么?通宵长谈,竟毫无睡意,这诗的魔力真可使人忘却长夜,忘却严寒……
两天后,启邦陪我沿山路步行去花滩区六合乡拜访阿宁。阿宁的家,在六合街后,一幢瓦屋被四周的田野树木和一弯清溪环绕,颇有“结庐在人境”的况味。那時,阿宁的父母是“双管”份子,被周围的乡邻监控得規規矩矩,不敢乱说乱动。我只知他的父母原在四川大学任教,50年代下放西昌后转回原籍荥经务农,却不知我的造访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危害!
稼轩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他断然想不到千年后的我们却是“少年不识世道险”。吴老伯父只对我点点头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吴老伯母微微一笑并不言语便进廚房忙晚饭去了。我和启邦被安坐在阿宁的臥室里,听得阿宁在廚房小声地对其母说:“把屋梁上的那块腊肉取下来做菜。”吴伯母小声说:“那是准备给你西昌的妹妹寄去的。”阿宁说:“我去信给妹解释。”说完,无事似的走出廚房进入臥室与我们交谈。
掌灯后,我和启邦应邀共进晚餐。那是一顿令我百感交集的晚餐。阿宁的双老简直是象征性地吃了一点饭就离桌了,说是不打扰我们谈话。饭后又摆谈一阵,启邦因有事,独自摸夜路回城去了,我留宿阿宁家。那一夜,我和阿宁抵脚而臥,窗外远山隐隐,流水潺潺,林叶摇动,万籁俱寂。我俩躺在床上,谈诗到天明,我甚至将拟搞《空山诗选》的打算也说了,忘形了不是?
南丝绸路上,我是满載“诗愁”而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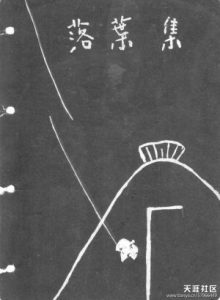
第 三 章 落 叶 满 空 山
1970年11月初,上山下乡刚8个月的陈墨突然从盐源县神秘地回蓉了,说是盐源生活太苦,想做点什么土特产生意挣钱云云。我当時正遭遇盘香滯销临時工被辞退且妻子临产急需用钱之時,对陈墨的困境爱莫能助。11月9日我女兒在荥经出生,初为人父,我虽喜亦忧,心急如焚。
11月13日(农历10月15日)是陈墨25岁生日,我邀他往杜甫草堂散心。那時的杜甫草堂一派萧瑟荒蕪的景象,偌大的园里少有游人。我俩在森森的楠木林中的小道上边踱步边交谈。陈墨将他在盐源乡下写的两首《独白》诗和白水君从甘孜寄给他的《小病》、《寄友人》、《笑》等几首诗交给我览阅。我细细地读了一遍,不禁为这几首诗叫绝。特别是陈墨的那首《独白·我要把忧愁忘掉》,我以为是陈墨迄今为止的登峰之作,短短的八行诗,却有着小说的份量,优美反复的吟咏中给人无限的联想空间;而白水君的诗,我在1969年通过陈墨读到他的《复硯冰信》等诗后,就给我极大的震动,被我視为中国新诗坛上的一朵奇葩,并迫不及待地与陈墨一道去成都城北建筑设计院宿舍拜访白水,今又读到白水的《小病》等诗,使我更加刮目,其《小病》一首,堪称中国新诗精品,“梦里犹枕着异乡溪声”,一个“枕”字,直追古人炼字之工力,结句“仿佛又听見母亲喚小鸭”,意在言外,读来令人心碎。吾乡唤鸭一般用“来来来”之音,此处借唤鸭之声暗喻母呼兒归之意,正是妙不可言。我越谈越激动,陈墨却郑重地说:“这些年来,朋友们写的诗都只是相互传覌,极易散失,若能搞一个诗集就好了。”我说:“这有何难?我平時就收集了不少,搞个诗选易如反掌!”陈墨为人一惯直来直去,一輩子搞不懂“激将法”,怪只怪我自己一兴奋就忘了“油盐柴米”,脫口就是“一锤定音”。陈墨说:“那好,你搞个选本,我给你供稿!”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但,总该给这诗选取个名字吧?”此時,几片黄叶从楠木林上飘落下来,陈墨一激灵,说:“就取唐诗中‘落叶满空山’诗意叫《空山诗选》吧!”
我事后方知我把自己“吊”起来了,不搞出《空山诗选》来就无法“解脱”!
1971年春节后,街道办事处经不住我的天天纠缠,终于给我安排了一个其他人只要有口饭吃就不愿去干的工作——在東郊的一家小型简陋的水泥厂造水泥。这工作“三大”、“一倒”。“三大”是粉尘大,噪音大,劳动强度大。“一倒”是三班倒,换人不停机,昼夜连轴转。我最怕的不是“三大”而是“一倒”。尤其是逢夜班,简直要了我的命!白天无法休息,晚上连个打盹的机会都没有,一周夜班下来,人整个儿脱了形,连走路都打偏偏。
为了那每个月28·50元的全部工资,为了跟我受苦的妻儿,我把命豁出去了,而且一干就是10年。我当時的最大愿望就是干若干年我的工资能达到每月64元(本厂工人最高工资标准)。妻子生女儿后,无法在公社挣工分,来成都当黑人黑户,全家人的口粮成了大问题,每月工资买了“黑市粮”后就所剩无几,得扳着指头过日子。走投无路,妻子去割牛草卖,一大背牛草能卖一、两角钱补贴日常开支。一次我下夜班,早上八点过偏偏倒倒回到家,妻割了一背兜草正打算出门去卖,几个月大的女儿醒了,吵着要妈妈,我说:“你抱女儿,我背草去卖。”肚腹空空,神志不清,我咬牙将一背草一口气背了近千米,驮到百货大楼一拐角玻璃櫥窗边沿,想依靠一下歇口气,谁知往后一靠太急,哗啦一声将櫥玻撞破,被抓进百货大楼办公室要求赔偿,说这是从秦皇島运来的浮法厚玻璃,价值八百多元还未包括运杂费云云。这天文数字我一家三年不吃不喝也赔不起!最后由我的单位出面协商处理,单位出一点,每月在我的工资里扣一点。人说:“麻绳尽朝细处断”,天有時真有绝人之路。这种日子只有怒火,还能有“诗”么?“愤怒出诗人”,我当時愤怒得只想上山为匪了!这年10月,我的父亲又因病去世了,我的天真的全塌了!每每想起我的未满周岁的小女儿爬在床沿叫“爷爷”的声音,我的淚就会不自觉地滾落下来。
“易如反掌”的《空山诗选》在我的手掌中整整闷了一年!
父亲的辞世给了我极大的刺激!他在人世間艰难地跋涉了六十八年,辞世后留给我的只是一張民国時期他的一位老友借钱的凭据以及修成渝铁路的纪念章、1956年到电訊工程学院工作参加工会的会员证之类。父亲的一生就如此简单么?他的酸甜苦辣,他的喜怒哀乐哪里去了?父亲逝世百日后,我的心沉静了下来,我不能像父亲一样在人世上“走”得太“干净”,我得走出声音来!走出意义和价值来!
我首先想到了诗,想到我承诺选编的《空山诗选》。
1969年中秋节,陈墨、九九、罗鹤参加我的婚礼,陈墨喜气地将一本漂亮的日记本和一支嶄新的钢笔递到我手上,说:“我、九九、罗鹤三人送你这个本子和钢笔,一是祝贺你和嫂子喜结良缘,二是希望你坚持写作!”当時参加婚礼普遍的社会风气是送日常生活用品如脸盆、保温瓶之类,恶劣的送“毛选”等。陈墨、九九、罗鹤此举,显然别出心裁,寓意深远。我太珍惜这礼品,一直不敢妄动。当我决定搞《空山诗选》時,我想到了这个日记本。
1972年春节后,我对《空山诗选》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首先在我以前的各种抄本上初选了陈墨的《独白》、《她要远去》、《薛涛井畔》等,徐坯的《夜巡》、《梦》、《露》等,何归的《我发現了爱情》、《冬夜书所見》等,白水的《复硯冰信》、《小病》、《红豆》等,阿宁的《活着为什么》、《无题》、《祈祷词》等,冯里的《爱情》、《自由》等,吴鸿的《小溪旁》、《独舞》、《清音阁》等,楊枫的《古银杏》等,长虹的《故园》等,峦鳴的《答友人》,张基的《雪堆中的鼾声》,九九的《秋月》、《火柴棍》等,罗鶴的《并非钗头凤》,我的《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当春風归来的時侯》、《秋游草堂》等,以及楊黎明的《纸船》,吳智楠的《母亲的眼淚》,峦鳴的朋友林仲威等人的诗共200多首。通过对整个日记本的安排和诗行计算,发現只能容纳150首,于是我又精选了一次,开始在日记本上的抄写工作。我特意在目录前空了几頁,留待陈墨写一篇序什么的。我进行得很慢,除了每天我必须上班,只能挤下班后的時间抄写外,我对这个诗集还必须尽力做到字迹工整,绝不能有错別字等。陈墨下乡前送我的那本《新华字典》帮了大忙,也使我在七十年代末搞《诗友》時闹了大笑话。因为这本字典是五十年代编辑的,汉语拼音尚未定型,鉴于当局对《野草》的围剿,搞《诗友》時一律用汉语拼音字母替代作者,结果“Z·K”有三个,“清和”变成了“坑和”。
我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時间,于1972年4月底前完成了《空山诗选》。我一桩心愿已了,兴奋莫名,邀徐坯、九九、罗鹤、乐加、云朗、黎明等九人骑自行车往青城山暢游了三天。
第 四 章 一 夜 惊 魂
《空山诗选》是一个手抄孤本且内容多为当局所不容,故首先在成都的朋友间传覌時,就严格限制外传;若需转抄一律使用作者认可的化名。朋友中间转抄得最多的是吴鸿(当時化名华汉,有个人诗集《冰凌集》等)、楊楓、罗鹤、峦鳴、运全、熊焰等人。当時,陈墨尚在盐源,白水已返甘孜,張基仍滞喜德,阿宁、峦鳴、长虹等长困荥经,这些友人飞鸿传书得知《空山诗选》已经搞出来却不得一見,恨得牙痒痒的。阿宁来信说:“行行好,明年春节探亲,请务必将《空山诗选》带来让荥经诸友一睹为快。”我顾虑太多,不敢遵命。
1973年初夏,九九“装病”跳出了农门,将户口迁回了成都。我把九九当成了能人,邀他陪我往荥经帮我妻“抢户口”。是年八月底,他随身只带了一把吉他跟我到了荥经,指导我妻在医院检查前夜如何大量喝水,如何倒吊,检查時如何在小便中加蛋清,如何坐姿悬空以加速心跳等等,结果被医生识破,未开到一張病情证明不说,还将我妻“折磨”得够嗆,当然户口也未“抢”到。因我未将《空山诗选》带去,阿宁、峦鸣、长虹等人大为不满,好在九九的几曲吉他弹唱终于“抚平”了他们的“愤怒”而且闹震了半个县城,连县文艺宣传隊都热邀九九去做艺术指导混了几天饭吃。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为了最后見证《空山诗选》的真实性,峦鸣再也按捺不住了,虽然他抄了不少诗友的诗,但他仍迫切想知道哪些诗入选了,便于1974年5月专程赶来成都一睹《空山诗选》“尊容”。到我家的那天,正逢我上白班,我妻子接待他,留他在家“饱读”。他读后兴起,给我留一条曰:
梦兄:好吧!
未能晤面,我将仲威处的诗五首(另附我的一首)献上。作为诗,
它们可能不够格,缺少诗的情调与味道,实不敢与《空山诗选》中众
君媲美,然而作者的心灵也曾被当時的激情所抓住,而采用了这种形
式。但从诗中实在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完人的。仲威早沉泥淖中,而峦
鳴者却还愿意有人救助,不然七窍之心闭塞尽矣!
读《空山》感受颇深,对于爱的永恒,只有夕瓦君能表述得那样
完美、深沉;对于理念世界的热烈追求,战斗的渴求,人类的爱,只
有梦君能使字句间传出阵阵金石的铿锵,吹出有力的生命的气息;爱
与剑是阿宁君所能把握住的结合物。其他诸君各有其立意较好而表述
特新的佳作。但从整个看来,量与质就不均衡了,可見修养的深浅矣。
可能无空闲来此了,留此纸以呈君。如我不到金堂,当再来奉教。
搁笔
祝宁静
峦鳴 即日
“祝宁静”却偏不宁静。许多時候许多事情无論如何規避,它仍要找上门来,让你防不胜防(眼下的《野草》案又是一例)。这不,一个始料不及的“黑弹”(应是从阴沟里扔出來的炸弹)就在1974年11月在朋友中“爆炸”开来,这就是突发的熊焰“叛国投敌案”!
熊焰是我的老友,其父早亡,小学毕业后便参加了工作。由于长期与老朋友们的交往与频繁的接触,使他对诗歌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这人,好勇斗狠,性刚烈,能与诸友相处甚欢,实属怪事。1965年陈墨生日,他居然也咿咿呀呀地吟哦了一首打油诗赠送陈墨,诗云:“今夕深秋二十載,硯盘橫溢八斗才,拂尽寒窗暮色意,冰结一块如玉开”。朋友间的文字游戏,他也学会了,将陈墨的筆名“硯冰”嵌了进去,真是应了那句古话“近墨者黑“。朋友们的诗,他抄了几大本,加之记憶力特强,许多诗他張嘴就能背诵出。我的那首臭长诗《春波夢》,他竟能一口气背诵几十段。
就这么一个人,竟于1974年夏鬼使神差地在红灯牌收音机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向“台湾”靠拢。第一封信他用“台湾”在广播里介绍写密信的方法,用假名左手写成后到外地寄出,没想到“台湾”居然收到了,并反复在收音机里向他喊话。他静覌了一段時间,没有发現周围有异常情況,于是就在成都发了第二封信和第三封信,仍用假名左手写的。“台湾”因此锁定范围,在收音机里继续向他喊话并约定某月某日在成都文化宮大门处派人与他“直接联系”。他混在行人、游人中去逛了一圈,就被“台湾”盯上并跟踪他一段時間后,于1974年11月21日晚,在家中将他逮捕,同時抄了他的家。这時他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诱他“入瓮”的“台湾”并不在海峡那边,而是这边的一个圈套。
他被捕,使朋友们惊恐万状。一是他的“罪名”太大了,“跨界”了,已不是当年买卖一辆无牌照的旧自行車把人供出来关几个月了事;二是他牵连的人太多了,他与朋友们的合影照不说,单是他抄在几个本子上的诗,就够大家分摊“罪名”的;三是“跳老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几輩子都挣不抻……
总之,我是他“落马”后最受当局“关注”的一个!
首先,他与我往来最密。他被捕前几乎天天往我家跑,明是与我夫妻下围棋,谁知道暗地里交换了些什么“情报”?公安盯了他几个月,我这里当然天天“聚焦”;其次,他抄我的诗最多,当然不只是那首《春波夢》,就是一首《当春風归来的時侯》就够我进去“解释”二十年!
我无法“解释”。与其等他们上门要求我“解释”,不如我自行了断。
我首先“自行了断”,就是焚文焚诗。凡是有关我的诗,我的日记,朋友们的诗,最重要的是《空山诗选》等,紧急投入炉灶。其次是坚壁清野,转移部份文稿抄本,选几个靠得住又与熊焰接触不多的朋友分別存放。忙乱了几天,屋内空空如也,专候有关人員上门。
公安未上门,一位老友上门了,说他的单位领导已找他查问有关熊焰的事,我放在他家的那些“东西”已不安全,问我怎么办?我肯定不愿連累朋友,非常干脆地说:“晚上我去你家取走”。他匆匆离去后,妻对我说:“你去目标太大,还是我去吧!”我想也是,但取回来放哪里呢?一時想不出一个稳妥的方案,于是我把心一横,说:“不必取回来了,今晚你去把这些东西全烧了!”当晚下起了雨,妻抱着刚半岁的小兒子作掩护冒雨赶了去,与老友夫妻烧了一夜,十年心血几十本筆记在老天哭泣声中倾刻化成了片片灰烬,天亮后妻才抱着兒子回来,疲累得倒床就睡去了。由于当時转移太匆忙,我不清楚那一包“东西”里究竟是些什么,我为此心痛了许久,仿佛烧掉了我的生命。
公安一直未上我家门,也一直未上其他朋友的家门,证明熊焰是一条汉子,把一切能背的不能背的全背了,被判徒刑八年。1980年10月,他平反出獄了,像英雄一样受到了全体朋友的欢迎。而我们大家的第一本诗集《空山诗选》,却永远找不回来了!
我总想,如果中国新诗史上不对《野草》大书一筆而让那段历史永远成为一片空白,实在对不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
——摘自长篇纪实《南河背影》1996年10月第一稿 2004年7月4日至10日改稿于“乱躲尘世化缘56洞主舍”
注:2004年6月9日晚,陈墨因“非法出版《野草》案”被抄家,6月21日又被第二次传讯。当時我和妻子正在外地照料生病住院的女儿,晚上得知此消息,我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阻,当晚买到第二天的火車票匆匆赶回,方知事态严重,除陈墨以外,另有几位老友也被传讯,于是在暂時迴避中产生了澄清历史久远的《野草》只是一个“文学小菜园”而非“颠覆组织”的写作冲动,于是在酷热中有了这篇老老实实的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