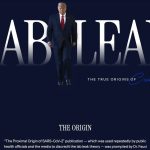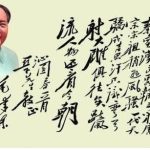“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2.2、追求精英生产的可持续性
2.2-1,零散的体制内资源
正如有知识价值的泛异议力量的著作,在不同层次上产生了影响一样,中国大陆内部在泛异议之外,尚存在一套知识价值化的生产系统。它们很零散,以至于不能严格地使用“一套”这样的概念去描述。
其分散性的特征,本质上是出版审查导致的后果。也正是由于其分散性,产生信息共享的概率几乎没有,只有凭精英阅读方式来产生非规模的价值。而且,这类的分散性知识价值又多以思想性国外著作的译介为手段。
2.2-2,样本性与案例
较早的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注8]一书提供了截然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价值;较近的,远不如哈耶克之书有名的则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注9],给出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对比于西方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及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中国的知识分子该具有何种道德禀赋?
这类的书目,包括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等在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远远超过上节统计表中的书目乘数级。而两者内在的知识价值问题只有一个:中国的精英生产的持续性,是否可能?
2.2-3,激烈的较量
这里的“精英”概念,很狭义,狭义得甚至招致一定程度的泛异议内部的反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之间,三种转型力量在「知识生产——信息共享体系」方面的较量将异常激烈,可能它完全超乎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3.0、城市化与中国转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端绪: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使现代化维继还是崩溃?
这个命题很技术性,甚至被认为不具有战略意义。
3.1、一个纯技术性问题
3.1-1,城市化与老龄化
但是,这个命题至少有两点,可以影响中国转型:
(一)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突破十亿,首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状况;
(二)在以后的二十年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大幅衰减。
3.1-2,第一种力量失败的城市化
面对这样的未来趋势,官方转型力量(即本文第一部分所指的第一种)肯定是无计可施的,而且他们利用城市化进程维系统治策略已经失败了——大量的维权活动,无法预测劳资冲突事件,农地权益空间诱导下的中下层政府黑社会化,不一而足。
3.1-3,“我们这一翼”的压力
那么,“我们这一翼”有解决问题的方略吗?有自己的“影子内阁”提供价值化文本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既然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对第三种转型力量(即不可预知论),就没有任何说服力。
3.2、国际比较,拉美化的含义
3.2-1,阿根廷经验
比之于世界经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层面(特别是泛异议群体)正面临着十九世纪阿根廷悖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阿根廷研究所的主任戴安娜•加托西一瓦松说道:“阿根廷知识分子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度发展的、世界方义的、消息灵通的精英阶层的范例,他们熟悉世界文学和意识形态的新生事物,但却置身于一个强烈抗拒这些新生事务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注10]
3.2-2,另一种拉美化
比照阿根廷也即拉美知识分子的经历,中国正在经历一种当下“拉美化”意义之前的“另一种拉美化”;刘晓波案件,实际上描述了中国在复制“另一种拉美化”之罗萨斯时代那样一种痛苦经历。
很明显,“维稳”这一词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贬义化,它指统治集团或狭义为第一种转型力量不得不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秩序之间所做的艰难乃至狼狈选择。其经济成本越来越成为其内部批评的一个对象。
3.2-3,第一种力量无意真正改革
维稳,不全面失败,第一种力量就没有真正改革的愿望。一些微观例证,已做了很好的说明。四川巴中市的白庙乡财政透明化,即为重要案例。境外分析家就此案例发表评论说:“如果北京希望实施能够改变当前政治与社会的环境重大改革,它是能够做到的,但似乎缺少必要的决心。”[注11]
3.2-4,知识价值的重置
决心,并非一个简单的决策行为,其背后是利益权衡。正是这种权衡,使得第一种转型成为不可能,其不可能的最终结果就是维稳的全面失败。这等于又给第三种转型力量以有力的证据。惟其如此,第二种转型力量的虚拟抗争的压力才更大,知识价值的重置才更显必要。
权衡的失败,在于腐败对政权的维继作用,一如麦格雷戈所说:“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交易税’,令统治阶层获得非法收益……腐败成了保持这一体系屹立不倒的黏合剂。“[注12]
4.0、中国模式与教育制度彻底失败
“中国模式”有时也被称为“北京共识”,在软实力的意义上,它是重视市场力量、转化政府作用的“华盛顿共识”或“美国模式”的替代品,其核心性要素是“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 [注13],因此,“开辟了一条通往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注14]。
借助欧洲政治与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的华人学者、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相蓝欣,曾指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系列问题,其中一条就是:“这个儒家社会本该重视教育,但教育制度却是失败的。”[注15]
4.1、严重的争议,混乱的判断
4.1-1,郑永年和韦森的观点
历来关注中国大陆发展状况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高度政治化,从而影响了学术的真实性:“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不计其数。”[注16]
审美也好,比较政治学评价也罢,国外学者的理论总结与国内总会存在相当差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韦森在对“中国模式”作为一个经济学论点进行比较学研究之后,指出了它的社会学本质:“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步形成,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卷入市场越来越深。”[注17]
4.1-2,秦晖和华生的模糊化
“中国模式”的理论总结如此,但实际存在与否仍是国内学者争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对此予以了不确定性判断:“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注18]同样,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有,但现在还没有” [注19]。这是一个看似清晰,但实质模糊的界定。
4.1-3,严重的学术盲区
韦森、秦晖、华生都是学院类学者,学术身份的基础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所有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讨论,均未涉及教育在这个模式(共识)中的作用,就更不用说教育所具有的文化创新功能在模式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学术盲区,也是严重的现实矛盾:(一)如果一个模式不具有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软实力”因素,那么,它肯定不具备国际上的可复制性与本身的可延续性;(二)如果“软实力”与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不挂钩,那么“软实力”本身就成了伪概念。
4.2、虚幻的软实力
4.2-1,宋鲁郑的忽略
上指盲区或矛盾在非常政治化的制度模式比较表达中也被印证出来,比如宋鲁郑从比较学方面做出的中国六大优于西方的制度因素之研究[注20],亦未给出教育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的说明。
4.2-1,政府仍创造力发挥的障碍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日本与新加坡(如我们刚引日新报纸的文章),在美欧则存在一些惕励性的观点。如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ivad Sharmbugh)认为:中国在向世界传播其文化(如到2009年底的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学堂)时,“总是带有一点呆板和宣传的味道”,“中国政府不断控制社会中最有创造力和最多元的因素” [注21],等等。
4.2-3,软实力来自社会而不是政府
按“软实力”还有后来的“巧实力”概念发明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来说,“软实力来自社会,而不是政府”。
中国社会的创造力被政府力量严重限制,包括政治创新的愿望,而政府也即意思形态主导集团试图通过教育这条单一途径保持国内的主导地位,同时向国际社会输送在传统包装下的新意思形态。但是,正如我们在4.0所引述的相蓝欣的结论那样——这个儒家社会本该重视教育,但教育制度却是失败的——它是本文发现的软实力与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之矛盾的一个注脚。
中国教育体制的失败有多么深远的影响,无须继续讨论,只须看一下近期中共党的最高首脑出席教育工作会议这一新闻就知道了。胡适先生曾说过的“教育亡国”之预测,似乎有了某种印证。
——————————————————————————————
注释部分:
[8]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一书汉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译者冯克利、胡晋华等。该书的副题是〈社会主义的谬误〉。出版者十分小心地在书的封面上消除了副题,而在封面之后,版权页之前,悄悄写上了副题——这是出版审查制度里的“有趣”现象。
[9]《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是法国知识精英纂的一个文集,主编:米歇尔•莱马里,让一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译者顾元芬。
[10]参见[9],P60-74(在P60)。
[11]参见2010年6月15日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文章:“裸露在‘阳光’下”。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17日)转介时的题目为:“『全裸乡政府』困境彰显反腐阻力”。
[12]参见2010年6月19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永远的政党——对中国秘密执政者有趣且深刻的描述”新华社《参考消息》(6月24日)转介时,眉题为:“英报记者麦格雷戈新书《中国共产主义统治者的秘密世界探秘》;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何经久不衰”。
[13]、 [14]参见日本《富士产经商报》2010年3月23日文章:“中国内外对‘北京共识’的看法有所不同”,新华社《参考消息》(3月24日)译介文章题目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并不存在’”。
[15] 2010年相蓝欣:“受困心态”,载于香港《南华早报》2010年6月17日,《参考消息》(6月19日)译介题目:“中国与西方沟通还须下大功夫”
[16] 参见郑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5月4日。
[17]参见韦森(即李维森):“构建良序的市场经济”,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29日。
[18]参见秦晖:“有没有‘中国模式’”,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
[19]参见华生:“可以有,但没有”,同[18]。
[20]参见宋鲁郑:“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0年3月10日;《参考消息》(3月18日)译介题目:“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21]参见沈大伟:“中国施展软实力”,载于《纽约时报》网站2010年6月7日,《参考消息》(6月9日)译介题目:“中国向世界施展新型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