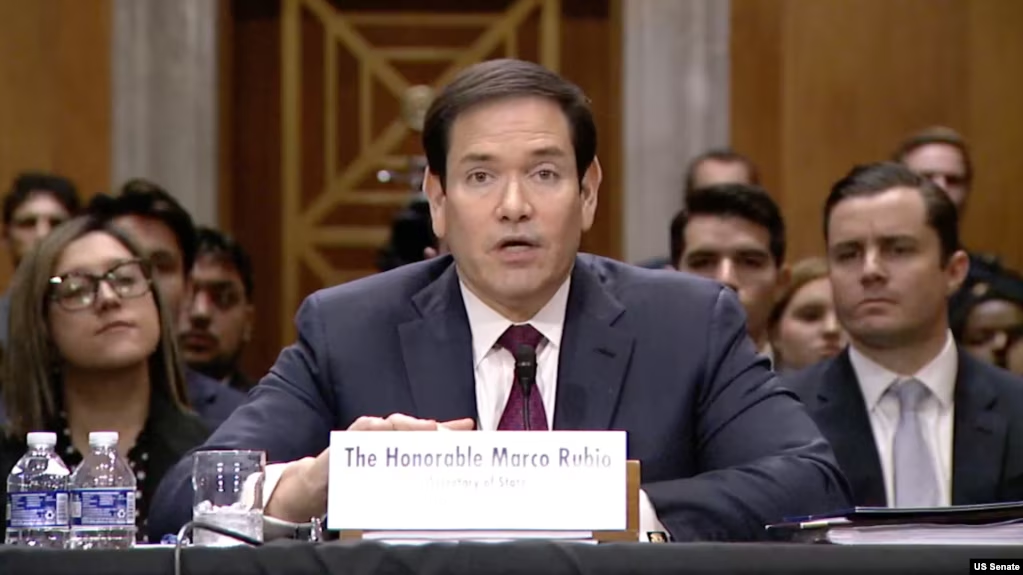在深圳,温家宝高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阔论以其\”科学发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体制改革,激起舆论热烈议论。而《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共喉舌,唯恐人们误解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厌其烦地诵念\”紧箍咒\”,要求\”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可怜,这些喉舌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以为把出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学说,这样胡乱地\”中国化\”一通,就可以成就他们所谓\”创新理论\”。
早些年,中共为其\”社会主义\”建立论述体系,曾煞费苦心, 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论述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此将社会制度脱离现实社会生产力性质制约的论述,可以视为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业之先声。如今,中共苦心经营的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中被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难以阻挡,现实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显现出来,它先前的论调不能不有所收敛。然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不时地还是要厚着脸皮吟唱一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就是最新的一轮演奏。
那么,如此先进的\”民主\”,其\”先进性\”究竟从何而来?
喉舌\”秋石\”声称,\”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历史时, 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俨然以\”理论权威\”面目出现的\”秋石\”,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耍了个手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经济之后的\”第二大形态\”,即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号称消除了资本主义,却还是难以回避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
这种\”物的依赖性\”普遍存在着,可以表现为依赖金钱, 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受到权力的制约,而后者,在东方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应在权力异化方面多下功夫,但是,中共喉舌们念念不忘的是批评\”金元民主\”,对于中共一党专政下权力对民主的压迫,则避而不谈。其实,在民众相当普遍地拥有资产性财富的社会变化影响下,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有了极大发展。民众权利与(资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体现着社会中\”物的依赖性\”本身发生的变化。形成对照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名义上\”以人为本\”,实则以权力及资本为本。在这里,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和压迫,民众在社会事务中只能旁观权力部门以及垄断国企的博弈,实为\”物的依赖性\”泛滥之典型。
喉舌们喜欢嘲笑西方社会选民投票率低, 只因它可以较真实地体现那里的人们对于政治的淡漠,而喉舌们不好意思提及的是,网络中的政治参与正在西方社会里兴起,在线\”微支付\”,以及社交网络与微博客,诸如此类的变化,改变着\”金元民主\”的面貌,而中共对这些变化的防范,也的确在全球堪称独领风骚。
喉舌们自己身在\”物的依赖性\”之中而不自知,自然就不知道那\” 先进性\”来源可疑,于是也就免不了有更多的胡说八道。
中共反对\”三权分立\”,喉舌们给出的理由是,\”权力多元行使\”, 致使\”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于是,中共掌中的\”民主\”标新立异,党权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言论出版结社等诸项权利的立法,都止步不前,但是,\”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还是无法避免。
在改革开放中,为避免这样的状况,曾设立体改委, 时任总理赵紫阳即为其第一任主任,并聚集了一批视野较为开阔的中青年学者,协力推进改革。\”六四\”后,体改委逐渐消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恢复了以往的风气,\”互相扯皮、互相掣肘\”愈演愈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报导了收入分配改革步履维艰的内情,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
无独有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 指出中国的外交决策过程受制于代表不同利益的不同行为者的影响,变得更加费劲和复杂,并且一再导致外界误解。\”德国之声\”对此的报导,用了一个颇为传神的标题:\”半打新厨师参与搅和外交政策的汤\”。
当今社会,多元化乃显著特征,权力是多元的,权利也是多元的。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现实的民主生活中难以回避,也难以或缺,否则,民主本身就变得可疑了。
当年,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消灭了多党制,但他后来发觉, 不允许其它政党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之影响就会在共产党内表现出来。在中国,到\”文革\”后期,毛泽东也以他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好忿忿不平指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革\”结束,中国转入改革开放,而现实的变化,却未能使得顽固的中共转变思维,它仍然坚持它的一党专政。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 致使必要劳动的比例逐渐下降,这一基本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劳动异化为价值,就失去其合理性──用后人的话说,资本主义因为\”创新式毁灭\”而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有意识、有计划地调节经济。至于社会究竟如何调节,马克思当时只是提出他的判断,未具体说明,因为他确信,现实生活本身会显现出它的答案。共产党理论家则顾不得那许多,没有现实根据,他们会生造出根据,论述说,计划经济必然需要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调节。现在,喉舌们要论证中共一党专政,还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争辩说,中国实行多党合作,而这种合作,\”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若指望他们能有所长进,实在难乎其难。
中央计划经济曾经辉煌过,然而它终究在现实的发展中被否定。 至于一党专政,其历史渊源可谓悠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类似的信念,甚至自诩\”天子\”,而中国否定帝制已近百年,中共的顽固坚持,不过是延续他们的愚蠢而已。
——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