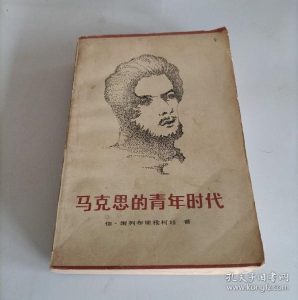中国的知识分子,身处国内的部分,一般都仍遵从马列毛的意识形态,即使内心完全否定马列毛一套,也不便公开表示对抗和反对;已经出国定居的部分,则多半用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待这类问题,除了像李泽厚等哲学名人(学术上转弯子绝非轻而易举),仍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都对马列毛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依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认真阅读,旁征博引,奉为圭臬,是比较罕见的。当然,我们同样尊重他的选择和认同。
我想介绍的是,德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否被修改、删除过,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以及近年来德国人民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德国人民对国际共运,工运和百年老党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在国内我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
文革时我高中毕业,读过一些马列毛著作。阅读时,我的状态不甚好。充满了自卑。因为文革时期家庭出身被看得非常重,所谓黑五类子女,到处都受压抑。读书时,心里想的也常常是所谓的改造世界观,跟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通读毛选四卷,后来又读完了第五卷,此外凡是我所能找到的所有毛选以外的毛主席指示、讲话和诗词(包括一些被误传为毛诗词的作品),我都要求自己阅读,诗词则要求背诵(已谱曲的学会哼唱)。文革期间甚至要求自己每看到一条新出现的毛语录,立刻就要能说出该语录出自第几卷,哪一篇文章。
我通读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因中学一直学习俄语,所以还尝试用俄文还原该书中人名地名的拼写。并按该书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重温学校中所讲授的哲学教条。我选读了斯大林全集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内容(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附毛的学习笔记。我读过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论左派幼稚病》、《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我没有通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厚本的巨著,中学和街道里不会有这样的藏书。我读得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生怕自己不能用先进的思想抵抗自己的世界观。也读过《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对科学的阐述,对基督教迷信的嘲弄,还是非常动人心魄的。有些艰深的内容,我也不免囫囵吞枣。其餘,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编印的马恩关于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论述节录,能找到的我都找来读过。此外,还读过一些列宁推荐的普列汉诺夫著作、法国和德国的反基督教的科学著作。我和很多知青一样,读过《马克思青年时代》;还因为觉得恩格斯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我特地远路借来《恩格斯传》仔细阅读,天真地希望自己也能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文艺理论课又重温了有关的马列论述,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历史知识也得到了系统的梳理。
拨乱反正,大哥的右派改正了,父亲的反革命平反了。我随着留学的人流来到了国外。改造世界观的压力没有了,孩子上学的宗教问题就出现了。德国从小学开始就有宗教课程。天主教和福音新教家庭的孩子,有传统的宗教课程。对移民中的穆斯林学童,逐渐开设了相关的伊斯兰教课程。中国人的孩子,Konfession宗教一栏填写什么呢?考虑再三,我填上了Konfuzianismus儒家文化。学校安排我的儿子在小学是旁听一点基督教课程,进中学则听哲学和美学讲座。我并不随意放弃我的无神论科学观,也不能随意地服从任何宗教意识形态。我皈依了民主和科学的普世价值。置身国外,我赢得了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权,我和我的孩子再也不会有面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自卑和屈辱之憾。
德国人民对马克思的态度
到达德国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有机会瞻仰了特里尔市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当时东西两个德国还没有统一,西德的百姓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崇拜,也没有鄙视。心态相当的平常。
自从八九六四以来,我曾担任留学生中文报纸《欧华导报》的编辑整整三十年。我翻译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威利勃兰特的生平,尤其是在他当主席的任内,社会民主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2005年著名的《明镜》周刊第36期刊登了该刊采访两位德国学者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舛误和全球化的选择》。我将此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翻译了出来,介绍给中文读者,并加入了我的评论。(见附录)。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习近平发表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长篇讲话,中国方面还赠送了一尊马克思的造像,千里迢迢,送到马克思故乡城市特里尔,在德国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讨论,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礼物。一部分马屁华侨搞了一场迎神赛会式的欢迎仪式,大部分德国人民根本不屑一顾。
社会民主党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仍然尊重历史,承认马恩仍是创党时代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跟中苏两党所贬斥的拉萨尔、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并列)。我借此机会阅读了一些他们的文章,从中了解到一些我们在国内不了解的情况。在不同的观点当中,当今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认为伯恩施坦赢得了胜利。
我还发现了一本近年新出的关于马恩生活轶事和书信摘录的书《马恩的私房话》。经过德文编纂者的同意,我获得了翻译授权,并找到了出版资助。在翻译和注释的过程中,我接触了马恩全集的文本,不仅是德文版,还有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怎样收集、整理;存在一些毁损;学术性保护),看到读者们对这类问题的关心,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瞭解的情况告诉相关的读者。
此外,关于马克思的私生子问题的传闻,过去在苏联、东德和中国都一直被封锁,不准议论,不准揭露。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官方的马列编译局出版了从最新英文版(作者是David Mclellan) 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传》,不得不面对历史,承认了事实。据说翻译者王珍女士竟然为此而彻夜难眠。多年闪烁其词的丑闻,变成了铁板钉钉的史实。在无可否认的史实背后,马克思夫妇和恩格斯对于婚姻、爱情、女权、宗教、文化等等问题的态度,并不简单,马恩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从这些微末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分析出他们真实的思想面貌,而不一定如党政宣传部门所描述的那样伟大而圣洁。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
出国前我已暗暗有个心眼,就是希望到达国外以后,留心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地位和影响,而这是在国内的党政宣传监控下无法探索的。根据我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光辉形象是靠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力量树立起来的。此话怎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都很少,《共产党宣言》是一本宣传小册子,所以出版稍多一点,其餘的文章,散见于《新莱茵报》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影响。到了列宁建立苏联政权以后,特别是斯大林经济上升阶段,政府可以拿出一大笔财政金额来从事宣传的时候,就开始支付数以万计的英镑购买马克思的手稿、遗物。二战胜利之后,苏联和东德一起,组织编辑和出版德、俄、英、中以及其他语文的马恩全集和大量的单行本,苏联不仅垄断了资料的信息来源,而且通过苏联和东德的出版机构(以及“国际书店”),垄断了市场价格,全面控制了马恩文献的出版和销售。
苏联倒台以后,中国的马列编译局成为马列出版机构的重镇,继续承担相关的出版和解释的事务,德文版的业务在东德共产党崩溃以后,一度限于停顿,辗转被所谓马列著作国际基金会接纳才得以延续。估计这个基金会也是得到中国当局的资助的。可以预料,如果中共的一党专政也走向末路,马列主义毛思想之类的宣传也将无以为继,风光不再。
根据长期参与马恩全集编辑工作的东德专家罗尔夫黑克尔先生的说法,党政领导按自己的需要干预马恩著作出版的事情是存在的,以斯大林时代最为严重。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类现象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并要求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相信,德国学者的严谨性格是举世闻名的。经过反斯大林化的洗礼之后,马恩著作出版过程中明显的删节和改窜已不太可能。精通中德英俄多种外文的朱光潜教授曾经质疑马列著作翻译上是否准确。翻译不可能绝对准确,在理解和遣词上总会因人而异,但是毕竟跟故意的删节和改窜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很多信件和手稿都留下了复印件,可供查证。上述的删改应该是发生在(俄文版)1956年以前。世界进入网路文明以来,马恩全集也已列入网站。德文、英文、俄文、中文以及其他多种文本,已经出版的都已上网。德文的第二版代号MEGA2是最具权威的研究版。知道某著作的篇名或信函的日期,就能查到。全集中文版五十卷,俄文版六十卷。
遇罗克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词句
遇罗克在文革时期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曾经引用过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语录。那是在中国当时极度专制没有任何其他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他也突破了中共狭隘的“家庭出身决定论”,提出了“社会教育远大于家庭影响”的重要观点。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如果遇罗克当时躲过了杀身之祸,并且有机会走出国门,定居海外的话,他的思想必定不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定能使用更加广泛的思想武器。
德国城镇多有卡尔马克思大街。把历史人名移作街名,在德国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只要历史上算个人物,就有可能入选。只要不是希特勒那样恶贯满盈的恶魔就行。例如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皇家宗室的姓氏是霍伦佐勒,虽是皇家人物,却无甚功德,德国许多城市竟都有霍伦佐勒大街。在中国就不大会有爱新觉罗大街。上得了德国街名的人物,并不一定有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业绩。
每隔若干年就会有人想到马克思
每隔若干年,就有人会想到马克思,讲述他的故事。大概是因为他身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却又标榜关心底层人民,为劳苦阶层呐喊,所以社会舆论会时常想起他。但是他的名声还是依靠他鼓吹的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维持住的。这种暴力政权曾经在20世纪中叶席卷了人类的一半,被暴力政权所杀害的人民数以亿计。马克思留给世界的印象,包括他所描绘的用暴力建立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以及他的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可惜在德国没有任何大学承认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1971年,中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两报一刊社论强调说,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是无产阶级专政,抽掉了这个要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则杀气腾腾地强调列宁和斯大林是“两把刀子”。今天的世界上,坚持赞扬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已经很少,例如印度丛林里的毛派游击队;其餘的马克思研究者几乎都不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而拉扯到异化之类的话题,2018年的德国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找出了一段马克思的名言,竟是保护地球环境的论断:“我们不是地球的所有者,而仅仅是享用者,我们应该将它维护得更好地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从这类转变中,也可以看出暴力理论的不得人心。环保也未必是马克思著作的主旨。现在国内的宣传说马克思仍然在西方社会受到尊崇,还有人仍在继续研究,其实都是不值一提的活动,因为这类活动都与马恩所提倡的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害无关。
把恩格斯跟马克思比较
离开了以马列毛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我们可以从容地走出迷信和崇拜,但是我们也并不需要把马恩简单地斥之为一无是处的魔鬼混蛋。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对马恩两人,我比较更倾向恩格斯一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包含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机制、投资风险、技术更新等诸多因素;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反杜林论》对教会迷信的嘲讽非常诙谐而有力。他对友情的笃重,矢志不渝;不仅资助了马克思的家庭,包括他们夫妇和子女,还有女仆和她与马克思的那个私生子。他又资助了他的妻子伯恩斯的家庭,乃至培养她的外甥女到德国上贵族中学。恩格斯没有上过大学,却掌握了德英法以及爱尔兰和东欧的多种语言,他的评论涉及军事、经济、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有些论述比马克思更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比如在文艺学和美学方面,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和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就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坐标性意义:
- 论悲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摘自 《致拉萨尔的信》 - 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摘自 《致玛 哈克纳斯的信》
无独有偶,2020年德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时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竟然取名为《被低估了的人》。恩格斯的思想能力未必逊色于马克思。
预言家的预言
马克思并没有像国内宣传的那样,至今“仍然是对的”(习近平语),相反马恩的预言很少能找到验证。2018年德国国家电视台ZDF拍摄的电视片《马克思:德国的预言家》的开场白是这样的:“在经济学领域里,自从19世纪末发现边际效用经济学以来,马克思实际上仅只与科学史有关而已。作为一名哲学家,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自从这个方向被克服以后,他也已属于过往陈词。卡尔·马克思的世界意义仅在于这样一种状况,即那些在残酷性上绝不逊色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权们都懂得,如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构建一套一本正经的意识形态。”独裁者们就是苏联东欧中朝越古柬等政权,标题所说的预言家,纯属讽刺和调侃罢了。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用平常心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离开了独尊马列毛的中国,来到了读书和思想都充分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的年龄也从懵懂的学生少年变成了涉世已深的中老年。马、恩的言论,不过是一两百年前两位欧洲读书人的看法而已,不乏真知灼见,也难免无端妄言。国内的马列专家们也不敢直接把马、恩的言论付诸实施:《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就是马克思声讨书刊检查制的檄文。国内宣传部门,哪个敢来当真?中宣部心里明白,国内只要有当年国民党那样有限的言论出版自由,中共的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国内如此,我们置身海外,更应该保留我们冷静的自我,认真读书,也不唯马、恩是从。
马、恩的言论多有不能自圆自洽的言论。我们知道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九条),而且马、恩都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致魏德曼的信》)……注意,恩格斯的论述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國、法国、德国……”,这种19世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口吻跃然纸上。俄国还可能被提及,亚非拉根本被忽略不计。既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文明国家的无产者包不包含在内?要不要一起革命?恩格斯起草这份文件时才二十六七岁,同时参与商议的“正义者同盟”的同道们,大概也是仿佛年纪,思想水平亦大致相若,所以无需多所指责,但也应该看清这类言论中存在的局限性。再者,“同时发生革命”?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是很难按照人们预想的计划安排的。每次革命都是某个特定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集中到无法解决时的总爆发。各国有可能相约同时举事吗?一国之内都行之不易,多国联手更比想象难多了。
忽然间,巴黎公社的工人起义在1871年发出了革命的怒吼。可是这不对呀!一来,没有跟英美大工业国家同时革命。再则,1871年的德国工业化还不够发达,至少要到恩格斯晚年的九十年代才成为第一流的工业国,应该等待德国的工业化发育达标(并具备充分的政治司法制度和相当的物质生活条件)才可以考虑。(列宁是突破了马、恩的理论,错误地在一国之内建成了苏维埃政权,因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发表过批评,认为公社委员会应该及时进攻凡尔赛,并劫持法兰西银行的财产,这样做比“扣押一万名人质”更为有效。所幸公社来不及听取意见便流血失败了。如果真的如马、恩所建议那样(进攻凡尔赛,劫持银行),公社胜利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新政权,那怎样跟英美同时革命呢?又如何等待德国迎头赶上呢?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跨越工业化的门槛,更别提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有多大了。等待也不要紧,等一千年,进入理想世界也值呀。但是这些发展各不相同的国家如何相互等待,呼应往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景象,我觉得有点滑稽。
马克思曾经特别指出过,科隆(德国西部工商业重镇,我在德国买下的住房就离科隆市附近30公里)、伦敦和巴黎三角可以跳过无产阶级专政,进入共产主义。1920年列宁曾在《青年团的任务》里预言说“今天15岁的少年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离开列宁的预言已经一百年过去了,离开《共产党宣言》的预言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没有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原始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的人数正在减少,社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科技专业人员。当我离开中国,刚刚踏入德国社会的时候,也到当地的工厂里打工挣生活费。据我观察,这里的工人无论言语思想素质,都没有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么高。技术含量越低的岗位,工人的言语思想水平越一般。德国社会已经变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最富裕的和最穷困需要救济的阶层都很小,中间阶层则越来越大,中产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也比较有担当,关注国家事务,影响社会舆论。马克思从未做工务农,除了当过一两年编辑(《新莱茵报》和《德法年鉴》)以外,没有在企业或机关上过一天班,几乎没接触过真正的工人。到他家里来做客的往往是共运或工运的骨干,是工人队伍中的精英人物。他把工人队伍可笑地理想化了。
暴力理论和虚幻梦想
近期我又读了恩格斯《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有人说这是恩格斯的一篇政治遗嘱,发表这篇文章以后不久,1895年他就去世了。有人认为恩格斯在此文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斗争的方式应该改变,枪炮等热兵器已经更加精良,面对政府军的街垒巷战已经没有胜算,普选权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还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等等。文章发表后发生了原文是否被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删改的争议,经过马恩文献搜集整理专家梁赞诺夫的考证,现在已经不难读到恩格斯的原文。不过梁赞诺夫本人却被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都是第二国际的著名人物,也是曾经深得恩格斯信任的门生,伯恩斯坦更是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他们都痛感马、恩的暴力理论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于是勇敢地提出了修正意见。伯恩斯坦提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更是典型的学者,他跟列宁针锋相对,预言苏维埃政权没有民主,也必然寿命不长,早晚会变成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他倾心于普选权,多党制议会民主,一生期待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伯恩斯坦有一句话,意思是说,“终极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在国内时,觉得不好理解。来到德国,阅读了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才明白过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认为工人运动不需要虚无缥缈的共产理想。马克思的那一套理论反而让工人群众经常询问,何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情况。踏踏实实的通过议会抗争,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人阶级的权益,才是现实的成就。民主社会既不要血腥的暴力,也不要虚妄的幻想。联邦德国七十多年来,实现了全民医保,包括失业保险和老年护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所描述的无产者生活无保障的情况早就没有了。任何政党都不能再以这些内容做自己的理念和信条。
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年来是社会党国际的标杆,战后由勃兰特领导改组,1959年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教条,赢得广泛的社会(青年)认同,十年之内赢得大选,勃兰特出任总理,又一跪成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社民党也是德国第一大党,战后执政时间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
历史的真实
恩格斯的晚期文章并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暴力思想,只是想到议会普选也可以是一种活动手段而已。在1891年他还在埋怨20年前巴黎公社竟没有去打劫法兰西银行,如果占领了银行,比绑架一万名人质更加有效。马恩的这类言行都是恐怖暴力式的,而且至死都没有悔过和道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承认工人运动应该参与议会活动,可是他已经年迈力衰,没有任何相关的实践和理论贡献。相比之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摒弃暴力主张,顶着俾斯麦等反动政府的残酷打压,运用智慧和才能,积极展开议会抗争,不断地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同情,赢得了多项权力,保护女工,废除童工制度,保障工人安全和健康,中下层人民的子弟同等享受高等教育,乃至推动同性恋合法化,为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民主党对于他们的党史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也是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都是党所尊崇和纪念的先驱。同时也不否认,每位先驱人物也都有理论缺陷或人格瑕疵。第三国际的苏共和苏共扶植的中共则废黜百家,独尊马列。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反而是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历史地冷静地尊重历史。
我在青年时代读过一点马恩的著作,老年岁月再次涉猎,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思考和判断。我觉得马、恩的思想,剩余价值,理想社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无产者大联合、暴力革命、经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逻辑并不缜密,预言多无验证;带给各国人民的灾难,则远远大于他们的一点点学术贡献。而且正因为他们披着科学和理想的外衣,更加迷惑了众多青年和知识分子,掩盖了恐怖主义暴力本质,导致了二十世纪数以亿计的人民生灵涂炭。我的概括是这样的,当今的西方知识界谈马克思,多是不着边际(脱离了该理论的暴力主旨)的概念游戏,当今国内对马克思的吹捧,都是为领导人脸上贴金,玩拍马游戏。马克思主义已是一具尸居馀气的僵尸。
马恩只是因为列宁主义的暴力政权而享受了近百年的虚荣,一旦这类专制的保证覆灭以后,他们的面貌就将失去过度耀眼的浮光,泯然沉入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