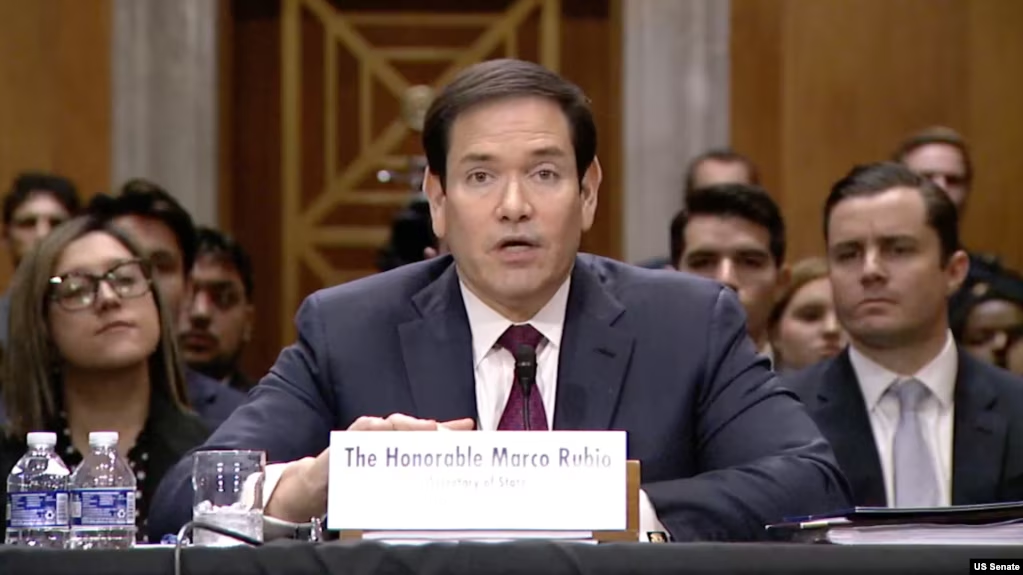当今社会,是一个以世界民主化为主旋律的后对抗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致使人类共同认可的普遍价值观跨出地缘疆域,突破了意识藩篱,汇合起各国文化,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的全球化思潮,堪为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同时,各种对抗全球化逆流也随之沉疴泛起,正在成为砥砺新文明时代潮流发展的反题。这是由社会发展的辩证逻辑使然的。
人类“类化”意识觉醒今日世界,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类自我分裂、相互对抗的旧文明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也使传统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受到挑战。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的觉醒-——人类“类”化意识,正作为一种全球化过程的哲学命题,在主权淡化、国界开放时代凸现出来。人类开始在21世纪的新文明起跑线上,超越党派分野,阶级阵线,民族自守与国家壁垒,以“类”的概念及话语体系来调整思维,反省历史,批判现实和创造未来。
所谓“类”的概念,也就是人类在彻底结束自我分裂与相互对抗的旧文明历史过程中,认知自身同属性的价值抽象。“类”的概念,等于人类的特定质料(自由意识与创新精神)加特定的实现形式(平等互利与协商合作)。人具有自由与创新的共同潜能,而这种潜能只有在平等与协商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以全面实现。由此可见,自由与民主,是作为人“类”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和潜能与实现的一种逻辑关系上的结果;是人类走过漫长苦难历程,感悟际间共同价值而形成观念上的理性提升。人是社会事实的主体。人类从自在的类存在向自为的类存在的不断类化发展过程中,由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时代,社会才能分娩出全新的文明。人们从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出发,以共同具有的自觉生命本能意识,用“利益共同性”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和发现世界联系与规律的立场,就会形成人类社会的“类”观念。
人是世界的核心。人权是一切社会权力之母。今天人类“类”意识的成熟,正在于它在价值判断上已经完成了“国际法高于国家法,人类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普遍价值高于特殊价值”的共识,即对人的普遍价值的尊重,已经超越了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形成了全球无疆界的主流思潮;而人类“类”意识的成熟,必将导致“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横扫东西,波及全球。
普世的人权观念就是承认人的共同性本质与平等资格是被先天授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自然的规定性。普世价值观之所以能被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在全世界范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原因就是相同的类本能、类理性。由于人类性相通,所以不同的人群才会有共认的价值标准评判是非。
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到人类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基于“类”这一身份而享有权利时,才会有人的同等权利意识的产生。从但丁提出“国家的基石是人权”观念,到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从西方国家的观念范畴扩展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至今,人权已成为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一面旗帜。
普世主义全球扩张所谓普世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结束相互分裂、相互对抗,走向经济全球化、政治世界化、文化共融时代,反映全人类“类”化意识全面觉醒所形成的全球观念;是在汇合不同文化过程中,将民主的价值观提升为普世模式或人类主义的新文明思潮。普世主义包含以下四层意思:
其一,普世主义是以新文明人本主义为道德理念的世界传播。所以它强调的是普遍观念和博爱主义的向善立场。它认为人类的道德都有向善与自由的统一性,认同所有社会制度的本质都应当是维护人的自由,守护向善的道德准则。
其二,普世主义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土壤,认为全球化是由“经济人”特性规定的自由市场的必然归宿,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全球化首先是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它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全球共同市场为基础,强调世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其三,普世主义以政治世界化为主要目标,推行人类民主制度与人权价值观的普世落实。民主制度如同资本扩张一样,会得到世界性的认同。普世主义认为,捍卫自由的民主制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正成为资本扩张全球化的又一翼——民主政治在世界化。
其四、普世主义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本位与民族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统一论的文化共融主义。普世主义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共融化,已经构成了一种后对抗时代全球认同的新文明价值体系。
新文明普世主义价值体系取向十分明确,就在于认为各国政府有限责任的核心,是尊重人类共同价值观,维护个体尊严与自由权利;放弃“主权至上”立场,裁减军费,保护环境和贯彻贸易自由主义。新文明普世主义思潮的政治特色就在于它的“非对抗性”。它主张价值多元,相互包容,即对一切价值都采取一视同仁的“豁达原则”,认为政府的立场是采取“价值中立主义”和奉行“不干预主义”,它较之强调“个人自主权”的传统自由主义比,更强调的是尊重、包容与豁达,因此更趋向共融性和普世认同性。
在当今现实中,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普世主义,已经构成了一个后对抗时代的价值体系——以自己的崭新语境,塑造后对抗时代全人类的新思维、新观念。这种思潮、观念上的更新,将借助全新的符号系统,即以更真实、贴切、开放的话语体系,来传达社会主体存在的自由倾向和客观要求,并通过摒弃传统对抗社会语境包围着的人类敌我意识,来构建符合人类自由属性的民主社会文化,从而实现世界政治文化模式上的转变。如“全球化”、“新文明”、“后对抗”、“人权至上”、“社群主义”、“政治世界化”等等新概念,已伴随着新文明普世主义新话语全球传播,而那些诸如“帝国主义”、“主权绝对论”、“不平等”、“阶级”、“民族斗争”等传统概念,已大大降低了其使用频率。
全球化已经导致了人类社会凸现出世界性视角:“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面对这种世界性的变化,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从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角度,对资本扩张世界化进行系统研究;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提出“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的主张。
国际社会宗教界更是从伦理角度对新文明时代做出了普世主义的回应。1893年世界第一次宗教议会大会后一百年,世界宗教人士于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这次大会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深刻反映了普世主义思潮的影响。宣言概括了人类面临的困境,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一种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建立又有赖于普世伦理。“我们所说的普世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该宣言主张,人类应“献身于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为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做出贡献的英国教授威德勒在谈及宣言的原则时强调,宣言“应该是人类中心的,而且,还必须是人类秩序中心的”。
除此之外,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对普世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已有知识与权威合法性的反省,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青睐,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使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全球理论”、“ 普世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从而与传统国家主义拉开了距离。普世主义的兴起,是一种趋向新文明形态发生的基本事实,其根源在于后对抗时代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这种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的内在动力,就是全球可以按统一技术与指令使用圆动工具创造财富与资本的现代价值增值机制全球扩张的必然逻辑,同时也在于人类“类”意识的成熟所导致“人权是世界和平基石”的国际社会新安全观。
新对抗逆流泛起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势不可当的同时,新文明普世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同任何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潮流一样,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新对抗逆流的种种非议与批判。这就如同资本在跨出国界进行世界性扩张的同时,招致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抵制与攻击一样。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内在辩证机理所决定的。不可否认,冷战结束的后对抗时代,在综合了世界性两极分裂的离心倾的同时,也刺激了被全球冷战深埋于政治分野之下的国家立场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复发。这就是世界性新对抗主义产生的土壤。
新对抗逆流不同于以强烈意识形态化为特征的传统对抗主义,而是一种以绝对国家概念与民族文化为本位,倡导绝对主权与大民族主义的“说不”立场为特征的反对和抵制全球化思潮。这种思潮产生的经济原因在于圆动工具全球化变革所带来的非民族中心化浪潮。许多民族主义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治不平等而大有失落感与恋旧情结,因而便在精神上亮起“新对抗主义”的旗帜。
反普世主义西方文化批评家杰姆逊就认为:全球化是多国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扩张而造就全球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英国学者汤林森也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导致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它威胁到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传统”文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源于法国的欧洲新右派对抗主义,则是以“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这场运动产生于欧洲的极右翼。欧洲新右派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怀有挑战现状的渴望,同时又摆脱了怀旧式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束缚。普世传播的新文明普世主义已经成为欧洲新右派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极右翼在许多国家的选举中都收获不断,尤其是法国、德国的共和党,比利时的佛拉芒方块党和奥地利的自由党都是如此。这些极右翼政党对内都主张民族认同高于其它一切认同,如阶级、种族和地方独立主义。这些政治力量也持有相似的对外政策立场,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欧洲统一。欧洲新右派强调,为了挑战普世化,需要对极右翼的观点进行调整、更新,以使欧洲新右派能够与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辩论其观点、并与左翼建立起反对普世主义的文化联盟。欧洲新右派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保持特殊性的权利,以及强调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以保持特殊性权利的原则来对抗普世主义。2011年7月22日,挪威政治极端分子安德斯先在该国首都奥斯陆军政府机构云集的地区引爆炸弹,造成7人遇难。紧接着,此人身穿警服窜入一座海上小岛,对着参加夏令营活动的青少年疯狂射击,造成至少80人丧生,制造了挪威几十年来发生的最大惨案,并震惊了全世界,为欧洲新对抗主义极端化的危害增添了最血腥的一例。
记得冷战刚刚结束时,日里诺夫斯基就成为“大俄罗斯民族失落感”的象征,扬言要使“汉普蒂邓普帝”重圆,到“印度洋洗脚”。在东亚,日本的国会右翼议员石原慎三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作为另一种新对抗主义的旗手曾联合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敢说“不”》一书,不赞同西方文明,声称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白种人所开创的近代文化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应挺起腰来,对自己要有自豪感。为此日本要敢于对美国说“NO”。该书出版后引起美国朝野情绪反弹,为此石原慎三郎不仅又与他的伙伴合写了《日本就是敢说“不”》,而且自己推出了《日本坚决敢说“不”》一书,扬言只有日本可以治美国的病,发起了日本对美国没有硝烟和军事竞赛的民族化情绪对抗战。
在中国,自从90年代以来,就有5次反普世主义发展的言论高涨。第一次是“6、4”风波后,因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真得“狼来了”一文而捞取了不少的政治资本的所谓青年学者,曾以“文化本体论”为武器抵制西方文明,并在一次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对话时声称: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面临空前挑战时期。中、日、俄可能形成三种对抗。第二次发生在94年后,中国理论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例如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对已经成为世界化的新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而模仿日本敢说“不”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为代表的反普世主义发展言论,则推动了第3次民间民族对抗“说不”的“情感选择”。那些青年自称“新义和团”,声称“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攻击美国,漫骂日本,排斥西方,扬言对台“无忌准备打仗”,直言“对抗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第4次新对抗逆流再起发生于最近几年。三年前有位御用学者抨击“普世主义”说:“剥去了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今中国无论官方民间,乃至知识界都还大有人在,网络媒体上中国愤青们的新对抗主义言论更是随处可见。第5次发生于眼下来自中南海的“两个绝不”与“六个不搞”为代表的反普世价值舆论战。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前,官方正在借90周年庆典,“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风潮”,企图借还魂整合“中国模式”的红色软实力,与世界埋葬阶级文化的新文明主流争夺语话权。中南海如此寄希望于在一个完全依赖 GDP 增长支持执政权力的政治结构里,靠启动毛左势力“唱红中国”与世界文明社会唱对台,无论如何也发展不出新的统治正当性。
结论当下,中国大陆各式各样的新对抗派别与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新对抗主义,正在汇成一种抗拒新文明价值观普世传播的共同逆流,撞击着后对抗时代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敏感神经,构成了时代潮流正面运动的反题。沃勒斯坦先生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写到:“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而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普世主义的顽强生命力不仅由于它体现了时代发展的主题,反映了人类进步的要求,更在于它能够迎接任何挑战,消解任何阻力,并在回应各种压力激励的过程中,推进新文明价值观的普世落实。
注:本作者早在1998年发表的《新文明宣言》一文中首次提出人类“类化”意识概念,并在《民主论坛》上首发了《新文明“类化”意识的觉醒——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一文,之后又多次发文深化此论。2000年本作者又在新著《走向新文明——后对抗时代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新文明“类化”意识理论;接着2004年撰写《发生之发现原理——东方圆和新哲学》一书的绪论中,进一步提出了本书作为人类哲学,是一种旨在追求人的类本性与类意识的“人类主义”新学问,并揭示了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原理。
人类“类化”意识觉醒今日世界,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人类自我分裂、相互对抗的旧文明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也使传统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受到挑战。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的觉醒-——人类“类”化意识,正作为一种全球化过程的哲学命题,在主权淡化、国界开放时代凸现出来。人类开始在21世纪的新文明起跑线上,超越党派分野,阶级阵线,民族自守与国家壁垒,以“类”的概念及话语体系来调整思维,反省历史,批判现实和创造未来。
所谓“类”的概念,也就是人类在彻底结束自我分裂与相互对抗的旧文明历史过程中,认知自身同属性的价值抽象。“类”的概念,等于人类的特定质料(自由意识与创新精神)加特定的实现形式(平等互利与协商合作)。人具有自由与创新的共同潜能,而这种潜能只有在平等与协商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以全面实现。由此可见,自由与民主,是作为人“类”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和潜能与实现的一种逻辑关系上的结果;是人类走过漫长苦难历程,感悟际间共同价值而形成观念上的理性提升。人是社会事实的主体。人类从自在的类存在向自为的类存在的不断类化发展过程中,由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时代,社会才能分娩出全新的文明。人们从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出发,以共同具有的自觉生命本能意识,用“利益共同性”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和发现世界联系与规律的立场,就会形成人类社会的“类”观念。
人是世界的核心。人权是一切社会权力之母。今天人类“类”意识的成熟,正在于它在价值判断上已经完成了“国际法高于国家法,人类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普遍价值高于特殊价值”的共识,即对人的普遍价值的尊重,已经超越了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形成了全球无疆界的主流思潮;而人类“类”意识的成熟,必将导致“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横扫东西,波及全球。
普世的人权观念就是承认人的共同性本质与平等资格是被先天授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自然的规定性。普世价值观之所以能被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在全世界范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原因就是相同的类本能、类理性。由于人类性相通,所以不同的人群才会有共认的价值标准评判是非。
人权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到人类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基于“类”这一身份而享有权利时,才会有人的同等权利意识的产生。从但丁提出“国家的基石是人权”观念,到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从西方国家的观念范畴扩展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至今,人权已成为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一面旗帜。
普世主义全球扩张所谓普世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结束相互分裂、相互对抗,走向经济全球化、政治世界化、文化共融时代,反映全人类“类”化意识全面觉醒所形成的全球观念;是在汇合不同文化过程中,将民主的价值观提升为普世模式或人类主义的新文明思潮。普世主义包含以下四层意思:
其一,普世主义是以新文明人本主义为道德理念的世界传播。所以它强调的是普遍观念和博爱主义的向善立场。它认为人类的道德都有向善与自由的统一性,认同所有社会制度的本质都应当是维护人的自由,守护向善的道德准则。
其二,普世主义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土壤,认为全球化是由“经济人”特性规定的自由市场的必然归宿,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全球化首先是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它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全球共同市场为基础,强调世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其三,普世主义以政治世界化为主要目标,推行人类民主制度与人权价值观的普世落实。民主制度如同资本扩张一样,会得到世界性的认同。普世主义认为,捍卫自由的民主制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正成为资本扩张全球化的又一翼——民主政治在世界化。
其四、普世主义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本位与民族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统一论的文化共融主义。普世主义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共融化,已经构成了一种后对抗时代全球认同的新文明价值体系。
新文明普世主义价值体系取向十分明确,就在于认为各国政府有限责任的核心,是尊重人类共同价值观,维护个体尊严与自由权利;放弃“主权至上”立场,裁减军费,保护环境和贯彻贸易自由主义。新文明普世主义思潮的政治特色就在于它的“非对抗性”。它主张价值多元,相互包容,即对一切价值都采取一视同仁的“豁达原则”,认为政府的立场是采取“价值中立主义”和奉行“不干预主义”,它较之强调“个人自主权”的传统自由主义比,更强调的是尊重、包容与豁达,因此更趋向共融性和普世认同性。
在当今现实中,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普世主义,已经构成了一个后对抗时代的价值体系——以自己的崭新语境,塑造后对抗时代全人类的新思维、新观念。这种思潮、观念上的更新,将借助全新的符号系统,即以更真实、贴切、开放的话语体系,来传达社会主体存在的自由倾向和客观要求,并通过摒弃传统对抗社会语境包围着的人类敌我意识,来构建符合人类自由属性的民主社会文化,从而实现世界政治文化模式上的转变。如“全球化”、“新文明”、“后对抗”、“人权至上”、“社群主义”、“政治世界化”等等新概念,已伴随着新文明普世主义新话语全球传播,而那些诸如“帝国主义”、“主权绝对论”、“不平等”、“阶级”、“民族斗争”等传统概念,已大大降低了其使用频率。
全球化已经导致了人类社会凸现出世界性视角:“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面对这种世界性的变化,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从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角度,对资本扩张世界化进行系统研究;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提出“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的主张。
国际社会宗教界更是从伦理角度对新文明时代做出了普世主义的回应。1893年世界第一次宗教议会大会后一百年,世界宗教人士于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这次大会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深刻反映了普世主义思潮的影响。宣言概括了人类面临的困境,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一种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建立又有赖于普世伦理。“我们所说的普世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该宣言主张,人类应“献身于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为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做出贡献的英国教授威德勒在谈及宣言的原则时强调,宣言“应该是人类中心的,而且,还必须是人类秩序中心的”。
除此之外,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对普世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已有知识与权威合法性的反省,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青睐,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使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全球理论”、“ 普世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从而与传统国家主义拉开了距离。普世主义的兴起,是一种趋向新文明形态发生的基本事实,其根源在于后对抗时代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这种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的内在动力,就是全球可以按统一技术与指令使用圆动工具创造财富与资本的现代价值增值机制全球扩张的必然逻辑,同时也在于人类“类”意识的成熟所导致“人权是世界和平基石”的国际社会新安全观。
新对抗逆流泛起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势不可当的同时,新文明普世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同任何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潮流一样,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新对抗逆流的种种非议与批判。这就如同资本在跨出国界进行世界性扩张的同时,招致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抵制与攻击一样。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内在辩证机理所决定的。不可否认,冷战结束的后对抗时代,在综合了世界性两极分裂的离心倾的同时,也刺激了被全球冷战深埋于政治分野之下的国家立场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复发。这就是世界性新对抗主义产生的土壤。
新对抗逆流不同于以强烈意识形态化为特征的传统对抗主义,而是一种以绝对国家概念与民族文化为本位,倡导绝对主权与大民族主义的“说不”立场为特征的反对和抵制全球化思潮。这种思潮产生的经济原因在于圆动工具全球化变革所带来的非民族中心化浪潮。许多民族主义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治不平等而大有失落感与恋旧情结,因而便在精神上亮起“新对抗主义”的旗帜。
反普世主义西方文化批评家杰姆逊就认为:全球化是多国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扩张而造就全球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英国学者汤林森也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导致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它威胁到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传统”文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源于法国的欧洲新右派对抗主义,则是以“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这场运动产生于欧洲的极右翼。欧洲新右派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怀有挑战现状的渴望,同时又摆脱了怀旧式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束缚。普世传播的新文明普世主义已经成为欧洲新右派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极右翼在许多国家的选举中都收获不断,尤其是法国、德国的共和党,比利时的佛拉芒方块党和奥地利的自由党都是如此。这些极右翼政党对内都主张民族认同高于其它一切认同,如阶级、种族和地方独立主义。这些政治力量也持有相似的对外政策立场,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欧洲统一。欧洲新右派强调,为了挑战普世化,需要对极右翼的观点进行调整、更新,以使欧洲新右派能够与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辩论其观点、并与左翼建立起反对普世主义的文化联盟。欧洲新右派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保持特殊性的权利,以及强调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以保持特殊性权利的原则来对抗普世主义。2011年7月22日,挪威政治极端分子安德斯先在该国首都奥斯陆军政府机构云集的地区引爆炸弹,造成7人遇难。紧接着,此人身穿警服窜入一座海上小岛,对着参加夏令营活动的青少年疯狂射击,造成至少80人丧生,制造了挪威几十年来发生的最大惨案,并震惊了全世界,为欧洲新对抗主义极端化的危害增添了最血腥的一例。
记得冷战刚刚结束时,日里诺夫斯基就成为“大俄罗斯民族失落感”的象征,扬言要使“汉普蒂邓普帝”重圆,到“印度洋洗脚”。在东亚,日本的国会右翼议员石原慎三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作为另一种新对抗主义的旗手曾联合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敢说“不”》一书,不赞同西方文明,声称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白种人所开创的近代文化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应挺起腰来,对自己要有自豪感。为此日本要敢于对美国说“NO”。该书出版后引起美国朝野情绪反弹,为此石原慎三郎不仅又与他的伙伴合写了《日本就是敢说“不”》,而且自己推出了《日本坚决敢说“不”》一书,扬言只有日本可以治美国的病,发起了日本对美国没有硝烟和军事竞赛的民族化情绪对抗战。
在中国,自从90年代以来,就有5次反普世主义发展的言论高涨。第一次是“6、4”风波后,因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真得“狼来了”一文而捞取了不少的政治资本的所谓青年学者,曾以“文化本体论”为武器抵制西方文明,并在一次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对话时声称: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面临空前挑战时期。中、日、俄可能形成三种对抗。第二次发生在94年后,中国理论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例如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对已经成为世界化的新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而模仿日本敢说“不”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为代表的反普世主义发展言论,则推动了第3次民间民族对抗“说不”的“情感选择”。那些青年自称“新义和团”,声称“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攻击美国,漫骂日本,排斥西方,扬言对台“无忌准备打仗”,直言“对抗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第4次新对抗逆流再起发生于最近几年。三年前有位御用学者抨击“普世主义”说:“剥去了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今中国无论官方民间,乃至知识界都还大有人在,网络媒体上中国愤青们的新对抗主义言论更是随处可见。第5次发生于眼下来自中南海的“两个绝不”与“六个不搞”为代表的反普世价值舆论战。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前,官方正在借90周年庆典,“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风潮”,企图借还魂整合“中国模式”的红色软实力,与世界埋葬阶级文化的新文明主流争夺语话权。中南海如此寄希望于在一个完全依赖 GDP 增长支持执政权力的政治结构里,靠启动毛左势力“唱红中国”与世界文明社会唱对台,无论如何也发展不出新的统治正当性。
结论当下,中国大陆各式各样的新对抗派别与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新对抗主义,正在汇成一种抗拒新文明价值观普世传播的共同逆流,撞击着后对抗时代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敏感神经,构成了时代潮流正面运动的反题。沃勒斯坦先生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写到:“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而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普世主义的顽强生命力不仅由于它体现了时代发展的主题,反映了人类进步的要求,更在于它能够迎接任何挑战,消解任何阻力,并在回应各种压力激励的过程中,推进新文明价值观的普世落实。
注:本作者早在1998年发表的《新文明宣言》一文中首次提出人类“类化”意识概念,并在《民主论坛》上首发了《新文明“类化”意识的觉醒——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一文,之后又多次发文深化此论。2000年本作者又在新著《走向新文明——后对抗时代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新文明“类化”意识理论;接着2004年撰写《发生之发现原理——东方圆和新哲学》一书的绪论中,进一步提出了本书作为人类哲学,是一种旨在追求人的类本性与类意识的“人类主义”新学问,并揭示了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