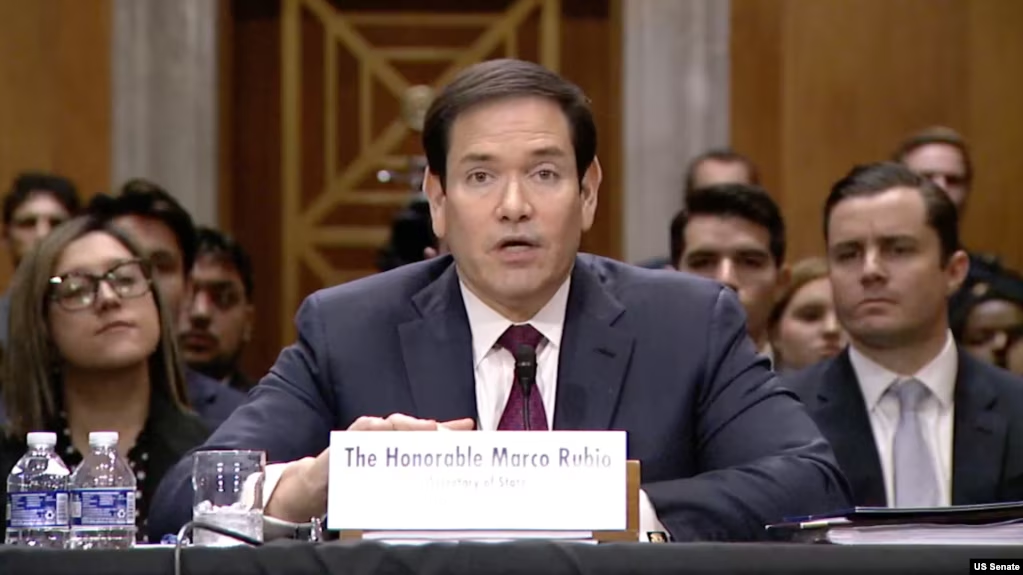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一个历史密码
面对极度不公与转型需求迫切的社会压力,中共最高权力层重新祭出“舆论监督”的法宝并且确实有一些收效。尽管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的较力年复一年,但也确实能够看到争执中言论自由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而是主要集中在民权的集体行动方面。当局避试图以更柔性的手段来管控互联网,以达到维稳的基本效果,即那种“让真相跑在谣言前头”的效果。诚如对此种机制的描述所云,“相信是被由下而上的‘倒逼’机制逼出来的”【注1】。作为一种有益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倒逼机制源于民众对知情权的诉求,进而是当局“分级阅读”治术的历史危机。
分级阅读作为产生于革命时期的制度安排,在中共政权建立后还在发挥作用,以至于到今天尚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或各自单行的两种法律。确切的分级阅读制度安排出现延安时期,它由一套完整的原则体系来体现,而最为经典的有两条:(一)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编制《参考消息》,“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注2】;(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供给,“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至于一般普通百姓,“就没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他的消息了”【注3】。此种做法有类于西方社会活版印刷机出现之前的《圣经》资源控制,控制集团垄断了《圣经》解释权与抄写许可;更远一些地看,是中国历史上神喻传统的遗传,神喻文化掌握集团垄断了对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解释。稍后,神喻传统渐变为古老且特定的舆论监督形式,因而,“从神喻传统到史鉴传统是中文传播的媒介权力的重要演变”【注4】。
一、传统困境:监督变为附庸
在中华政治史上或文化共同体里面,神喻传统与最终影响西方的东方基督教有着许多相似性。中华的贞人集团为皇权进行以卜筮为专业的宗教活动,而不得不服务于投身所依势力的犹太先知(如约瑟之在埃及)则进行专业的解梦,以至于到耶稣时代,当权者(如尼哥底姆)还向新先知耶稣求问哲理。这些不烦引述《圣经》原例而是在于说明高级信息消费是重要文明传承的内在要素,而且越具权势的集团就越有内卷的愿望,即是说这种消费是贵族化的。
中华之有史鉴文化即贞人集团完成了向史鉴集团的转化,确实是重大历史演进。但是,信息消费的贵族化仍然没有改变。简单地说,左史记言与右史记事所形成的重大信息(当然也是高质的政治信息)不可能为百姓所知晓,只有到一个王朝消失后,后来的追记(作史)才能有选择地被“事后”知晓,从而形成广义的镜鉴。在这个意义上,放诸现代环境,历史知情权与就成了一项人权。
左记言、右记史的操作规则对每个历史当下的统治者都是一种舆论监督,尽管那种舆论监督还远未具近代报刊之功能。但无疑是:(一)当下统治者无权翻看所记,因为监督权力从伦理上与行政权力是平行的;(二)即便违规翻看,也难以改变所记,经典是董狐直笔不阿的故事;(三)即便宜是秦以后,翻看与改写都成了当下统治者的应有权力,但还是没法取消体制内的谏言制度。在另一端,监督不断地往附庸化趋近,或者说秦以后每个朝代只是监督行政权力的附庸程度的不同而已,或者说史鉴非现时性【注5】使行政权力没有太多的必要顾忌自己的作为:“体制内儒家言论经典性记载(如流传于后世的名奏)往往推崇三代之治,而君王们对那种榜样性版本不是认为远不可考而难尊之,就是阳奉阴违。如果他们(受谏的君王们)一定要效法史上的‘史鉴’,大多是对自己有益的,如封禅之流传、祭孔之继承性宣示行为。”【注6】
监督沦为附庸在当代中国史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目前最高当局又把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话重新提出来,用于警示统治体系里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以使其在行为上自我约束。然而,这个史鉴新版几乎没法摆脱哈罗德•D.拉斯韦尔(1936)著名的行为政治学论断:“一种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生存下去的,不需要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而煞费苦心的时候,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的前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注7】。
二、单一权力:苏联影响仍在
中华政治史在二十世纪进了灾难性的阶段,舆论监督不仅没有基本上的狭义古典作用,还沦落为政治迫害的帮凶。即便不说影响至今且有复炽之势的“大批判”语言暴力习性,仅看政治话语权所产生的公信力后果,就足以让人们惊惧。统治集团或因一时之发而欢欣于强势,但这种伤害的远期成本之大几乎使他们无力承担。比方说,由体育名人转成文化产业经营者的邓亚萍(2010)曾说“《人民日报》从来没出过假新闻”【注8】,时隔两年,被吹捧对象《人民日报》则自己间接承认出过假新闻,是谓“新的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讲实性”【注9】。这种矛盾出现原因固然是由于政治治理周期的变化,即人们所说的习李新政代替了胡温新政,但是,它却明确地证明了舆论监督的沦落,一如吴予敏(2001)所说,“如果媒介权力失去了道德优越性和职业的独立性,它本身就会比其他权力更加邪恶”【注10】。
何以会出现史鉴舆论监督的失败以及更细节的话语失真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即取中共革命到建政、由建政而建设的内在演化过程作为观测区间,那么,不难发现失败与失真导因于苏联体制,即追求政治权力的单一性。简单地说,党控新闻是党控政权的必然结果。在苏联政治初期,列宁为实现单一政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排除了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制约。在一份政治宣言中,他公然称:“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人民委员会名单,而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的名单。”【注11】
中共建政之初虽未直接实现单一权力而有协商名义下的议政党派,但在新闻管制方面,准确实施了单一权力计划。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报纸“从民办到党管”【注12】的历程是一个经典。在这个经典发生之前,基于新闻业维续之必需的商业先机遭到了重挫【注13】。换言之,新闻业的商业内核已经被政治内核所取代,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出现邓亚萍之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子矛子盾:善意欺骗固化
上海报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遭遇,证明单一权力统治比国民党时期的新闻自由还要差,尽管在革命时期作为反对党的中共从未放弃过对政府的言论批判。比如,《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情况下)社论要求国民党“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以及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注14】。时至今日,中共当年的民主(特别是要求言论自由)主张已经不断地被网络舆论当做“反面教材”来指斥【注15】,其道德逻辑就是中共是个一贯行骗的政治组织。其在建政前的一切民主诉求都是政治表演。
就中国近晚传统的原因看,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与建政之后的表现,尽管明显表示出目的第一的企图,但自袁世凯陷入威二主张的困局以来,民主政治与国民素质之关系确实是至今未解的难题【注16】。这个难题更多地源于传统哲学浅薄而致的思维缺陷,其结果是政治科学探索的懒惰。因此,目的第一的企图可视为善意的欺骗。而最大的不幸是: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新国家,在权力系统里面都不可避免进入革命专政向反动专制堕落的逻辑,特权泛滥成为社会特征,最终使善意的欺骗走上假戏真演的路子。南斯拉夫首先没有例外于此种堕落,而后是波兰、苏联等一大串国家,中国当然也没能例外之。
当然,善意固化即假戏真演于共产党政权建政后,不惟中共本身要承接威二主张困局之负资产,还在于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单一权力设想有着强大的基督教(广义的含新教、天主、东正三支系)背景支持。尽管所有共产党政权(乃至未能获取政权的议会党)都是无神论即非宗教意识形态,但是基督教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是西方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历史与政治哲学资源,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不可能实质性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更为决定其命运的因素是:基督教迅速现代化后(如解放神学之出现以及跨宗教教会形成),共产党还在加尔文主义的单一权力魔咒下无法解脱。无须讳言,努力建立单一权力的列宁就是十六世纪中后期加尔文的翻版,而所有的试图挑战单一权力的思想家都是塞维特斯,尽管未必人人遭遇火刑【注17】。同时,列宁主义下的所有政治整肃运动也无疑是当年加尔文肃清日内瓦的翻版,“当‘正义’完成时,全城留下的唯一政党是加尔文的私党”【注18】。
四、激烈反对:宗教精神动力
固化了的善意欺骗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现象,因此世界上最激烈的思想改革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宗教领域内。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被历史学家特别是神学背景的历史学家所夸大,与之对抗的塞维特斯之激烈仍不容忽视。其之激烈,以至于同情他的后世作家斯•茨威格也不由地将他与小说人物唐•吉诃德相提并论。在更长的历史上看,塞维特斯有(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卡斯特利奥)显然不是特例,仍是发生在十六世纪但影响远没塞维特斯事件为大的意大利的麦诺齐奥事件亦是之。
麦诺齐奥以不承上帝创世而犯罪并被处死,但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两大诱因:第一,社会内部不断地产生反对单一权力的力量,他的“胡言乱语”(如出自奶酪的蛆虫变成天使)与塞维特斯数百页之巨的著作没本质的区别,都是追求激烈变革,享有一个信息供给更充分、信息流动更畅通的世俗结果;第二,新技术出现与宗教改革相得益彰【注19】,对单一权力形成了巨大的破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因此而碰撞,碰撞更加大了信息流动的乘数规模。
反对单一权力作为具有宗教改革精神的现实抗争,存在于共产党政权的所有国家,不管规模大小与形式如何(如街头运动与地下教会之共存),它们都在起作用。时过二十四年,中国当代社会最大的反对单一权力运动,不仅仍是社会政治的不易中心话题之一,而且它具有转型“核能”力量。首先,“八九•六四”是一切起于内部改革诉求的“教派冲突”,结果是原教旨社会主义取得政治胜利,自由主义一方在政治上失败但获得了体制外的远期道义认可——赵紫阳(作为中国版的塞维特斯,尽管没丢命)于今成为底层维权力量的“神学”符号即是证明;其次,革命专政堕落为反动专制的社会压迫性后果已经难以令人承受(表面是通胀即物价问题)的程度,由此也引起正统革命精英之政治生存与新生底层庞大群之生活生存的冲突,造成社会运动在所难免;再次,这场源于体制内“宗教改革”的社会冲突对一个传统而未解决的信息等级问题的显性化起了巨大作用。
结语:失败的反抗亦意义深远
由分级阅读、单一权力、“洪宪改良”暨威二主张负遗产混合而成的信息等级问题,就是新闻出版立法问题。公平地说,在“八九•六四”事件发生之前即胡耀邦逝世之前,中共高层已在推进该方面改革。比如说,1987年7月出了新闻出版法送审稿,1989年1月又出了新闻与立法各自单行的草案。此被非常专业的学者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闻立法工作成果结晶【注20】。不过,这类的立法本该在毛统治结束后马上研议,估计是经济难题压在头上,改革权威邓小平尚没意识到这场补课绝不亚于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也由于补课太晚且立法过程的拖沓或有明显反对(如陈云所讲随意控制【注21】),以至于信息等级问题成了“八九•六四”事件过程中一个当局无法绕开的话题。可惜的是,研究该事件的权威们尚未对此给予重大关注。现在不妨根据正统的官方资料(1989)进行描点:
(一)4月29日,《世界经济导报》因刊登19日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内容而被上海市委整顿【注22】;意味着中共党内规则可行使新闻审查的法律功能。
(二)4月30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首都高校学生对话,否定中国有新闻检查制度,更不会出现报纸“开天窗”现象,尤其讲道:“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草拟新闻法、出版法,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今年有可能拿出草案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注23】。
(三)6月30日,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做平叛报告,再次提到上海《世界经济导报》4月19日的座谈会(合办者有《新观察》杂志社),指责该座谈会“为反自由化‘翻案’”【注24】。
这三个点准确地证明了体制内基于反对等级阅读暨信息等级制度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袁木技巧高超的说谎已钙化为历史,背景问题“要求新闻说真话是学生最强烈的要求之一”无疑是“八九•六四”留下的“核能”矿区。在此后二十四年的历史中,一方面,新闻说谎变成“反正我信”式的官方自言自语,而饱受民间诟病,以至于体制内重提新闻出版立法的诉求于今再度发出:另一方面,从袁木的无审查之说到邓亚萍无假新闻之判,不仅被体制的言说技巧自己证伪(死),而且,维稳式新闻管制在网络社交平台勃兴的今天已经全面破产,尽管它还以某种形式顽固地存在【注25】。整个统治集团自“八九•六四”之后的二十四年里,所言越伪,越证明事件过程中反对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度的诉求越有历史担当;所行越谬,越证明事件过程中打破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的行为越有现实责任。可以说,在大历史视角下,中国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的启动恰恰始自于二十四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事件。
2013年4月初构思,中旬备齐主要参考文献(书目);4月下旬至5月初,续补报刊资料;5月4日至6日初稿,7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4月5日文章,“让真相跑在谣言前头”(作者:沈泽玮);新华社《参考消息》4月8日转刊,题目未变,第15版〈观察中国〉。
[2]&[3]参见《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8月号,“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作者:孙旭培)。
[4]参见《读书》杂志2001年3月号,“帝制中国与媒介权力”(作者:吴予敏);亦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舆论监督的历史困境”,2013年5月5日,原文为2002年狱中读书笔记。
[5]关于这点可见我的[4]所指博文。
[6]同[5]。
[7]参见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汉译本,杨昌裕译),P19;杨译版本:商务印书馆,1992(2005年第5次印刷)。
[8]参见深圳广电集团资讯(中国时刻)2010年12月16日报道,“邓亚萍称《人民日报》六十二年‘没有假新闻’引起起哗然”。
[9]参见新浪新闻2013年1月2日转引《南方日报》报道,“《人民日报》改版称新的一年努力说真话”。
[10]同[4]引吴予敏文章。
[11]同[2]指杂志,2013年2月号,“契卡:建立清一色政府的工具——契卡成立新说”(作者:闻一)。
[12]参见[4]指杂志,2012年4月号,同题文章(作者:张济顺)。
[13]同[12],文章援引著名报人徐铸成(《文汇报》经营者)的说法:“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做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
[14]同[2]。
[15]到本文写作时,我以品质(而非数量)标志所做的微博统计,当中的“重头微博”仍显示出自由学者暨良心公知对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观点的对比性关注,即试图用历史原证来促使当局清醒。比如,徐昕(http://t.163.com/justice)在2013年5月4日引述《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社论:“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子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16]关于袁世凯第一个面对的民主政治与国民素质的难题,可见我对“洪宪改良”的政治学分析。两篇拙文:(一)“多党制被抑制的历史考察——从古德诺事件到贝尔现象”,载于《零八宪章月刊》网站,2013年4月1日,亦可见我的网易博客(4月3日);(二)“威二主张翻版的现实解析——既得利益决定政权过渡性质”,同前网站4月16日,博客亦4月16日。
[17]就塞维特斯事件的肇因来说,它也是一个广义的分级阅读制度下的事件,至少也是标准的言论自由事件。他因反对附加教义(而非《圣经》原本的)三位一体,写了《基督教的恢复》(1553)一书,因此不见容于天主教与新教两方,终在同年被日内瓦的加尔文改革派判处火刑。事件描述可见斯•茨威格(1936)《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史实》(汉译本,赵台安、赵振尧译),P99-143(第五、六两章);两赵译本:三联书店,1986。
此外,我本人是可以归为文化基督徒的那类信仰者,且在政治学术研究中高度关注信仰自由暨反对来自政权的强行干预(宗教事务),但我从来不否认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残酷性与非人性,也秉持整个人类不存在唯一神宗教的宗教哲学观点。
[18]同[17]引书,P204。
[19]意大利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在研究麦诺齐奥事件的专著(1982)《奶酪与蛆虫》中,指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发生碰撞,宗教改革与活版印刷术发明有着重要促成意义。转引自《读书》杂志2001年6月号,“小人物和大时代”(作者:李霞),是为《奶酪与蛆虫》一书的书评。
[20] 同[2]指杂志,2012年2月号,“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作者:孙旭培)。此文在前,[2]文在后,同为一个作者且关注同质主题,因此,本文中称其为“非常专业的学者”并不为过。
[21]陈云曾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出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引文出处同[20],但原文未具该说法的时间。
[22]参见乔初编《戒严令发布之前:4.15-5.20动乱大事记》,P17;乔编版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23]同[22],P102。
[24]同[22],P172。
[25]此类的“某种方式”一方面说明袁木所掩饰的新闻审查制度存在,另一方面,“开天窗”虽未得到任何一家报刊的证实,但是隶属中共党权体系的宣传部门不时向媒体直接下达方向性指令以至某些“选题不能做”确是真实存在的。参见[20]文章里所列编辑人员的日记资料。
引言:一个历史密码
面对极度不公与转型需求迫切的社会压力,中共最高权力层重新祭出“舆论监督”的法宝并且确实有一些收效。尽管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的较力年复一年,但也确实能够看到争执中言论自由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而是主要集中在民权的集体行动方面。当局避试图以更柔性的手段来管控互联网,以达到维稳的基本效果,即那种“让真相跑在谣言前头”的效果。诚如对此种机制的描述所云,“相信是被由下而上的‘倒逼’机制逼出来的”【注1】。作为一种有益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倒逼机制源于民众对知情权的诉求,进而是当局“分级阅读”治术的历史危机。
分级阅读作为产生于革命时期的制度安排,在中共政权建立后还在发挥作用,以至于到今天尚没有一部《新闻出版法》或各自单行的两种法律。确切的分级阅读制度安排出现延安时期,它由一套完整的原则体系来体现,而最为经典的有两条:(一)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编制《参考消息》,“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注2】;(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供给,“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至于一般普通百姓,“就没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他的消息了”【注3】。此种做法有类于西方社会活版印刷机出现之前的《圣经》资源控制,控制集团垄断了《圣经》解释权与抄写许可;更远一些地看,是中国历史上神喻传统的遗传,神喻文化掌握集团垄断了对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解释。稍后,神喻传统渐变为古老且特定的舆论监督形式,因而,“从神喻传统到史鉴传统是中文传播的媒介权力的重要演变”【注4】。
一、传统困境:监督变为附庸
在中华政治史上或文化共同体里面,神喻传统与最终影响西方的东方基督教有着许多相似性。中华的贞人集团为皇权进行以卜筮为专业的宗教活动,而不得不服务于投身所依势力的犹太先知(如约瑟之在埃及)则进行专业的解梦,以至于到耶稣时代,当权者(如尼哥底姆)还向新先知耶稣求问哲理。这些不烦引述《圣经》原例而是在于说明高级信息消费是重要文明传承的内在要素,而且越具权势的集团就越有内卷的愿望,即是说这种消费是贵族化的。
中华之有史鉴文化即贞人集团完成了向史鉴集团的转化,确实是重大历史演进。但是,信息消费的贵族化仍然没有改变。简单地说,左史记言与右史记事所形成的重大信息(当然也是高质的政治信息)不可能为百姓所知晓,只有到一个王朝消失后,后来的追记(作史)才能有选择地被“事后”知晓,从而形成广义的镜鉴。在这个意义上,放诸现代环境,历史知情权与就成了一项人权。
左记言、右记史的操作规则对每个历史当下的统治者都是一种舆论监督,尽管那种舆论监督还远未具近代报刊之功能。但无疑是:(一)当下统治者无权翻看所记,因为监督权力从伦理上与行政权力是平行的;(二)即便违规翻看,也难以改变所记,经典是董狐直笔不阿的故事;(三)即便宜是秦以后,翻看与改写都成了当下统治者的应有权力,但还是没法取消体制内的谏言制度。在另一端,监督不断地往附庸化趋近,或者说秦以后每个朝代只是监督行政权力的附庸程度的不同而已,或者说史鉴非现时性【注5】使行政权力没有太多的必要顾忌自己的作为:“体制内儒家言论经典性记载(如流传于后世的名奏)往往推崇三代之治,而君王们对那种榜样性版本不是认为远不可考而难尊之,就是阳奉阴违。如果他们(受谏的君王们)一定要效法史上的‘史鉴’,大多是对自己有益的,如封禅之流传、祭孔之继承性宣示行为。”【注6】
监督沦为附庸在当代中国史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以至于目前最高当局又把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话重新提出来,用于警示统治体系里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以使其在行为上自我约束。然而,这个史鉴新版几乎没法摆脱哈罗德•D.拉斯韦尔(1936)著名的行为政治学论断:“一种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生存下去的,不需要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而煞费苦心的时候,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的前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注7】。
二、单一权力:苏联影响仍在
中华政治史在二十世纪进了灾难性的阶段,舆论监督不仅没有基本上的狭义古典作用,还沦落为政治迫害的帮凶。即便不说影响至今且有复炽之势的“大批判”语言暴力习性,仅看政治话语权所产生的公信力后果,就足以让人们惊惧。统治集团或因一时之发而欢欣于强势,但这种伤害的远期成本之大几乎使他们无力承担。比方说,由体育名人转成文化产业经营者的邓亚萍(2010)曾说“《人民日报》从来没出过假新闻”【注8】,时隔两年,被吹捧对象《人民日报》则自己间接承认出过假新闻,是谓“新的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讲实性”【注9】。这种矛盾出现原因固然是由于政治治理周期的变化,即人们所说的习李新政代替了胡温新政,但是,它却明确地证明了舆论监督的沦落,一如吴予敏(2001)所说,“如果媒介权力失去了道德优越性和职业的独立性,它本身就会比其他权力更加邪恶”【注10】。
何以会出现史鉴舆论监督的失败以及更细节的话语失真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即取中共革命到建政、由建政而建设的内在演化过程作为观测区间,那么,不难发现失败与失真导因于苏联体制,即追求政治权力的单一性。简单地说,党控新闻是党控政权的必然结果。在苏联政治初期,列宁为实现单一政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排除了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制约。在一份政治宣言中,他公然称:“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人民委员会名单,而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的名单。”【注11】
中共建政之初虽未直接实现单一权力而有协商名义下的议政党派,但在新闻管制方面,准确实施了单一权力计划。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报纸“从民办到党管”【注12】的历程是一个经典。在这个经典发生之前,基于新闻业维续之必需的商业先机遭到了重挫【注13】。换言之,新闻业的商业内核已经被政治内核所取代,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出现邓亚萍之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子矛子盾:善意欺骗固化
上海报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遭遇,证明单一权力统治比国民党时期的新闻自由还要差,尽管在革命时期作为反对党的中共从未放弃过对政府的言论批判。比如,《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情况下)社论要求国民党“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以及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注14】。时至今日,中共当年的民主(特别是要求言论自由)主张已经不断地被网络舆论当做“反面教材”来指斥【注15】,其道德逻辑就是中共是个一贯行骗的政治组织。其在建政前的一切民主诉求都是政治表演。
就中国近晚传统的原因看,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与建政之后的表现,尽管明显表示出目的第一的企图,但自袁世凯陷入威二主张的困局以来,民主政治与国民素质之关系确实是至今未解的难题【注16】。这个难题更多地源于传统哲学浅薄而致的思维缺陷,其结果是政治科学探索的懒惰。因此,目的第一的企图可视为善意的欺骗。而最大的不幸是: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新国家,在权力系统里面都不可避免进入革命专政向反动专制堕落的逻辑,特权泛滥成为社会特征,最终使善意的欺骗走上假戏真演的路子。南斯拉夫首先没有例外于此种堕落,而后是波兰、苏联等一大串国家,中国当然也没能例外之。
当然,善意固化即假戏真演于共产党政权建政后,不惟中共本身要承接威二主张困局之负资产,还在于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单一权力设想有着强大的基督教(广义的含新教、天主、东正三支系)背景支持。尽管所有共产党政权(乃至未能获取政权的议会党)都是无神论即非宗教意识形态,但是基督教早期共产主义思想是西方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历史与政治哲学资源,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不可能实质性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更为决定其命运的因素是:基督教迅速现代化后(如解放神学之出现以及跨宗教教会形成),共产党还在加尔文主义的单一权力魔咒下无法解脱。无须讳言,努力建立单一权力的列宁就是十六世纪中后期加尔文的翻版,而所有的试图挑战单一权力的思想家都是塞维特斯,尽管未必人人遭遇火刑【注17】。同时,列宁主义下的所有政治整肃运动也无疑是当年加尔文肃清日内瓦的翻版,“当‘正义’完成时,全城留下的唯一政党是加尔文的私党”【注18】。
四、激烈反对:宗教精神动力
固化了的善意欺骗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现象,因此世界上最激烈的思想改革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宗教领域内。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被历史学家特别是神学背景的历史学家所夸大,与之对抗的塞维特斯之激烈仍不容忽视。其之激烈,以至于同情他的后世作家斯•茨威格也不由地将他与小说人物唐•吉诃德相提并论。在更长的历史上看,塞维特斯有(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卡斯特利奥)显然不是特例,仍是发生在十六世纪但影响远没塞维特斯事件为大的意大利的麦诺齐奥事件亦是之。
麦诺齐奥以不承上帝创世而犯罪并被处死,但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两大诱因:第一,社会内部不断地产生反对单一权力的力量,他的“胡言乱语”(如出自奶酪的蛆虫变成天使)与塞维特斯数百页之巨的著作没本质的区别,都是追求激烈变革,享有一个信息供给更充分、信息流动更畅通的世俗结果;第二,新技术出现与宗教改革相得益彰【注19】,对单一权力形成了巨大的破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因此而碰撞,碰撞更加大了信息流动的乘数规模。
反对单一权力作为具有宗教改革精神的现实抗争,存在于共产党政权的所有国家,不管规模大小与形式如何(如街头运动与地下教会之共存),它们都在起作用。时过二十四年,中国当代社会最大的反对单一权力运动,不仅仍是社会政治的不易中心话题之一,而且它具有转型“核能”力量。首先,“八九•六四”是一切起于内部改革诉求的“教派冲突”,结果是原教旨社会主义取得政治胜利,自由主义一方在政治上失败但获得了体制外的远期道义认可——赵紫阳(作为中国版的塞维特斯,尽管没丢命)于今成为底层维权力量的“神学”符号即是证明;其次,革命专政堕落为反动专制的社会压迫性后果已经难以令人承受(表面是通胀即物价问题)的程度,由此也引起正统革命精英之政治生存与新生底层庞大群之生活生存的冲突,造成社会运动在所难免;再次,这场源于体制内“宗教改革”的社会冲突对一个传统而未解决的信息等级问题的显性化起了巨大作用。
结语:失败的反抗亦意义深远
由分级阅读、单一权力、“洪宪改良”暨威二主张负遗产混合而成的信息等级问题,就是新闻出版立法问题。公平地说,在“八九•六四”事件发生之前即胡耀邦逝世之前,中共高层已在推进该方面改革。比如说,1987年7月出了新闻出版法送审稿,1989年1月又出了新闻与立法各自单行的草案。此被非常专业的学者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闻立法工作成果结晶【注20】。不过,这类的立法本该在毛统治结束后马上研议,估计是经济难题压在头上,改革权威邓小平尚没意识到这场补课绝不亚于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也由于补课太晚且立法过程的拖沓或有明显反对(如陈云所讲随意控制【注21】),以至于信息等级问题成了“八九•六四”事件过程中一个当局无法绕开的话题。可惜的是,研究该事件的权威们尚未对此给予重大关注。现在不妨根据正统的官方资料(1989)进行描点:
(一)4月29日,《世界经济导报》因刊登19日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内容而被上海市委整顿【注22】;意味着中共党内规则可行使新闻审查的法律功能。
(二)4月30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首都高校学生对话,否定中国有新闻检查制度,更不会出现报纸“开天窗”现象,尤其讲道:“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草拟新闻法、出版法,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今年有可能拿出草案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注23】。
(三)6月30日,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做平叛报告,再次提到上海《世界经济导报》4月19日的座谈会(合办者有《新观察》杂志社),指责该座谈会“为反自由化‘翻案’”【注24】。
这三个点准确地证明了体制内基于反对等级阅读暨信息等级制度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袁木技巧高超的说谎已钙化为历史,背景问题“要求新闻说真话是学生最强烈的要求之一”无疑是“八九•六四”留下的“核能”矿区。在此后二十四年的历史中,一方面,新闻说谎变成“反正我信”式的官方自言自语,而饱受民间诟病,以至于体制内重提新闻出版立法的诉求于今再度发出:另一方面,从袁木的无审查之说到邓亚萍无假新闻之判,不仅被体制的言说技巧自己证伪(死),而且,维稳式新闻管制在网络社交平台勃兴的今天已经全面破产,尽管它还以某种形式顽固地存在【注25】。整个统治集团自“八九•六四”之后的二十四年里,所言越伪,越证明事件过程中反对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度的诉求越有历史担当;所行越谬,越证明事件过程中打破分级阅读(信息等级)制的行为越有现实责任。可以说,在大历史视角下,中国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的启动恰恰始自于二十四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事件。
2013年4月初构思,中旬备齐主要参考文献(书目);4月下旬至5月初,续补报刊资料;5月4日至6日初稿,7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4月5日文章,“让真相跑在谣言前头”(作者:沈泽玮);新华社《参考消息》4月8日转刊,题目未变,第15版〈观察中国〉。
[2]&[3]参见《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8月号,“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作者:孙旭培)。
[4]参见《读书》杂志2001年3月号,“帝制中国与媒介权力”(作者:吴予敏);亦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舆论监督的历史困境”,2013年5月5日,原文为2002年狱中读书笔记。
[5]关于这点可见我的[4]所指博文。
[6]同[5]。
[7]参见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汉译本,杨昌裕译),P19;杨译版本:商务印书馆,1992(2005年第5次印刷)。
[8]参见深圳广电集团资讯(中国时刻)2010年12月16日报道,“邓亚萍称《人民日报》六十二年‘没有假新闻’引起起哗然”。
[9]参见新浪新闻2013年1月2日转引《南方日报》报道,“《人民日报》改版称新的一年努力说真话”。
[10]同[4]引吴予敏文章。
[11]同[2]指杂志,2013年2月号,“契卡:建立清一色政府的工具——契卡成立新说”(作者:闻一)。
[12]参见[4]指杂志,2012年4月号,同题文章(作者:张济顺)。
[13]同[12],文章援引著名报人徐铸成(《文汇报》经营者)的说法:“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做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
[14]同[2]。
[15]到本文写作时,我以品质(而非数量)标志所做的微博统计,当中的“重头微博”仍显示出自由学者暨良心公知对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观点的对比性关注,即试图用历史原证来促使当局清醒。比如,徐昕(http://t.163.com/justice)在2013年5月4日引述《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社论:“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子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16]关于袁世凯第一个面对的民主政治与国民素质的难题,可见我对“洪宪改良”的政治学分析。两篇拙文:(一)“多党制被抑制的历史考察——从古德诺事件到贝尔现象”,载于《零八宪章月刊》网站,2013年4月1日,亦可见我的网易博客(4月3日);(二)“威二主张翻版的现实解析——既得利益决定政权过渡性质”,同前网站4月16日,博客亦4月16日。
[17]就塞维特斯事件的肇因来说,它也是一个广义的分级阅读制度下的事件,至少也是标准的言论自由事件。他因反对附加教义(而非《圣经》原本的)三位一体,写了《基督教的恢复》(1553)一书,因此不见容于天主教与新教两方,终在同年被日内瓦的加尔文改革派判处火刑。事件描述可见斯•茨威格(1936)《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史实》(汉译本,赵台安、赵振尧译),P99-143(第五、六两章);两赵译本:三联书店,1986。
此外,我本人是可以归为文化基督徒的那类信仰者,且在政治学术研究中高度关注信仰自由暨反对来自政权的强行干预(宗教事务),但我从来不否认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残酷性与非人性,也秉持整个人类不存在唯一神宗教的宗教哲学观点。
[18]同[17]引书,P204。
[19]意大利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在研究麦诺齐奥事件的专著(1982)《奶酪与蛆虫》中,指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发生碰撞,宗教改革与活版印刷术发明有着重要促成意义。转引自《读书》杂志2001年6月号,“小人物和大时代”(作者:李霞),是为《奶酪与蛆虫》一书的书评。
[20] 同[2]指杂志,2012年2月号,“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作者:孙旭培)。此文在前,[2]文在后,同为一个作者且关注同质主题,因此,本文中称其为“非常专业的学者”并不为过。
[21]陈云曾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出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引文出处同[20],但原文未具该说法的时间。
[22]参见乔初编《戒严令发布之前:4.15-5.20动乱大事记》,P17;乔编版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23]同[22],P102。
[24]同[22],P172。
[25]此类的“某种方式”一方面说明袁木所掩饰的新闻审查制度存在,另一方面,“开天窗”虽未得到任何一家报刊的证实,但是隶属中共党权体系的宣传部门不时向媒体直接下达方向性指令以至某些“选题不能做”确是真实存在的。参见[20]文章里所列编辑人员的日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