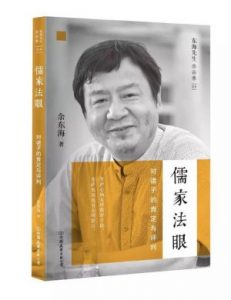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陈一谔因称北京处理六四问题的手法“有问题”,被指责为袒护北京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遭到各方强烈抨击。有港大学生发起罢免陈一谔的公投。陈一谔认为事件被放大,自己没有错,坚持不道歉。
为纪念六四而作的雕塑国殇之柱(The Pillar of Shame),就坐落在香港大学学生会正门前,见证著学生会将“平反六四”的呼吁通过公投写入会章。而与此同时,一场有关六四的风波,正衝击著上任一个多月的学生会会长——陈一谔。
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陈一谔在香港大学有关六四的论坛上发言时说,中央政府在处理六四问题的手法上“有问题”,被指责为袒护北京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遭到各方强烈抨击。其后,港大学生会发表声明,表示陈一谔的言论不代表学生会立场。同时,港大学生陈巧文发起了弹核陈一谔的动议。校园内外则流传著“陈一谔是左派中学毕业的『隐形左派』”、“陈一谔是中联办的特务”等说法,莫衷一是。更有不少港大的学生和校友发出了“清理门户”的号召。对此,陈一谔感到十分无奈。
“我觉得这是误读。”陈一谔对亚洲週刊表示,他在论坛发言中的真实表述是,六四事件中政府的手法“是有问题的”(原话是“中央政府可能鳋呢个镇压上面、手法上面系有问题鮋”),而不是“有点问题”,同时还一再强调了手法的残忍和血腥。但他没有料到会遭到另一位嘉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的反驳——“岂止是有点问题!”(原话是“陈同学话政府的手法系有鱓问题,喂,我觉得有好大问题喔!”)在其后的发言中,他便援引了议员所说的“有点问题”进行解释。
陈一谔称,他不想就字眼做太多争执,他认为,叫“屠城”也好、叫“镇压”也罢,对于整个六四来说只是微观层面的句读之争。“姿态上做出为六四平反的呼吁是必要的,我更希望用正视历史的态度去认识整个八九民运。”他一再重申,自己坚决支持平反六四,并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派”。
至于指责其是左派甚至间谍的言论,陈一谔表示,自己毕业的沙田苏浙中学并没有鲜明政治立场,而与中联办也从未有过往来,只是在外校的某个典礼上“打过招呼而已”。
生于一九八九年的陈一谔坦言,自己主要是通过“自学”的方式,来认识与自己同年的八九学生运动的。“我关注六四事件的历史进程和转捩,重点不会全部摆在军队怎麽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样血淋淋的场面和主观描述。”除了当时的新闻资料,张家敏的《建国以来》、赵鼎新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是他认识六四最重要的读物。此外,卡玛·韩丁(Carma Hinton)的纪录片《天安门》,他也看了很多遍。
与他的成长过程相似的,是港大学生会副会长成晓宜。她说,香港各间中学所教授的中国近现代史,并不包含有关六四的内容,“考试范围也没有涵盖,老师有兴趣,才会在课堂上提起。主要还是靠自己搜集资料。”听到有内地学生在论坛上指“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流一滴血”,她感到痛心,但并不愤怒。“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内地生和本地生标籤化,有很多本地生也不了解、不关心六四事件,而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内地生的邮件支持平反六四。”但她认为,总的来说,香港比内地情况要好,“想去了解,总能了解得到,不像内地,想了解也很难取得资料,所以我觉得不能责怪他们”。
内地学生迴避政治立场
为推进公众对六四事件的关注和认知,二零零八年,成晓宜主编了港大学生会出版的六四特刊。但她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成效,关注特刊的,大多是原来就关注六四的人。还有内地学生跑到学生会来要求退会,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学生会是有政治立场的”,而自己也“不想有任何政治立场”。在学生会干事的解释下,才逐渐消除疑虑、打消退会的念头。现在正值六四二十週年前夕,成晓宜又与同伴一起在港大校内发起了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平反八九民运,并就『六四屠城』负上责任”的公投,希望激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但陈一谔却对其中“屠城”一词,持有保留意见。他认为,这样“激进”用词会置香港于中共的对立面,无助平反,并认为平反之外,可以参考北京异见作家戴晴提出的大和解模式。“以前我们看六四,总是把眼光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暴行上,而我更希望将眼光放在整个八九学运的历史上面,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样才会对将来中国和香港的民主进程有帮助。”陈一谔说,他并不想淡化历史,只是希望正面宣扬六四运动中学生关心家国的情怀,所以在发言时没有把重点放在“屠城”或“镇压”上,而是“希望将正面的信息带给新一代”。
而面临罢免程序的陈一谔,是否还能像在竞选时一样,将变革的希望和正面的信息带给港大的学生呢?二零零九年二月港大学生会选举,陈一谔以独立竞选者身份参与,打出“变革”与“希望”、尊重非本地生文化等口号,击败领导十人候选内阁的竞争对手,高票当选会长。如今不少港大内地学生也卷入纷争。论坛当天,有内地生发言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留一滴血”,话音未落即被现场观众轰下台。去过论坛现场的港大学生对亚洲週刊表示,论坛的目的是讨论交流,不仅缺乏倾听和理解,甚至不让人把话说完,实在让人不快和不解。
陈一谔在该名内地同学被轰下台后,曾走出来对现场听众说,作为会长,他需要捍卫每个人说话的权利,也被现场嘘声的洪流淹没。他指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氛围和状态,并不利于达到平反的目的:“我不过是想提供多一种看问题的角度。而各种观念的交流、碰撞甚至互相学习,正是香港这座自由的城市最为宝贵的地方,也是让大家重新关注、思考六四的契机。”
成晓宜和陈一谔,都充满著对遗忘的恐惧和焦灼,儘管两人选择的方式不尽相同。成晓宜说,四月八日学生会干事会已发表了声明,指陈一谔的谈话不代表干事会的立场,至少不代表她本人的立场。而在陈巧文等人发起罢免动议之后,干事会已将罢免程序的宣传和运作交给了发起的同学,自身则尽量保持中立。至于她个人,对于陈一谔的言论则表示“震惊”。
在罢免大潮中,陈一谔似在“孤军作战”,但他坚持不会就罢免事宜以及之前的言论道歉,他说:“我希望我留下来,不是因为别人认为我言论正确,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敢言敢为、能为大家带来希望和改变的学生会会长。”为了在公投之前争取支持,陈一谔已有四天没离开学校,没有换衣服,也几乎没怎麽合眼。採访步入尾声时,他说:“好在事情很快就会完结。”倦意难掩。
四月二十二日,罢免公投将正式开始,二十四日,陈一谔将知道自己的去留。成长于九十年代的陈一谔、成晓宜以及其他港大学生,也许从未想到,对六四的关注和讨论会让自己的生活与二十年前的这段历史发生如此共振。陈一谔认为:“如果历史会还六四一个公道,也会还我一个公道。”但作为香港大学历史上少有的经历罢免程序的学生会会长,这段经历很可能是陈一生的污点。然而,不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对香港大学的学生来说,这场风波都将是一次可贵的民主体验,而关于六四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