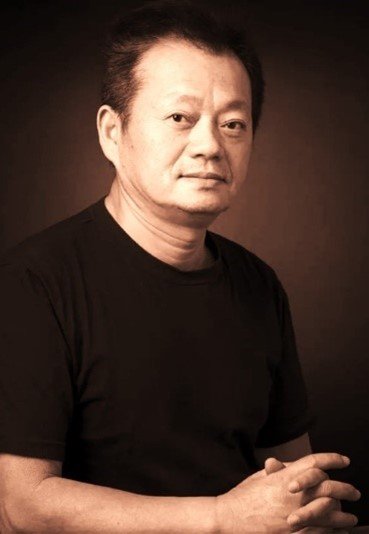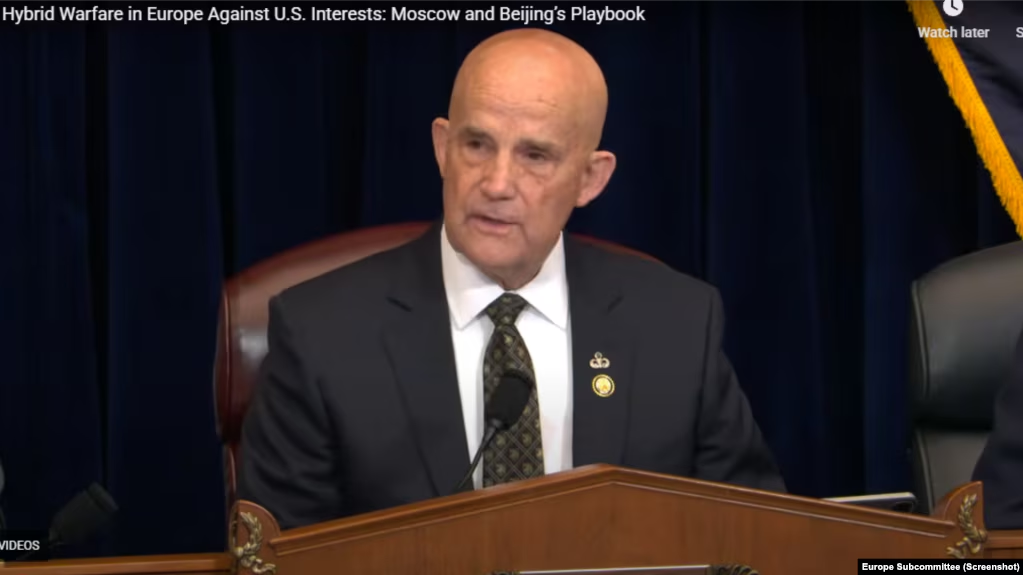(前言: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本文是三万多字的长篇评论《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中的第二节。全文收进本人2025年出版的上下两卷《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一书中。)
欧阳昱博士
在整个澳大利亚文坛,欧阳昱一开始就以诗歌特别是英文诗歌创作出名。他的英文诗歌连续十多次入选澳大利亚最佳诗歌选;英文诗集《异物》获悉尼2003年快书诗歌奖;中文诗歌两度入选中国最佳诗歌选。这位喜欢探索、创新和做实验的诗人,写起诗来更充满先锋探索意识,更以特立独行给人们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例如,关于“死亡”。如果说当年在澳华留学生小说中,对死亡作最“另类”的描写非欧阳昱莫属,那么,他那部1997年出版的约三千行英文长诗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死亡就是其关键词。长诗第五章中写道:
那瞎眼的算命老头已经告诉过他/在变成另一种东西的过程中你成为你自己/你那失落的身份将永远把你拖向/混乱的中心/最好安于如此/因为它是你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有如你习惯死亡/生存本身于你是一种折磨/比死亡更甚(见钱超英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页256)
欧阳昱《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
一个“中国诗人”是这部长诗的主角,在一个个片段的场景中,他骄傲、自卑、激昂、沮丧、愤恨、幽默、反叛、退守,自我庆幸又自我哀怜,回顾和展望都惟余茫茫。在一个人生意义的废墟中,他飞舞于一堆无法守护的身份碎片,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回归的退路,因为他属于一个带有弗洛依德式“死亡冲动”的、像鲸鱼一样扑岸自杀的神秘群体。欧阳昱把他的“诗人”所经历的身份追寻历程描写成发现死亡的过程(见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欧阳昱这部充满先锋探索意识的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的重要文献。
欧阳昱确实一开始就很“先锋”。2009年,欧阳昱在诗集《慢动作》(原乡出版社)“自序”中说:“先锋的意义至少有三:一,不写别人写过的东西;二,写别人不敢写,也不愿写的东西;三,写到完全没有可能发表的程度。……”他还说,“先锋不是姿态,而是一种亲力亲为的实践活动。”“先锋是一种精神,但它一定得实事求是、实字求字、实诗求诗地加以实践。”欧阳昱那些极富形式感的诗歌,说极具语言破坏力,不如说极具语言创造力,以至无法翻译。他在2017年5月出版的第十部中文诗集《入诗为安:一首不可能译为任何文字的诗》(台北猎海人出版社),如他自称那样,是一部不可能在中国出版的诗集,也是一部除了中文之外,不可能翻译成任何外语的诗集。它是诗人要写到不可发表、写到无法翻译之格言的真实写照和实践结果。全书以“诗”入手,改写、改装、插入、消解、溶化、颠簸乃至颠覆中国成语、古诗句、当代语汇、经典名言等,并把既定的语言、语汇和语言秩序加以肆意拆解和双语化,无不以“诗”进入一切,直到“入诗为安”。这部诗集前前后后写作了三年多,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场合朗诵给不同的熟人和朋友听,不少人的名字也以“诗”的名义进行改写后入诗为安了。
欧阳昱诗集《入诗为安:一首不可能译为任何文字的诗》
欧阳昱说,总之一条,世界之大,诗歌无处不在,包括厕所里的告示,他看着根本就觉得是一首诗。“好坏对我无所谓,只要好玩就行。”(磨铁读诗会网站)
“拾得诗”是欧阳昱诗歌实验的一个重要类别。何谓“拾得诗”?欧阳昱说,简单说来就是把任何地方,包括报纸、杂志、产品说明书、课本等上看到的文字拿来,略略加以改造,如删节、调整行距、分段等,重新加工为诗,这有点像民国时期三十年代文人看了外国影片之后,根据影片内容,重新翻写短篇小说,也有点像成龙的武打电影,不用专业武器,而是随手抓到什么,什么就是武器。至于什么材料和内容会刺激欧阳昱去“拾得”?他开始想要“拾得”的时候,最看重原始材料中的什么特质?对这个问题,欧阳昱觉得很难说。他说,比如最近他看足本《金瓶梅》,对那种对性爱的描写就特别感兴趣,大篇幅地拾得。还有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翻译到一段特别有感觉的文字,他会停下来,立刻拾得为诗,比如写鱼的那首,就是翻译海明威时出现的。
欧阳昱的《重放》一诗(见磨铁读诗会网站),被选入“汉语先锋·2021年度最佳诗歌100首”中。这首诗“好玩”地把一节诗重放了四次,如入选理由所言:这样,如果大声读出来,用各种节奏、各种抑扬顿挫、各种南腔北调去读,越读越会觉得这首诗的效果太好了。欧阳昱对于形式的探索真的是层出不穷,他的脑子里装了一个神奇的百宝盒,仿佛随时都能从中掏出一些bling-bling的东西来。在欧阳昱这里,形式主义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生命活力。(磨铁读诗会)
“好玩”中自然有关于“性”的。他数量庞大的万余首诗中,很多诗歌因直白、不避粗俗鄙陋而对读者构成直接而强烈的冲击力,对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底线进行挑战,特别是他的性爱诗。《B系列》里的二十三首“B诗”,从其标题已经知道写的是什么:《找 B》《换B》《审 B(1)》《卖 B(1)》《日 B》《摸 B》《假 B》《看 B》《傻 B(1)》《舔 B》《玩 B》……。这些诗大部分创作于1998年,也有的作于1999年,评者注意到,这个时间节点颇有意思,刚好是在中国大陆网络诗歌风起云涌的前夕,同时,也是轰轰烈烈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前夜。这组《B系列》是真够惊世骇俗的。其实,在欧阳昱出版的四十多本诗集中,其性爱诗占的比例也不小,比如《啊,月下的树荫多么宁静》《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女人》《渴望裸体》《性的告示》《性爱是一件体力劳动》《黑美人》《迪斯科舞厅》(Discotheque)、《妓女们》(Prostitutes)、《性而上》(Sex Up)……等,这些诗中,性语言、性动作、性暗示屡屡出现。据说欧阳昱写的性爱诗远远超过千首。有人说,这些性爱诗歌让人读后感觉他有时是在以下半身思考用上半身写作,有时又是在以上半身思考用下半身写作。他在用性爱诗挑战自己写作底线的同时,也在挑战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底线。不了解他的读者,猛不丁读到这些诗,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倪立秋《欧阳昱:在中英双语之间自如游走》,网络)。
但是,必须指出,欧阳昱许多所谓“另类”诗作,在探索、创新、实验的旗帜下,亦可能另有深意,大有深意。
欧阳昱诗集《限度》
例如,欧阳昱2004年8月由原乡出版社出版的第四部中文诗集《限度》中的诗。例如其中这首《中》:
不就是中不溜儿/不就是中庸之道/不就是中国的中吗?/中不就是/口/中间竖着插了一根钉子/而成中的吗?/不就是用钉子从一只空心盒子正中穿过去/而成中的吗?/拔掉这根从中作梗的钉子/让它成为无遮无拦的口吧!
这首叫《中》的诗,步步推进讨论“中”字。一个简单的汉字,欧阳昱却从中发现“游戏”的由头——不,是发现“深意”的所指。这个“深意”太丰富太深刻了。我分明听到欧阳昱对几千年中央皇朝的控诉。中国人何时可以口无遮拦有言论自由?当然首先要“拔掉这根从中作梗的钉子”。这是什么“钉子”?就是专制独裁统治。
欧阳昱这些好玩的“游戏”诗歌,往往“图穷匕首见”,关键在诗的最后结尾。看看《拆卸祖国》这首:
祖国其实不是母的/先看“祖”/左边是个“示”/显示的示/右边是个“且”/念“qie”/还/念“ju”/现在来把“且”/“ju”(举)一“ju”/看它象个啥玩意:/“且”/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原来是个阳具/现在明白为什么它又念“qie”了吗?/原来下面两个卵蛋被人切去
中国人都喜欢说祖国是“母亲”,而欧阳昱偏偏要说“祖国其实不是母的”。欧阳昱绝非开玩笑,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据权威专家考证,并得到业界共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被出“示”的“且”是个象形字,有两个意思,其中特别是表示男性生殖器的文字符号,后来在汉语里出现“祖”这个会意字,可谓出于男性生殖器崇拜意识。欧阳昱从“祖国”里拆卸出“阳具”,又发现它“原来下面两个卵蛋被人切去”了。我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到本来是“公”的国家残废,而且残废到不成样子,不就是那些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最拿手的把戏吗?不就是那些统治者把国家变成“母”的而大肆强奸吗?也是诗人的杨邪说得好,欧阳昱“所谓文字游戏,只是他穿着的掩人耳目的外衣而已”。读者只要仔细体味就应该感受到欧阳昱的严肃,甚至愤怒。(杨邪,《几个标本,一柄标杆:欧阳昱诗歌与小说印象》,《华文文学》,2013年2期;也见网络。)
《限度》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作,或多或少都带有“游戏”的性质,但其中的深意是可以发掘的。
其实,欧阳昱的诗作往往带着极强的各种各样的而且是先锋性的批判意识。他早在1997年出版的那部英文长诗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如此,2012年出版的The Kingsbury Tales: A Complete Collection(《金斯伯里故事全集》,Otherland Publishing)更是如此。
欧阳昱《金斯伯里故事集全集》
欧阳昱这部重要作品并非简单的诗歌合集,它借鉴“英国诗歌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的形式,更像是一部小说,尽管缺乏传统小说的整体情节,分为多个章节,如“历史故事”、“女性故事”、“移民故事”、“新加坡故事”等。欧阳昱的灵感来自地名金斯伯里(Kingsbury),这是他1991年从中国到澳洲后定居之处,在这个充满多元文化的地方,他首次接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并与之发生冲突。在这部作品中,欧阳昱传递一种因对世界无法理解而产生的错位感与悲剧感,这种体验既来自诗人本身,也来自他笔下的角色。欧阳昱选择了一种直接且愤怒的方式,揭露种族主义、语言冲突以及对中澳两国社会问题的批判,不仅捕捉了个体的孤独和边缘化,也揭示了文化交流中深藏的荒谬与不和谐。
小说家和诗人希瑟·泰勒-约翰逊(Heather Taylor-Johnson)称《金斯伯里故事全集》为“直白的诗歌,没有废话”。她写道:“欧阳昱并不想展示渴望。他表现的是愤怒——对种族主义的愤怒,对语言的愤怒,对中国追求西方化的愤怒,对澳大利亚缺乏追求的愤怒。”(“This is straight-talk poetry. No bullshit. Yu does not wish to demonstrate longing. He depicts anger. Rage against racism. Rage against language. Rage against China and her drive to be Western. Rage against Australia and her lack of drive.”Cordite Poetry Review, 6 February 2009)
欧阳昱这本书得到了澳大利亚著名诗人约翰·金塞拉(John Kinsella)的高度评价,他称之为“一部杰作——‘澳大利亚诗歌’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I think this work is a masterpiece -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of ‘Oz poetry’.”见网络)
诗人评论家大卫·麦库伊教授(Prof David McCooey早在评价欧阳昱的The Kingsbury Tales: A Novel(《金斯伯里故事:一部长篇小说》,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社,2008年)时,就这样说过:
欧阳昱的诗歌辛辣、幽默、充满政治讽刺,始终关注现实的陌生、多样与恐怖。《金斯伯里故事》是他的一部重要新作,充分展现了欧阳昱的才华与广度。作品充满了历史、记忆以及日常对话中的故事,是一部既深刻震撼又极具娱乐性的诗歌作品。(“Ouyang Yu’s poetry, acerbic, funny, wickedly political, is unremittingly concerned with the strangeness, multiplicity and horror of the real. The Kingsbury Tales is a major new work that shows Yu’s brilliance and range. Filled with stories from history, memory and everyday conversations, The Kingsbury Tales is both a profoundly shocking and entertaining work of poetry.”中文为本文作者翻译,英文见网络。下同。)
的确,《金斯伯里故事全集》是一部融合了愤怒、幽默和洞察的极具对话性和探索性的诗集。通过对诗歌与小说形式的模糊界限的突破,欧阳昱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他深刻的文学洞察力。对那些对诗歌、历史话语以及跨文化冲突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部书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本。
欧阳昱《异物及其他诗歌》
欧阳昱于2022年10月10日出版的新书Foreign Matter & Other Poems(《异物及其他诗歌》,Ginninderra Press)也是充满先锋批判意识。人们读这部新诗集,觉得欧阳昱不屑于区分所谓“高雅”所谓“低俗”的艺术,他在解构诗歌,逐步拆解、重新思考并重新设计这门古老的艺术。他利用一切设备和手段,以一种充满语言游戏的方式穿梭于英语之中,来创造属于他的“反诗”品牌。人们发现,在欧阳昱这部“反诗”诗集里,有一种带刺的观察,澳大利亚常被描绘成一个“反乌托邦”,一个充满波动却又平淡的文化大熔炉,混合着被接纳和被引入的各种文化,是一种“充满监狱”的自由;被流放的角色们在愤怒与屈服、愤世嫉俗或是愕然之中闪烁不定,甚至出现心理崩溃。如书评人所说,欧阳昱徘徊在游离的边界上,观察着家庭生活、政治、悲伤和知识,以锐利的批判性和微妙的诗句粉碎了任何界限,其“异物”既是催化剂,又是挽歌。他是后民族、多语种、多元文化的诗人部落中一位值得尊敬的成员,一位无边界的诗人,一位真正的国际诗歌共和国的公民。他证明了单单以诗歌为生命意义和价值便已是无价之宝藏和美好的目的。
欧阳昱双语诗集《永败之旗》
于2019年1月1日出版的Flag of Permanent Defeat(《永败之旗》,Puncher & Wattmann出版)是欧阳昱融合双语写作的代表作。这本诗集收录了诗人自1982年到2019年的二百零七首英汉双语诗,囊括了他大量的实验性作品,包括声音诗、无字诗、摄影诗、概念诗、拾得诗及拼音诗等多种形式的探索性诗歌,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无缝流动,最具趣味也最具挑战性,充满了反叛精神。诗集封底印了一句别出心裁的广告语:“Ouyang Yu is still alive, and writing. This is his most posthum(or)ous work.(欧阳昱还活着,还在写。这是他最后幽默或死后而生的作品)”。
人们评价道,这就是欧阳昱和他的诗作,它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不会是平凡或平庸。
人们说,在欧阳昱英勇的诗歌旅程中,没有什么能够征服他的独立与独特。他的诗歌总是生猛、新鲜、激烈而有力。
人们非常欣赏欧阳昱活泼的生命力,觉得他的实验精神和创新精神让他不知疲倦地疯狂折腾,他甚至命令自己去实现一种完全不能为当世接受的先锋精神。
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迈克尔·法瑞尔(Michael Farrell)也禁不住赞叹道:“Yu brings a refreshing oddness to the oddness of Australian poetry……(昱为澳大利亚诗歌的奇特更增添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异色彩)”(Flag of Permanent Defeat诗评,网络)。
《永败之旗》书名出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欧阳昱就像那位老人一样,坚信,而且以行动证明,人可以被摧毁,却不会被击败。那面“永败之旗”正是一面永久胜利的旗帜。
再回头看看早年欧阳昱出版的第四本中文诗集《限度》开篇第二首小诗《把》:
母语/带/回国/让/大家/操/去吧/我/带/父语/出/海/把这颗独种/撒下
有人看出了《把》诗绝对不是纯粹的语言游戏之作,不过只认为它是表达诗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同时也从一种语境进入另一种语境”的“苦涩与无奈”(杨邪,《几个标本,一柄标杆:欧阳昱诗歌与小说印象》,《华文文学》,2013年2期;也见网络。)。我的解读不同。相对于“母语”这个人所共知的词,欧阳昱独创“父语”这一个全新的概念。“父”是可以下“种”的。如果说,“父”下“种”虽正常却平常;那么,“父语”下“种”就非同小可了,而且欧阳昱还不是一般的“下”,他是“撒下”!所以,在我看来,这首《把》诗可谓欧阳昱的不同凡响的“宣言”,他的确毅然与决绝表达了他“出海”弘扬中华文化的雄心壮志——他将有一番“撒下”“父语”“独种”的壮举。从欧阳昱“出海”至今三十多年文学文化业绩来看,他大大超额实现了他的宣言,他的壮举引人注目,非常成功。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来源: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