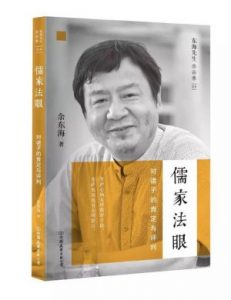十八、站街女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七月十九日開始掃黃打非,董姐早就交代了,並把我們五個姐妹安置在四樓的閣樓上不允許下樓,吃飯也是派人送,她們四人打牌吸煙,我悶得要死,閑得無聊也拿起煙抽,我一連抽了五六根,還真覺得吸煙有些提神、解悶。
二十日,我和小燕子都懶散地靠在床上聊天,董姐叼著煙進來了:今天還得到閣樓上去,你們打撲克、打麻將,隨便玩吧……這兩天損失慘重。
小燕子:董姐,反正不能做生意,悶死了,讓我們上街逛逛吧,我們不會跑的。
我說:是呵,廣州是什麼樣子?董姐,你讓我們出去看一看吧,我都這樣子了,哪還會跑呵!
董姐若有所思:好吧,我安排你們出去玩一玩,我帶上保安和狼狗,估計你們跑也跑不掉。
我和小燕子同時高呼“董姐萬歲、”“董姐偉大!”
兩輛麵包車出發了,前面車裏坐著董姐和我們五個姐妹,後面車裏是三個保安和一條狼狗。
正是炎熱的夏天,被關了幾個月的我,真感到恍若隔世。
我們去的第一站是白雲山,先遊玩了雲臺花園、星海園,再沿索道上行,只見山巒起伏,溝穀縱橫,氣勢磅礴,真是漂亮極了,我們五姊妹說說笑笑、嘰嘰喳喳,好不開心。
又玩了滴水岩、白雲曉望、白雲晚看、天南第一峰、明珠樓、水月閣等景。到白雲晚望,憑欄遠眺,珠江如帶飄散在廣袤無垠的土地上,羊城美景盡收眼底。
一直到華燈初上時,才進入廣州市城區。好大一個城市呀,林立的高樓、璀璨的星空,闌珊的燈火,玲瓏滿目的商品、川流不息的人群,構成了城市繁華的畫卷。我終於看到廣州的樣子了,這個城市的外表真是太美了。
看著外面的景色,我尋思:這麼美麗的一座城市,為什麼有齷齪的鳳凰娛樂會所?除了鳳凰娛樂會所,還有多少見不得光的地方?
董姐說:我們就在外面吃飯吧,換一換口味。
我們歡喜雀躍。
找到一個“天外天”的酒店吃晚飯,玲玲和芳芳要喝啤酒,逼著我和小燕子也喝了起來;董姐興趣也高,就敬來敬去,好不開心,我也喝多了酒。來到廣州幾個月,我從來沒有這麼開心。
再次上車後,路經一處繁華的街道,只見路邊站著三三兩兩地打扮妖豔的女人,董姐介紹說,這些都是站街女,她們不僅生意難做,還得自己租房子、吃飯,接待的都是農民工,打工仔什麼的,都是低檔次的客人,都不講衛生,好多女人都有性病。
玲玲問:她們賣一次多少錢?
開車司機說:價格不等,主要靠跟客人討價還價,一般兩百元成交。”
玲玲哈哈大笑:兩百元賣一次?太便宜了吧!
董姐:只有這個價。所以說,你們要知足常樂,我給你們的提成就是兩百,而她們在街上守著,還要跟過路的先生們叫賣:先生,玩玩嗎?先生,打炮嗎?多沒廉恥呀。
眾姐妹大笑不止,我卻發現了一個現象:這些女人年齡都偏大,長得也很一般,多數都是胸脯平平、肚子肥碩的女人。
小燕子:她們都是年紀大的女人耶,都不漂亮,我們不敢說十分漂亮,至少比她們年輕,身材好!
眾姐妹嘻嘻哈哈地附和:是呀是呀!我們吃青春飯呢。
董姐坦言:不錯,她們多數是下崗工人、農村家庭婦女,以為沿海城市的錢好掙,就跑來了。
行駛到天河北路,是一條林蔭道,燈光若明若暗,玲玲堅持要下去看一看,眾姐妹齊聲叫好,董姐無奈,只好說:下去玩一會……這幾天嚴打,這些站街女可能還不知道,你們可別出亂子。
於是,我們走在前面,安保牽著狗走在後面。
這是一條老街,兩側門店多數是髮廊和餐館,街上大葉榕樹根粗壯,電線杆上昏暗的路燈從上面照射在樹木中間,婆娑的燈光灑在地面,婆娑的樹影倒映在路邊的老牆上,若隱若現、突明突暗,給人一種詭秘、迷惑的感覺。
昏暗的樹影下站著無數的女人,她們有的三四十歲,最年輕的也有二十多歲,她們嘴唇擦得血紅,臉上塗脂抹粉,眉毛畫得有些誇張,她們或蹲或站、或互相摟著站在那裏,看去懶散、悠閒,只是當她們嘴裏吸進煙捲燃起的一刹那,才能從紅指甲的縫隙裏看到她們機警的、複雜的、左顧右盼的眼神。
而穿梭其中的是一些面孔黑瘦、手腳粗糙、衣服灰暗的男人,不用說,他們是董姐介紹的農民工群體了。
走到一棵大樹樹影下,我看到一個女人叫住兩個男人:帥哥,過來,過來。
兩男子:呵呵,做什麼?
女人:要不要呵?去不去?
兩男人怪笑:去哪里?
女人:不遠,走十分鐘。
男子甲:多少錢?
女人:一百五十元
男子乙:貴了。
女人:一百二十元
男子甲:還是貴了。
女人:一百元,不能少了。
走到我後面的玲玲放聲大笑,那女人和兩男人驚住了,我忙拉她往前走,她笑得前仰後合。
小燕子說:你攪黃了人家的生意呢,她們不是為了生活嗎?
玲玲:好便宜呀,賣一次一百元,我要是男人……
我心裏有一種苦澀:我們與她們有什麼不同呢?我們只是中級妓女,而她們是低級妓女,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自由,她們有自由。
就在我發愣的一瞬兒,遠處傳來撕破夜空寧靜的警笛聲,刺眼的燈柱像無數道金光刺得我們睜不開眼睛,警笛一聲緊是一聲。在這一刻,無數的女人象像草叢中被獵犬追趕的兔子驚慌失措地奔跑著,她們有的逃進一旁的計程車裏,有的逃進發廊裏。
我們的麵包車就在後面,董姐從車裏跳出來,緊張地大叫:快快快,上車上車,警察來了。
我十分緊張,麻利地爬上車。卻不曾想,一個陌生的女人爬進我們車裏,昏暗的燈光下看不清她的臉。董姐大叫:你是幹什麼的?下去下去!
她身子縮在過道上不動,乞求地聲音說:大姐,我給錢……我給車費。
董姐大叫:不行不行。你別讓我們惹麻煩。
女人渾身戰慄,不斷地哀求。
也許是惺惺相惜吧,我動了憐憫之心,我說:董姐,我們就幫她一下吧。
女人唯唯諾諾:謝謝小妹妹。
董姐只好說:快開車。
車子啟動後,女人帶著哭腔說:我們幹這行也沒辦法呀,我男人又懶,種田交農業稅費都不夠,我孩子得了肺炎,瞧病欠了一屁股債……
小燕子關切地問:孩子治好了嗎?
女人說:感謝你們關心……救是救好了……但還欠債呀,我就是不吃不喝,賣這個爛身子,也得還人家錢呀……
我聽了,心頭一顫。
麵包車一會兒駛到明亮的燈下,外面是安靜的大街,女人要求下車,借著燈光,我看清她身上骨瘦如柴,臉上儘管抹了厚厚的脂粉,但仍然掩蓋不了蒼白與憔悴——這是一個被生活壓得不堪重負的女人。
回來後,這個女人的苦臉一直縈繞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