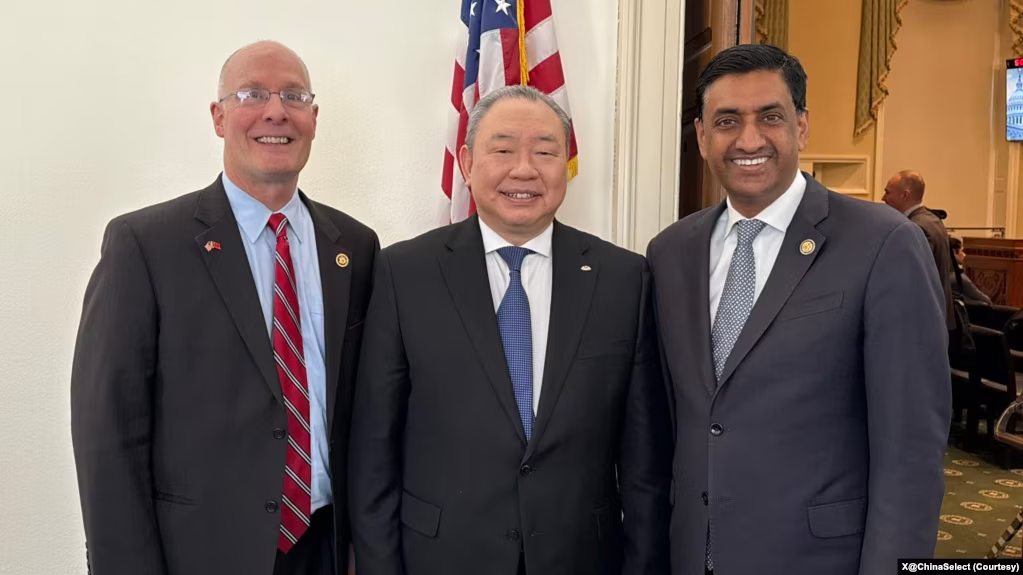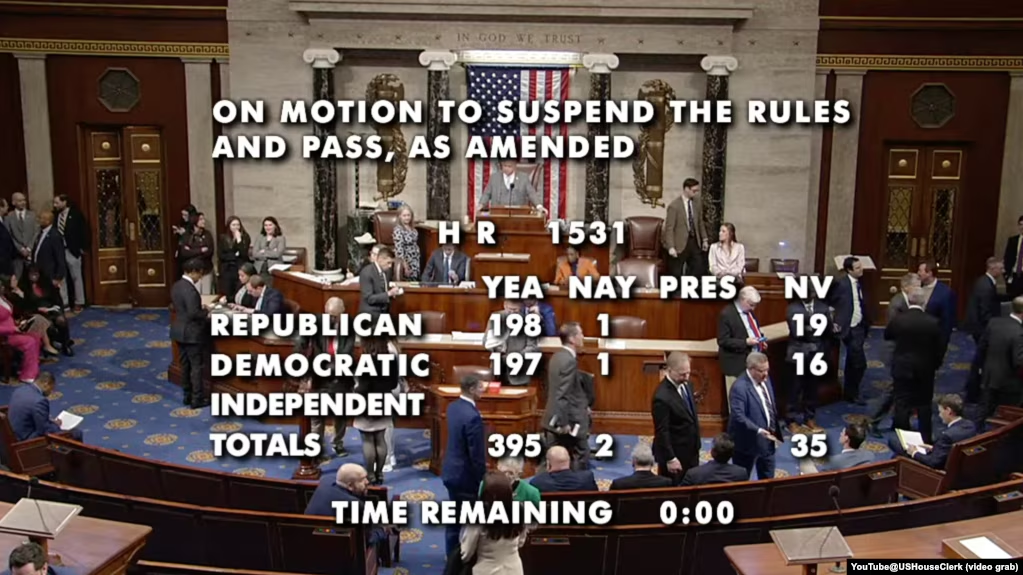一
过去的2025年,世界像一张被反复折叠、揉皱又试图摊平的地图,在局部战争的硝烟、制裁的铁幕、地缘联盟的重组与文明的裂痕之间,剧烈地开合。数字时代的新闻滚动不停,人群在信息的洪流中匆匆而过。可在这震耳欲聋的喧嚣之外,我常常想起一个在历史深处回响的名字——波斯。
那是一片曾经孕育过《王书》与星辰的土地。卢特沙漠的风,带着干渴的咸味,日复一日地掠过波斯波利斯的遗迹。残缺的石柱在血色夕阳下保持着千年不变的沉默。历史在那里层层堆叠,如同地底深处从未真正熄灭的火,在冰冷的表象下,涌动着岩浆般的余温。
二
自那场改变国运的宏大革命以来,信仰与权力便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如同粗壮的枯藤锁住了一棵正值盛年的树。古老的经文在清真寺那如孔雀羽毛般绚烂的穹顶下回响,亦在逼仄街巷的扩音器里反复振荡。
宏大的口号在广场上如浪潮翻涌,化作标语、化作教条,也化作回声,潜入人们的潜意识。岁月流转,一代又一代人在同一种严密的叙事里降生、成长。有些目光在长期的洗礼中变得坚定而狂热,仿佛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可有些灵魂,却在长久的沉默中,开始侧耳倾听围墙之外的风声,寻找一扇未被察觉的出口。
三
在任何一种单一声音覆盖大地的地方,风都会变得格外沉重。
这股风吹过肃穆的学校、繁忙的集市、紧闭的家门,也吹过女人的黑纱与少女那被束缚的发梢。在许多被遗忘的角落,女孩们尚未读懂“春天”在诗集里的含义,命运的剧本却已被粗糙地写就。
当婚礼的鼓声沉闷地响起,她们的童年便在那一刻仓皇退场。母亲站在斑驳的木门后,眼眶泛红——怀中曾经温热的婴孩,如今正被作为某种契约,送往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家庭。牛羊的数量、聘礼的厚度、繁琐的仪式、僵硬的祝福——一切都按部就班,唯有那双尚未成熟的眼睛,在厚重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清亮,也格外荒凉。 这种苦难往往没有惊天动地的碎裂声,它只是像沙漏里的细沙,日复一日、静悄悄地掩埋掉一个人的所有可能。
四
我并非只看见黑暗。在极端的压抑之下,总有不屈的生命在低声祈祷。
在某些极其隐秘的房间里,厚重的窗帘被拉得严丝合缝,阻断了外界窥探的目光。昏黄柔和的灯光下,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膝盖上摊开一本被反复传阅、甚至有些破损的书。他们极力压低声音,读着关于爱、宽恕、平等与灵魂自由的句子。
那声音虽然微弱,却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穿透力,刺破了漫长而冰封的极夜。
有人因此被冠以“叛教者”的污名,背负着被放逐或惩戒的风险。可或许,他们并非背叛了谁,他们只是在窒息的生存裂缝中,为灵魂寻找另一种呼吸的方式。信仰,本该是人与神之间最私密的私语,是孤岛对彼岸的眺望。若所有的选择都必须在恐惧的枪口下完成,那这种“虔诚”便失去了它最宝贵的灵魂。真正的光,从不惧怕理性审视;真正的爱,也永远无需暴力的强迫。
五
我想象一场春天。
它不是街头嘈杂的口号,不是随风翻飞的旗帜,而是深埋在干燥土壤里的种子,在无人察觉的静谧中,悄悄顶破了坚硬的壳。春天最初的面貌总是卑微且寂静的——它是一滴渗入裂缝的雨水,是一寸倔强的新绿,是一阵带着暖意的、无法被囚禁的微风。
也许,“古波斯之春”并不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而是一种关于“个体觉醒”的缓慢苏醒。它发生在一个女孩第一次对自己命运提出疑问的时候,发生在一个母亲决定不再为陈旧传统推波助澜的瞬间,发生在一个青年在深夜的旷野上,避开所有的教条,对上帝说出那句最真实的、发自肺腑的祈愿。
沙漠仍在,古老的风仍在吹。
但只要有人在黑暗中拒绝沉睡,只要有人在废墟上守望光明,春天就不会缺席。这种力量比钢铁更坚韧,比高墙更持久。
愿爱,比恐惧更长久。
愿自由,比压抑更深远。
愿神,爱这世上每一个卑微而勇敢的灵魂。
(202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