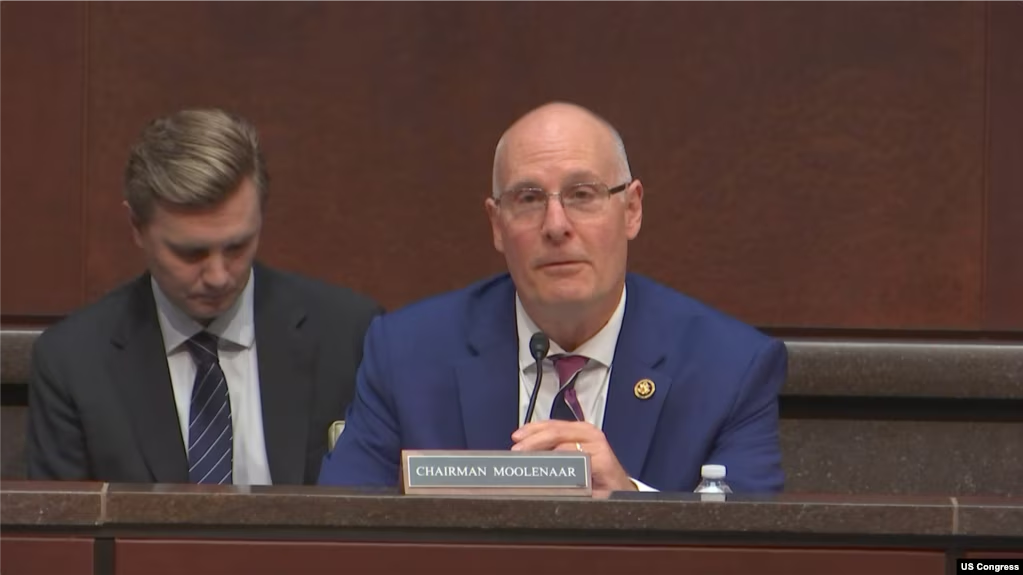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上,我觉得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失去了非常可惜。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就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两次和平转型,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然后政协决议没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和平转型成为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搏奕,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和平转型只有在这个社会有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说每一方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时,才有可能出现。
我们看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大约十来年,为什么第一次出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当时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列强大大地削弱,本身已不是一个能绝对说了算的力量,这时候在民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以往曾经被我们忽略的力量,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量开办的工厂和对外贸易都是以往传统社会不可想象的一种经济方式,随之产生了那些人、那些力量。可以说,立宪派就是清政府之外的、独立于官方的一种新经济力量,这是第二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强烈不满分子,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主张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状的力量。当时至少出现了这三种力量的博弈。每一种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说清政府内部,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他代表的北洋力量几乎超过了皇室的力量。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新式的北洋陆军,其他各地新办的新式陆军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手里。所以,我们看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不是一场纯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它是在武昌工程营几个士兵首先起事,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暴力冲突,长江流域就传檄而定,各地就纷纷独立了。各地独立的基本力量实际上也不是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举足轻重,是朝廷不能完全控制的力量。清廷面对这样的格局,选择了一个禅让的方式,它说的非常体面,只是交出政权,继续保持皇室的尊荣。在孙中山代表的革命阵营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都听孙中山的,他仅仅能掌握同盟会的一个派系,名义上他是同盟会领袖,但是在同盟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并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组织,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跟他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宋教仁、陈英士他们成立的,在成立宣言里面甚至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他们对于向来很敬重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也颇有微词。浙江、安徽一带的光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合并到同盟会里面。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说,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兴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他们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事实是,这三个会从来没有以会的形式合并过,也就是说不是组织上的合并,华兴会也是一样,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开会研究要不要取消华兴会,讨论的意见是既然大部分骨干都已加入同盟会,华兴会就不要活动了。兴中会整个转入同盟会,兴中会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光复会只是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同盟会,但光复会的名称一直保存着,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活动,从来没有说它们被同盟会取而代之。仅仅两年以后,1907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为了经费的支配、筹集等问题,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的主要人物都脱离了同盟会,自立门户,重建立了光复会总部,重新去发展自己的组织,跟孙中山派系争夺筹款的资源。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从来都没有。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103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我们现在对晚清历史很多地方都矮化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决策者已经感觉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她开始意识到严峻的危机,不光来自外患,还有内忧。当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较完整,从地方到中央把整个官制都改过来,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农商部、学部、交通部这样的新机构都已经出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延续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简单的行政改革范畴。清末新政带来的最大一个遗产就是地方自治,它给予了各个地方成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实质性地去做了。咨议局的选举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它有一个最低财产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来确定选民资格和侯选人的资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这样,在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我们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这种度量、这种开放。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变革社会,而是自上而下的统治,一个圣旨下去一切都解决。但是,咨议局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跨入一个农耕社会陌生的状态。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带有准议会性质、名义上当作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由各省咨议局选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选自己的代表共同组成,皇室的比例占了1/2强,在人数上略多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一些老朽,一些没有什么新知识的人,所以开起会来,整个会场就被那些地方选举上来的代表给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发言,那些官选代表无法对话,压根就没有对话的能力。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数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会场里,哪怕只有1个人说出“我反对”,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国,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窜起来。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到了新疆,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坐马车从北京去新疆要很多时间。他拍下了新疆咨议局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院,却赫然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新疆咨议局”牌子,门口有一棵老树,掉光了叶子。看了这幅照片,我的感觉是,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跟现在无法比,如今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可能就富丽堂皇、豪华奢侈。那个时候一个省级议会机构不过是几间平房,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院落。但是这不要紧,那块牌子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牌子就意味着新的因素。
当时的清政府和社会已经出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做这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主动放弃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让民众来分享的,开明君主的“开明”一定是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要到历史中去寻找,他们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主动地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包括蒋经国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走向民主化,他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压力,是综合的因素迫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一个统治者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离不开他主观上的决定。所以哪怕是不情愿的,是假的,最后弄假成真了,我们都得肯定这个统治者的这一举措,历史上还是要给他写上一笔。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他做了这个事,就要把它用刀刻在一片一片的竹简上。
有了朝廷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到了清朝快要崩溃前几年,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而且历史的步伐已经迈开了,但是它的步子慢了一点,被革命的步伐超过了。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终是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哪怕他们的人数最少、力量有限,哪怕他们都被赶到海外去了,但它始终在场。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弱小就不存在,而且所谓的弱和强是可以转化的,有时候它的转化可能就在一个晚上。我们看东欧的当代历史,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演讲的时候还是威风八面的,他在台上侃侃而谈,那么的从容,转眼之间攻守之势易也。历史不能完全用量来衡量,有时候数学在历史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它是无法进行精密计算的,数学算不出历史的尺度,数学也算不出王朝更迭的时间,数学更算不出历史未来变化的趋势。很多的时候,量的因素在历史当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概而言之,一个社会产生了两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且没有一种可以把另一种立马吃掉的那种格局下,是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
当然,和平转型需要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遭遇一个大的契机,这个大的契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性的背景。世界进入近代之后,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把自己画地为牢,关起门来玩家家了,尤其不能再按照历朝历代玩过的旧玩法,它要融入整个国际政治新格局当中。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人,他们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人。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甚至是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多次介入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跟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交。武昌起义之后,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利用给《泰晤士报》写电讯的这个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其影响之大,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他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英国介入中国的政局,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很不希望外国人介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历史就是有悖论,就像租界的存在一样。租界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有法外治权。但是没有租界,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要彻底地改写,包括中共的党史。没有租界,毁灭一个新生事物,毁灭一个密谋组织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有了租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租界也好,外国力量对中国的介入也好,我们在看到它负面影响的同时,应该也包含了一些正面的因素。它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当中,有时候往往起到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英国人对中国的国策是什么?它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中国不能大乱,中国要保持适当的稳定和秩序。它不想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动荡的局面,它希望中国保持相对的统一。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事实上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因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强人,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机会。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立宪派就是建立在中国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中国的企业都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最初几乎都是以军工企业为主,没有什么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企业除了几家官办的大企业之外,其余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后,是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要赔款、割地。这个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正是这个条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张謇,他是1894年的状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亲死了,按照惯例,他要在家守孝。就在这个期间他在南通创办了一个有名的大生纱厂。与此同时,在交通发达的长江流域开始出现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屈辱的《马关条约》刺激之下产生的。现在看来《马关条约》还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没有它的刺激,民营企业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起来。到清朝灭亡之前,民营企业已初成气候。特别重要的是清王朝居然在1905年到1909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从今天来看,那个年代连破产法都有了。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走到非常前面,从这些经济立法的脚步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状态,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践,空洞的立法怎么可能出现呢?一般来说都是实践推动立法,当然也有例外。新的工商业的崛起意味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运作方式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统治方式,更新政治结构。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以说就是一种回应。预备立宪之后的中国就不是一个朝廷说了算的中国,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几种力量并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力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清朝末年发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社会上相对有钱一点的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绅、资本家,办企业的人、开当铺、钱庄的人,一些家里有私产的人,这些人是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同时又都是读书人,他们有文化,又有经济的支撑。在这场历时两年、先后有三次高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革命党人,而是来自社会中层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这种挑战。这些人在社会的变化当中已经看到了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大势。他们认为如果继续延续旧的统治方式,君主传统将保不住,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要发展经济,要争得更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要推动君主立宪,就要把预备立宪变成真的立宪,这符合中产阶级以上的最大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满清贵族,连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他们的屁股也开始坐到立宪运动的板凳上来。整个中国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不过我们从来不把有钱人参政议政的愿望当作是革命,认为那个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恰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制度,而有一些主张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复制前面的制度,这一点,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过了。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专制,而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有可能成为真实的解放,那就是自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别人给你的解放都是要打问号的,人家怎么可能解放你呢?如果说承认别人有解放你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承认世上有救世主,只有救世主才可以解放别人,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的过程,个人的解放也是自我解放的过程。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加入不发生辛亥革命,就按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下去,也完全有可能走通的。但历史不能假设,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记录下来。清朝到了1910年都还有一个机会,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也失去了。当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经办了14年企业,手里掌握巨大的资本,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威震东南的社会新兴阶层的领袖人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在一次跟外商见面的宴会上面透露了一些不寻常的信息。这个外商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了他们一次饭桌上的对话,张謇竟然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对清王朝的不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像张謇这样状元出身的士绅阶层都已经跟清王朝离心离德了。1910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异心,对王室不忠的异心。在这个之前,他们都非常热心地去做国会请愿运动。结果他们一次、两次、三次遭到拒绝,实际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一张时间表。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就是一张时间表的问题。清王朝那个时间表的分歧非常小,双方的要求只相差两年。民间的要求是立即立宪、开国会、颁布宪法,朝廷给的答案是在拖两年到1913年再解决,但是1913年就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如果说立宪运动的要求被清廷接受,和平转型在那一刻就实现了。国会开了、宪法颁布了,君主就是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宪的框架就可以确立起来。我们不知道清廷拒绝这些要求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可以知道当时的清廷也面临着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的东西。它的皇帝是个小孩,是由摄政王载沣来具体管理国家政事,但是载沣又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所以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是一个多头政治的状态,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载沣不是,隆裕也不是,她虽然可以约束摄政王,但不能具体管理国事,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不利于变革。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路面只说了104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国民党在开放党禁、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内部并没有达成高度的统一,没有中委开会充分讨论、做出决定,就是蒋经国决定了就可以了。人家服从他、信任他。权威有时候也有权威的好处。历史经常有这样的悖论。清朝末年缺乏一个说了算的权威,也使它失去了一个接受民间要求迅速开国会、立宪法的可能性,接下来辛亥革命发生了。辛亥革命是有限的暴力革命,不是无节制的暴力,杀虐不是很重,而且时间很短,没有发生大的南北战争。这个辛亥革命看起来就是整个清末民初和平转型进程中的一支插曲,一支类似于放鞭炮的庆祝性的插曲。[1949年毛泽东站到天安门城楼要死多少人,据说死了两千万人,用两千万人的血换来的,而辛亥革命的伤亡数字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应该说这样的转型还是在相对比较和平的范围内实现的。]
和平转型的重心从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春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报纸一下子出现了500多种,今天听来,认为500是一个小数字,但在那个年代有500多种报纸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政党和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个,当然经过分化以后留下来的不多。1912年冬天参众两院的选举跟咨议局的选举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选民资格的四个条件是: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文化强调同等学力,那个年代的人不重视文凭而重视能力,第二个条件是财产的限制,我们看西方的选举史一直就有这种限制性条款。虽然有条件限制,选举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个别的越轨,包括极少数的买选票行为。但这并不表明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恰恰说明了这种选举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当时叫中华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来可以慢慢改变的,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非常有意思,有人把咨议局和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作了一个比较,咨议局议员大都有旧的科举功名,秀才以上,有的是举人,有点甚至是进士,以秀才为主,有个别是新式学堂出身,也有从海外归来的,但是不占主流。就年龄比例来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占多数。到了民国选出来的参众两院代表平均年龄是36岁,都是少壮,学历有个别是旧科举功名的,绝大部分是新学的,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或者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下子面目全新。当时这个两会选举结束,宋教仁就踌躇满志、志得意满,认为成功了,袁世凯已经成了掌中之物了。因为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法律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相结合,内阁总理要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意味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成为总理。当时还有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签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那就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所以宋教仁非常兴奋,以为凭宪法、国会和内阁这三样法宝就可以约束旧官僚、旧军阀,让中国走上宪政的轨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要拿出铁血的精神拼命,现在我们是普通政党,就要拿出自己的政纲来去跟他们奋斗。这几句话非常到位,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了。普通政党就不是天生的执政党,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的,没有足够的选票,你就得在野。1913年春天,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胜利在握,但就在这一刻他被暗杀了。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
民国初年的两院选举是完全建立在晚清宪政的基础上的,中间的辛亥革命是个插曲,它并没有中断和平转型的进程。一个社会在大的变迁过程中,怎样不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冲突,怎样避免出现长期的乱局,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局,这是需要政治家、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精英、企业家阶层,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能够运用自己高度的理性,付出最大的努力去达到这个结果,这是合理的构成,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组织可以做到的。历史变革的进程出来不是一家所决定的,包括那些暴力最强大的、大一统的新天下,在造成之前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众所周知,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选择了暴力反抗,组织了“二次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当时叫“赣宁之役”。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国民党用武力造成了一个新政权。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给中国带来再一次和平转型的新机会。这个机会是,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的条件,当时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势力主张中国走和平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了中国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机会,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之程度,也让我们今天很惊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其实和平的呼声非常响亮。特别是国际压力,所以蒋介石才会一而再地从重庆发电报给毛泽东,请他到重庆来。这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党,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武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都是统一的,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是我们今天可能已难以想象,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罗隆基一生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弹,而靠才智发言的时代。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每一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可以讨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讨论完了,双方还可以握手言欢。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产党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双方有可能是对立的,分歧很严重,但是可以坐下来协商。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协商的格局当中的社会团体,批评他们那些党派开的是分赃会议。中国这么大,怎么只有这么几家坐下来谈,其他人怎么办?跟这些党派都没有关系的人更多。那个时候选择各种政治党派基本上是基于信仰,当然也有机会主义的人,这个永远都避免不了。有一个党叫中国青年党,是跟国共两党同时崛起的一个党,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国家主义派别。这个政党鼎盛时期党员有四、五万人。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等岗位上。中国青年党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后来分裂出来。民盟为什么影响比青年党大,因为民盟都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会议,能够坐在桌子上谈判的代表,国民党8个、共产党7个、民盟9个、青年党5个、无党无派9个,其中有出版家王云五、报人胡政之、银行家钱新之、实业家缪云台和李烛尘、学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郭沫若是红色背景。这样一些人坐下来讨论,讨价还价,刀光剑影,唇枪舌战,最后终于达成了五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非常的细致,里面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都非常好,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包括改组国民党主控的国民政府方案,怎么样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选举一个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民大会,代表比例怎么分配,原来的老代表承不承认,这个争论是最激烈的。还有一个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也达成了原则性意见。除了这四个文的方案,还有一个武的军事整编方案,共产党下属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按什么比例整编都已经谈妥了。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带入了西方主流世界的共和国。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五个协议,最终还是以武力决出了胜负。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会接不住?我个人有几个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如果中国同时并存两个拥有武装的打天下集团,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则是不会罢休的。他的这个说法放在1946年的中国来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国共双方都掌握着大规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战争、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一个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负责任。当时民盟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都普遍有一种思想上的模糊,这有时代的原因,他们对苏联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民盟有一个中常委张东荪,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民主社会主义,又叫做新民主主义,跟毛泽东的表述完全是同一个词,但里面的内容略有区别,但大同小异,最根本的是八个字“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当时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骨子里面信仰的是这八个字,他们认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样板,苏联提供了计划经济的样板,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好,有些人穷,有些人富,计划经济好,由国家按计划来搞经济。他们没有看到苏联本国发生的问题,比如饥荒,这些负面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苏联解决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的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等问题。他们设想,如果把苏联和英美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完美的模式。他们忽略了在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或社会制度当中都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这个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决,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种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个时候他们还看不到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左的,都是中间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间偏右。这就意味着在有武力的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本身就带有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这是导致和平转型破产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三个原因,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国际势力,特别是苏联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论证。
历史留给我们中国人和平转变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暴力造成的,连伟大的、创立民国的孙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见到张国焘、许德珩这些“五四”学生时,竟然对他们说,你们搞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很了不起,有点作用,但这只是赤手空拳,我给你们五百枝枪,你们敢去干吗?这番话流露出来的那种心态大成问题。就是说连孙中山这样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最终走的道路就是黄埔建军,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是国民党专政的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连孙中山这样的人,现在看来已经够伟大,要给他足够多的正面评价,但就是他这样的人物身上也带有这么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倾向,要让中国人从暴力的传统当中超越出来,确实非常艰难。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说一种宿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当然,这些努力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不是完全无效的,总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迹。真正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努力背后,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天命”,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命不太一样。传统的“天命”讲皇帝是天命,君权神授那些东西。在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改变历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挽回的。历史的一次扭转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编年史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只要写一句话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写西方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未来五百年之后去写历史,当代史也许只需要几个字去表述,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个未知数。这就是天命,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尽人事,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不会等于零,为什么不会等于零,因为它可能在编年史的竹简当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划痕,这个划痕也许很轻,但是它会留下。因为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紧扣。古往今来,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人物都在历史中化为烟尘,化为粪土。所以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等于零,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义和团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个时段看起来也许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主义,主义都是人为的、强加的,主义多了,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纷争。我看晚清到民初的这段转型,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讲主义,人们所追求的方向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要把中国从古老的帝国带入一个新的民国。从帝国到民国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抗日战争胜利后就是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目标都很清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主义,主义的纷争都是在社会和平转型的契机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分歧还不是主义的分歧,选择的路不同,但最终要回到一条路上来,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类的历史证明一点,那么多成功完成制度转型的国家最终靠的都不是枪杆子。我们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但那种武力都是有限武力,那种暴力也不是绝对暴力,那种暴力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假如说华盛顿的军队跟英国皇家的军队真的要血战,当然也打过几次硬仗,它是耗不起八年的。华盛顿的军队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象征性的武力征战,类似于当年曼德拉要搞“非洲之矛”一样,他不是要打人,而是要打建筑物,他的武力是象征性的,是有具体目标的。我觉得中国人失去了那两次机会之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历史就走到了今天。
(根据作者2007年8月在北京@中国律师观察网“博闻讲坛”的讲演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