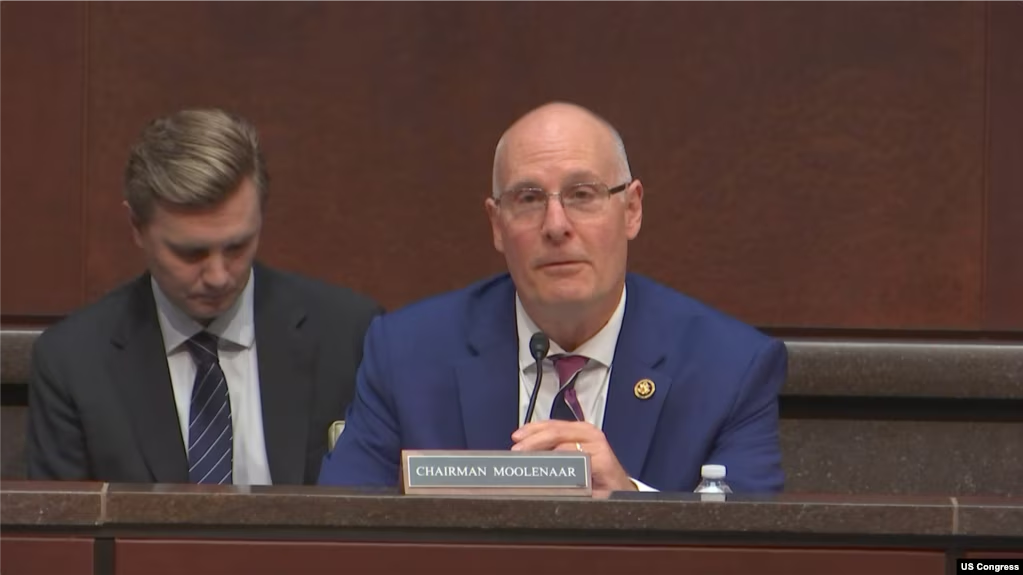主持并记录:武宜三
参加者:铁流、李昌玉、俞梅荪、嘉宾几位
时间:二OO七年二月一日
地点:香港某酒店
武宜三:首先欢迎诸位光临香港。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我们趁此机会座谈一下,也算是小型研讨会吧。铁流先生,原来叫晓枫,是《成都日报》记者,成都“七君子”之一;李昌玉老师是山东大学附中老师,十六岁参军,投身革命;两位是当年的罹难者、幸存者。俞先生尊翁被打成右派后跳楼自杀;几位嘉宾的家族中都有人被打成右派,有的甚至不止一个。现在请铁流先生先讲。
中共的残暴并不自反右派始
铁流: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官方公布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六万,现在大约还剩下一半;再过十年,可能就死得差不多了。四川所谓“七君子”,死了三个,还有四个;我算年轻的,也七十二岁了。我认为,必须抓紧反右五十周年的机会来反思反右问题,因为过了五十周年就没有六十周年了。
中国一切的灾难都是始于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年之前,中国多少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空间。各民主党派还可以给共产党建言,知识分子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九五七年之后,所有言论都被封杀,中国进入了完全专制、独裁、黑暗、封建的状态,其专制、独裁、黑暗、封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讲假话、吹牛拍马、出卖人格、出卖朋友,越演越烈,大跃进亩产十三万斤,一头猪一天长二十斤,一条苞谷可重二三十斤,一切假话都说得出来。
没有一九五七年,就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也就没有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四千多万人;没有一九五七年,就没有反右倾、四清运动,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我写过《中国死于一九五七年》,指一九五七年是彻底走向独裁、彻底背叛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作的承诺的分水岭。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应有重视。现在对六四事件,大家都很重视,香港甚至全世界每一年都有纪念活动;但对一九五七年,却基本上被遗忘了。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最年轻的已七十一岁了,老的则八九十岁;其中很多人还心有余悸、不敢说话,把痛苦、灾难深深埋在心中;这些人中,大部份知识老化,不会上网,对外界不了解。现在懂上网的右派,据我所知只有十来人。流沙河,一九五七年因《草木篇》被打成右派分子,但直到今天还未为反右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有的人怕影响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还要靠共产党吃饭。
在海外搞媒体的多是五十岁或以下的人,他们对文革、六四有认识,对反右认识就很有限。所以海外网站上,反右的题材就很少。
武宜三:其实中共的残暴并不自反右派始,可以说自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直至今天,中共始终都被一条谎言加暴力的恐怖路线所统治,杀AB团、苏区肃反、肃托、整风抢救、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哪一次运动不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作为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的最近五十年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在大陆有一种说法:六十岁的不知道反右,五十岁的不知道文革,四十岁的不知道华国锋,三十岁的不知道四五,二十岁的不知道六四。历史正被肆意篡改、歪曲、抹煞、掩盖……
铁流:我是童工出身,十五岁出来打工。本来是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可是共产党也不放过我,因为一篇所谓干预生活的文章《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把我打成右派分子。当年三个人写了所谓干预生活的文章,我、王蒙和刘宾雁;这三个人都是共青团系统的大右派。《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共共八千八百字,被关押了二十三年,相当于一个字关一天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差一点被杀掉。发生在我身边血淋淋的事件太多了。一九六二年,我所在的四一五筑路支队,是四川省公安厅的劳改队,一万多名右派集中在一起修铁路。四一五筑路支队从一九五八年成立到文革时期解散时,死于公伤、饥饿,被打死、枪毙的,逃跑的,占了一半。
中国共产党杀了多少忠诚党员和真正爱国者?
当时有个「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我是涉案人之一;周居正、杨应森被枪毙。周居正是一九四五年的中共地下党,一九四七年他领导重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大游行,被国民政府抓捕,关在重庆渣子洞;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和关在一起的难友罗广斌等人绣红旗迎接“解放”,红布是罗广斌的被面。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们怀疑国民党会血洗渣滓洞,便组织越狱,他在枪林弹雨中还身背一个四岁小孩,这小孩叫郭德斌,后来在天津当了工程师。周居正没有死在国民党枪下,倒让共产党自己把他杀了。
他不过给党委提了几条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接着开除党籍、公职,送劳动教养。在劳改队里因对饥饿、劳累表示过不满,加上当时苏联共产党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肯定了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有人跟着说了句,我们也要有马列主义联盟,被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右派分子姚某所告发;四川省公安厅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举抓了二百多人,用逼供信的办法,一个咬一个,咬出了六十九个,并定周居正为反革命集团首犯。
周居正临刑时,监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来?周居正说:“告诉我家里人,要相信党,一定要跟党走。”从周居正临死的遗言看,他何曾反党?然而,周居正被枪毙后,他两个儿子备受歧视、侮辱,无法存活,一个以镰刀割喉、一个跳了嘉陵江,都死了。
武宜三: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中国共产党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忠诚党员和真正爱国者。
铁流:重庆渣子洞还保留有“志士周居正”五个字,《红岩英烈》中也有他的姓名,但是他被杀掉了,以反革命的罪名死在他拼死为之奋斗的政权的枪口下。几十年了,直至今天,也没给他平反。
杨应森当过志愿军,是解放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官,因议论“军队国家化”被打成右派,因“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案,一九六四年三月被枪杀。我和他关在一起三个月,临刑那天,因为手反铐着,让我把他洗得发白的军帽帮他戴上,他说:“晓枫,我要走了,你要保重。”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然而,杨应森都做到了。(铁流先生讲到这里,哽咽流泪,仍难抑悲痛之情)
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精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些人就这样被摧残、被虐杀。但当局仍不承认反右是错误、是罪恶,只说是“扩大化”;所以,不彻底清算反右派运动,就不能动摇共产党的独裁本性,“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就没有希望。
嘉宾甲:我同意铁流先生意见,我在媒体上写文章也阐明这个观念:一九五七年这场运动不仅是几十万右派分子和他们家属的灾难,也是我们民族的灾难;而且是不可估量的灾难。这场运动是其后一切罪恶的根源,它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失言;以致对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干了那么多指鹿为马的荒唐事,没有人敢出来说话。知识分子,有些还是大科学家、大文豪,也在助纣为虐,钱学森居然胡说八道:只要充分吸收太阳能,亩产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斤。郭沫若、巴金都是“大跃进”吹鼓手。因为说真话没有好下场,只好说假话。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征过头粮通行无阻,于是饿死了几千万人。
彭德怀良心未泯,说了几句实话,又引发了反右倾运动,抓了三百八十万右倾分子。刘少奇本是支持“大跃进”的,但对于饿死几千万人,他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然而,刘少奇的这句话为他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中共对右派分子的群体灭绝
李昌玉:对右派的惩罚,大概不少于一半的人送去劳动教养,这是非常残酷的惩罚。各省的省级机关、高等院校的右派分子一般在本省劳改农场劳改,如甘肃省的夹边沟,四川省的四一五信箱,山东省的王庄。山东王庄规模也很大,是个有上万人的劳改基地,有农业、矿山、工厂等。县里的右派一般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也有条件好的地方往艰苦的地方送,如上海市的右派分子送到甘肃省,北京市的送去北大荒。
嘉宾乙:夹边沟当时饿死很多人,最高峰时一天死六十四人;都是些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新闻工作者,还有工人和学生。以往熟悉的圈子里,几乎家家都有死人。夹边沟的大规模死人,最终惊动了北京,因为死者中有些是高干亲属。中央派内务部长钱英下来,钱英亲自到右派分子们住的洞穴里去看,有些洞穴仅能容一个人爬得进去;里面没有取暖设备,当时气温是零下三十度。那些右派又饿又冻,一个个骨瘦如柴。于是北京指示“抢救人命”,没死的让家属领回家,叫回原单位。在“抢救”过程中仍然不断死人,一天也有死二三十人的;有人饿久了,一吃东西反而“胀死”;有人就死在回家的火车上;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
嘉宾丙:有资料说,当时洞穴里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有个人说是死了,刚好他老婆来;他老婆一摸他还有一口气,就用咀嚼过的馍喂他,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了。当时有一些女人凭着她们坚韧的天性,给了男人一个支撑,结果有人就挺过来了。但更多的是在政治高压下,划清界线,夫妻离异;许多人垮了,自杀了,就是因为被家庭所抛弃。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给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带来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人性、人伦荡然无存。由于传统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制度的弊病,又造成了今天的全民腐败。所以,反右运动确实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几十年灾难的根源。我们必须反思历史,从体制、文化、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加以反思。否则死了这么多人、流了这么多血、受了这么多苦难、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例如铁流先生坐了二十多年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避免这些灾难的再一次到来。
武宜三:积我几十年的观察所得,共产党是和所有美好的东西过不去的。你有好的生活,它把你破坏掉;你有好的家庭,它把你拆散;你有好的学问,它叫你去扫厕所;你有好的思想,它把你批臭;你有好的身体,它把你摧垮、甚至杀掉。小到中南海花圃,大到北京城墙,必拆之而后快;上自文化、道德、伦理,下到戏曲、音乐、图书,不毁之不得安生;如今沙尘滚滚、森林绝迹、江河污染、农村凋敝、满目疮痍,哪一样不是共产党的“德政”?昌玉老师的坎坷一生,也很能说明问题。
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
李昌玉:我出生于一九三四年,略大于铁流,十五岁入团,十六岁半参军,对党忠心耿耿,我的女朋友送了本红彤彤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给我,以成为布尔什维克相期许,真是“风流蕴藉,百年绝唱”,这样的故事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在“革命大家庭”里,我也真的追求进步,给《解放日报》等写过稿,被请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演讲。但是实际上,军队里也充斥着冷酷、恐怖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我虽然只是个初中生,就已经很受排斥了。肃反时,我成了后勤部揪出来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我在军队呆不下去了,一气之下,一九五六年去考了山东大学。因对肃反还是耿耿于怀,一九五七年趁大鸣大放之机就写信要求平反,结果成了右派。后来摘了帽子,文革时还提出平反,再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了二进宫右派。
反右后还有个一九五九年的拔白旗运动,把右派以外的人又排了左中右,分为三六九等。我的一个同事王显柄,崂山人,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被评为中右分子,由于受到严密监视,一言一行均为积极分子所记录,文革开始时成了昌潍地区、平度县、华侨中学言论最多、质量最高的反革命分子。由于不服气,文革十年中王显柄反反复覆地和整他的人对着干,不惜以鸡蛋碰石头,有一次被殴打后昏睡了一二十天,使他的精神受到巨大冲击、肉体受到严重摧残,最终在不足六十岁的时候憾然逝去;而整过他的人,有的入党,有的升官,皆大欢喜。
潘仁山,我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学,也是中右,开除了团籍;整他的人叫郑若范,是个女的,党支部委员。后来这郑若范因和历史反革命的丈夫离了婚,又和潘仁山结为夫妇。文革中这一对夫妇互向对方转化,男的越来越左,左到被邓力群的《中流》所罗致,女的反而思想越来越开放。
我们中文系五六级一百零五名学生中,打了八个右派;后来“改正”时,找出的材料是十个。原因是名额够了,超过百分之五了。我是第八个,前七名是一九五七年宣布的,我是一九五八年补上的,那两个成了漏网之鱼。
武宜三:所以,我对五十五万这个数有保留。一从县的数字算,抓右派分子最多的县是河南南阳县,一千一百六十四名(而全南阳专区抓了八千七百二十七人,县平均八百多人);抓右派分子最少的县是黑龙江省嘉荫县,全县仅六千余人,也抓了十五人。其它如湖北省襄阳县是八百五十二名,随县是七百四十一名;安徽省全淑县是四百四十五名,休宁县三百三十九名;四川省新津县右派份子一百三十一人,仁寿县四百六十二人;山东省庆云县仅中小学教师中就抓了八十二名。江西省万载县抓五十人,高安县一百一十名。内蒙古巴林左旗抓了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丁抒:《阳谋》)。取最多和最少平均值乘以两千多个县,粗略推算是一百二十万人以上。二,从省的数字看,河南省抓了九万人右派分子(《李锐近作》),考虑河南省不是人口大省,但不考虑京、沪、津高校密集、知识分子集中、右派分子比例更高的因素,姑且把这九万打个对折,即四万五,与广东省打出的六万五千多名比,还是保守的;四万五乘上二十九个省市,约为一百三十万。
加上同样享受右派待遇的「中右」、「内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份子」,总数将是二百万以上。还有反右派运动副产品,如广西上林县除在教师中抓右派外,还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辽宁省海城县,除抓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竟多达二百四十八名;四川省什邡县抓了一百二十一名右派后,在工人、农民、城镇居民中又抓「反社会主义份子」九百七十八名。这个数字将更加庞大了。
草菅人命,杀人如麻
李昌玉:我那年级有叫朱玉标的,和两个同学一起上街,有一个说:“朱玉标你胆子大,你说句最恶毒的话看看。”朱玉标就说一句:“打倒共产党!”结果这个人去告密,朱玉标被秘密处决了。
武宜三:所有人的个人祸福、政治际遇、家庭离合,甚至肉体的存废,在党的眼里都一文不值,可以任意处置。
李昌玉:我班上的徐邦志,无锡人,是《上海青年报》的编辑,人很聪明,单位对他也不错,到山大后还给长了一级工资转过来。他有个习惯,见纸就写字;三年大饥饿期间人祸期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随手在一幅号召“大养其猪”的漫画上写了“毛主席”三个字,其实是下意识的活动,让旁边的同学看到了,报告上去;结果徐邦志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马上送去劳动教养。
还有叫郝常磊的,参加过三青团。他本来考上了一个美术学院,后来又跑到山东大学来。又有个叫朱迪的,现在社会科学院;朱迪油画也画得好,所以经常和郝常磊在一起。有一次郝常磊对一个也是爱好艺术的同学说到一丛花:“看,社会主义的花,连蜜蜂都不叮。”结果,朱迪去汇报了。郝常磊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在文革中上吊自杀了。朱迪从此不与同学来往,毕业后也从不参加同学聚会。
武宜三:告密者手上染着别人的血,一辈子也不得安宁吧。只是这个社会太恐怖了,这种事可谓俯拾皆是;希特勒的德国和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也只能瞠乎其后。
嘉宾乙:这是一座可怕的绞肉机:他今天害了别人,明天别人又来害他。
李昌玉:关于反右,还有一个惨痛的例子。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广西日报》正面报导了该省环江“包产到户”的消息;同月二十七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专题报导。但不幸的是,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派: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
王定的继任人洪华,放出了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大卫星,大出风头;当时有中央各报记者,有农科院院长,各级官员在场,而且还要签名作证;结果全县人口从一九五九年的十七万降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二万,算上新生的,净减五万人;也就是说,饿死了百分之三十。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这县还造了另一个假,日产钢铁五万吨,原始森林都砍光、烧光了。广西省还有荔浦县,该县机关,包括县党委、县人委的干部,有百分之七十被打成右派。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很多右派青年作家,如丛维熙、王蒙都出来写文章了。那些掌握很多资料、有地位的人本来应该站出来说话,他们却不对反右置一词。他们不说,我就自己说。我本来一直谨小慎言,规规矩矩;但想到七十多岁了,再不说什么时候说?很多人也这么想,所以史若平老师的呼吁信得到很多人响应,有超过一千人签了名。
武宜三: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就是“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然而那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恰恰忘了马克思这句话。
李昌玉:今天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否定反右运动呢?当然不仅仅是根据个人的得失利害。我们个人何必冒犯巨大的政治风险出来说话呢?枪打出头鸟的教训,我们看得还少吗?因此,作为中国人,最大的精明事故就是不为人先,坐享其成。比如,在我们单位里,常常有些人,邀我参加一些争利的活动。我说:你们去争吧,反正是有了也少不了我的一份。但是,反右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有一位北大的著名教授,叫做孔庆东的人,后来我听说,他的名气可大了,他的书可好卖了,就是这么一位大学者大才子,竟然说:“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右派)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我们且不说对右派是不是只“批评”了几句的问题。照这位大教授的想法,该怎样对待右派呢?他说:“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好家伙,我们大教授的想法是对右派“枪毙”、“全部消灭”。我真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是他老人家仁慈宽大,没有对右派“枪毙”、“全部消灭”,所以我苟活到如今。孔庆东先生说:“改革开放之后,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那么,按照这位北大教授的逻辑,毛主席是养痈遗患,留下这些恩将仇报的坏蛋,现在跳出来反攻倒算,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了。我刚刚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孔庆东,一位欠缺常识的北大教授》。从我们这些经历过历史的过来人看,这位大教授实在是欠缺常识。
大家要知道,孔庆东不是一个两个。在中国多得很。因为共产党至今仍然把反右、文革列为言论、新闻、出版的禁区,使人们对这些历史真相,一无所知。就凭了孔庆东的思想,我们还苟且活着的右派,也应该拍案而起,站出来说话,把历史真相说出来。
正本清源,坚持民主与法治
俞梅荪:我爷爷俞颂华是老报人,一九一九年为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刊载在上海《学灯》杂志而扩大了影响;一九二0年,他二十七岁时带着为他当翻译的二十一岁瞿秋白,去苏俄采访列宁、莫洛托夫、托洛斯基等苏俄领导人和那里的情况,发回不少中国最早有关苏俄革命情况的通讯报导,是中国第一个海外记者。一九三七年,红军到达陕北,他又去了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张国焘,在上海《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的照片刊在杂志封面上,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瞿秋白就秘密住过我家。我父亲受我爷爷影响,掩护中共地下党,一九四五年他随我爷爷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聚会;我父亲是金融专家,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拒绝前往台湾,共产党派他来到北京,参与创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参加开国大典,他参与制定保险政策和各项业务规章,对保险事业有所贡献。
一九五七年,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召开座谈会,要求大家提意见。父亲指出:“我国‘解放’以来,全国的保险业一会儿要发展,一会儿要收缩,方针政策摇摆不定,影响了业务的开展,广大保险从业人员还是应该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人民日报》报道后,他因这几句话而受到批判和人身攻击,成为右派分子,跳楼自杀后又被开除公职,仅三十一岁。当时我四岁、弟弟一岁。
我奶奶热爱共产党,“解放”初期是上海市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接管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成员、业务骨干。因我父亲问题的株连,奶奶被迫退休,母亲下放北京农村劳动,我们两兄弟被送到上海由奶奶抚养。我和弟弟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又因父亲的问题而备受歧视,弟弟在文革中服毒自杀被救以后患了精神病,反反复覆三十六年,至今仍长期住在精神病医院,一个大好青年的一生就这样毁了。
我当农民、工人,靠个人奋斗,一九七九年加入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国务院当秘书,从事立法工作。一九九二年应中共上海《文汇报》的请求,支持其做好中共十四大的方针政策和法治宣传并取得成效,却被诬陷成“泄密”罪,在狱中自杀未遂,为了我党的事业坐了三年牢,又妻离子散,母亲晚年因我而贫困直至病逝。
从我本人的冤案至今十四年仍求告无门和近年来参与失地农民维权来看,中国的司法、执法充满着坑、蒙、拐、骗。办案不是实事求是、不是为维护法律,而且为了「政绩」、为了邀功、为了上级的好恶而践踏法律,漠视群众的疾苦,甚至漠视生命、滥杀无辜,制造了数不尽的寃、假、错案。痛感“反右”乃至“文革”等等,不仅仅是历史,今日仍时有发生,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一黑色幽灵时隔五十年并未消失殆尽,这是长期以来“左”的人治习惯势力而使然。为了下一代的安全与和幸福,必须正本清源,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树立公平与正义,民主与法治的规范。
武宜三:从以上各位所讲,我想我看到了两个问题:
一、凡亲共信共的、跟共产党跑的,都没有好下场。类似俞家这样帮过共产党、为共产党卖过命,却给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康心如一家、黄炎培一家,遭遇都非常悲惨;康家康心如、康心之、康国杰“一门三右”;黄家六子女、一个外甥是右派,如果加黄炎培本身这个“不戴帽的右派”,他们家就有八个右派分子;毛泽东说:“你们家左中右都有。”可谓极尽愚弄、作践、耻辱、挖苦之能事。铁流先生、昌玉老师,你们年纪轻轻就跟共产党搞革命,结果为了一篇文章、几句话,受了几十年苦难,辱及父祖,妻儿遭殃;共产党之反骨负义、恩将仇报,古今少见。
二、从根上讲起,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那一套、文革那一套在今天仍然盛行,专制和独裁还笼罩在中国上空、谎言和恐惧仍盘踞中国人民的心头;所以要正本清源,把共产党整人、害人、杀人的那条路线、那个思潮、那种体制,以及犯下的罪行、欠下的血债,都仔细、认真的清理、反思一番;这也许就是我们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的目的所在。谢谢各位。
四月十日整理、补充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