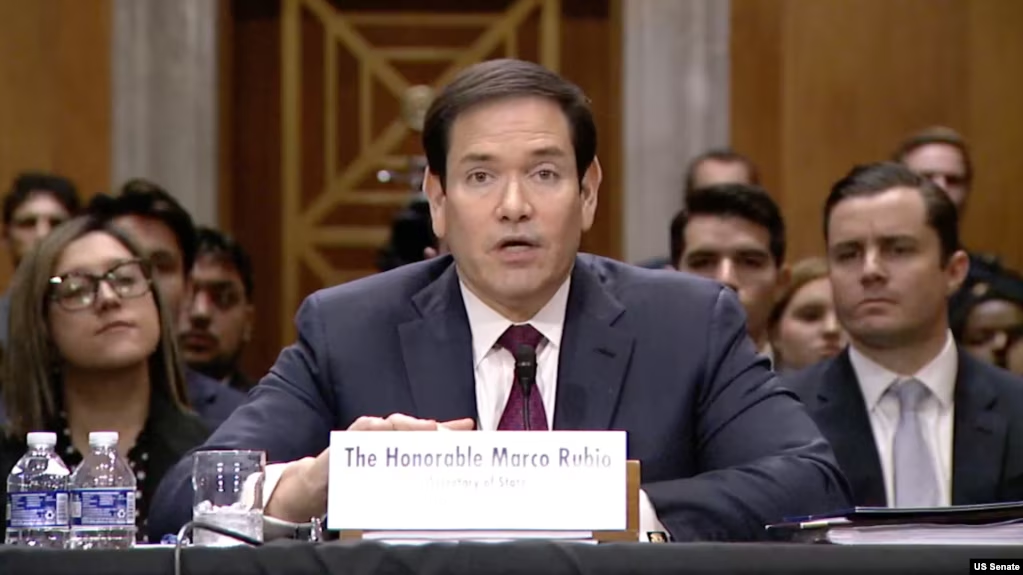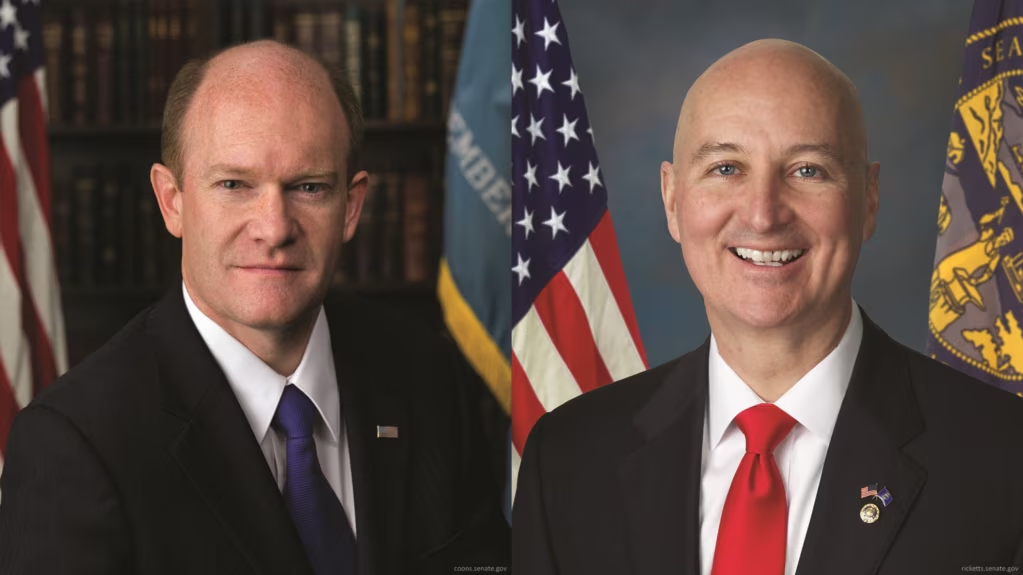四
在延安的共產黨幹部跟著毛澤東整日開會學習的日子,國民政府的抗日形勢又如何呢?1941年9月底和1942年1月初,國軍與日軍在長沙打了兩次大會戰,史稱第二次和第三次長沙會戰。國軍先後投入兵力五十七萬人,日方共投入三十六萬五千人。第二次會戰中,國軍的部分軍隊遭受重創,日軍攻入長沙,但在薛岳率部的猛烈攻擊下,日軍攻佔長沙不到三日,旋即狼狽撤出。國軍打了一個轉敗為勝的會戰。此役國軍殺敵兩萬零八千三百人,傷敵三萬五千左右。國軍死傷亦很慘重,陣亡兩萬四千八百多人,傷三萬五千二百多人。第三次會戰中,日軍企圖再次攻佔長沙,但在國軍的頑強抵抗下全綫潰退。雙方均付出慘重的傷亡。國軍陣亡兩萬四千八百多人,傷三萬五千二百多人。據國軍方面發表的數字,國軍共殺敵兩萬八千三百人,傷敵三萬五千人。19
1940年春,朱德應毛澤東之召從太行山根據地返囘延安,他此後再沒能親臨抗日前綫。朱德本有一個籌謀已久的作戰計劃,他這一走,就只能留給彭德懷獨自去運作了。為打破日軍對根據地的“囚籠政策”,切斷其交通命脈,朱德與彭德懷合謀組織八路軍各部打一次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朱德曾就這一計劃上書蔣介石,極言此戰役關乎全國戰局的重大意義。毛澤東對朱德在抗日前綫與國民黨積極配合的動作早就有所覺察,他急召朱德返回延安,就是想把總司令閒置在窯洞内無所事事。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彭德懷指揮八路軍執行了這個計劃,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八路軍在華北敵佔區發動多次襲擊日軍的戰鬥,在正太路沿綫破壞鐵路,切斷日軍補給綫,投入了一百多個團的兵力之多,因而號稱百團大戰。此戰役中八路軍傷亡一萬七千人,斃傷日軍兩萬餘人。中共對外曾極力宣揚此役的戰功,但毛澤東在黨内軍内卻對指揮這場戰役的彭德懷嚴厲批評,怪罪此役得不償失,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引起日軍大掃蕩,喪失大片根據地,導致八路軍極端困難。彭德懷因此遭到多次批鬥,直到文革中紅衛兵揪鬥老元帥,仍然舊賬重翻,糾纏不休。毛澤東爲什麽對彭德懷發動這場戰役如此不滿呢?從彭的檢討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另有其卑劣的用心。彭德懷自訴說,他組織百團大戰,原以爲日軍要進攻西安,直接威脅到延安的安全,因此冒險發動這次戰役,以阻止敵軍西進。但他沒想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粵漢路,是爲了便利進行太平洋戰爭。如果當時看破了敵人這樣的戰略企圖,那就再熬上半年時間,或者等敵人進攻長沙、衡陽、湘桂以後,兵力更加分散時,我軍再舉行這次大規模的破襲戰役……雖然在戰役上取得了勝利,但是推遲了日軍打通粵漢鐵路的時間(約一個月時間),而減輕了當時日軍對蔣介石的壓力。在客觀上是起到了援助蔣介石的作用。” 20 原來彭德懷挨批是由於毛澤東認爲百團大戰起到推遲日軍南下的作用,結果緩解了國軍在長沙和湘桂會戰中的壓力。在毛澤東心目中,與日軍作戰完全是國軍的事情,八路軍打擊日寇的行動不算愛國,而是幫助蔣介石,是犯了不聼他指揮的重大錯誤。直到多年後在廬山會議上批鬥彭德懷,毛仍訓斥彭說:“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沒真正改變他“抗日反蔣”的策略,難怪斯大林對毛的抗日誠意始終不放心,從莫斯科派出專職人員到延安探測監督他的言行。
百團大戰結束後,共軍再沒發動什麽值得稱頌的對日作戰。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記為我們提供了中共消極抗戰的衆多明證。他在1942年6月7日寫道:“八路軍並不積極迎擊來犯的日軍,他們只守護在自己的地盤内作散漫的應付。一旦日軍發動進攻,八路軍就退入山區,避免與日軍交鋒。”那年九月,弗氏去賀龍部所在的戰區進行考察,親眼目睹了八路軍消極抗日的實況。他看到,“軍中士氣不振,一片渙散,他們尸居素餐,一任戰局自然發展。……八路軍與日軍和平相處。日軍在他們的據點内安逸過冬,八路軍則在周邊消閒度日。” 弗氏說,他發現有一爲數僅四五十人的小股日軍佔領了幾個村莊,整個處於賀龍部大批人馬的包圍中。他問指戰員何以不率部去收復村莊,因爲打這一仗易如反掌,不該眼看著敵人在那裏安然無事。他得到的回答是:“他們有四百人,可不是四個人呀!……上級有令,不准我們去惹他們。要是消滅了這股日軍,就會招引來大批援軍。到那時我們該怎麽辦呢?我們不碰他們,他們也不會碰我們。”弗氏氣憤地寫道:“八路軍只顧盯準國民黨的軍隊,部隊中的宣傳也矛頭直指國軍,他們明顯在等待時機,與國軍決一死戰。他們這樣做只會長日軍的威風。”“只要日軍挫敗國軍,摧毀當地政府的政權,八路軍就立即趁虛而入。必要時他們甚至會殲滅孤軍抗日的友軍,從而攫取政權。”“毛澤東之所以命令八路軍採取日軍來犯即撤退的做法,是爲了坐收國軍抗日的漁利。當此國難時期,民不聊生,犧牲慘重,國家在日寇的蹂躪下存亡危急,毛這種策略也未免太背信棄義了。” 21
五
正是在共軍與日軍互不相擾的局面下,陝北特區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和平穩定。毛澤東一任國軍每日每時在前綫上流血犧牲,他自己只管埋頭窯洞中揮筆疾書,三天兩頭發文章作報告,帶領上留在延安的幹部以及前來投奔的愛國青年整日學習文件,開會討論,從黨内閙到黨外,從上層批到基層,把一場整人鬥黨的運動,斷斷續續搞到四、五年之久。“學習”現在被毛澤東部署為另一種革命鬥爭,被強調得比抗日殺敵更爲重要。他先是在“九月會議”後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無形中置換掉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職權。1942年2月,隨著整風運動開展起來,又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簡稱中央總學委)取而代之,由他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下設五個分區的學習委員會,統領整風運動,成爲全黨一切工作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毛澤東手下現在網羅進一批新提拔的幹部,除康生外,另有劉少奇的得力幹將彭真,陝北根據地的主將高崗,上海新來的左翼文人周揚,包括陸定一、王首道和毛的秘書胡喬木、陳伯達等人,都摻沙子到各學習小組中作領導,對尚留在黨内高層的國際派人物形成紛擾和鉗制。22 毛澤東的主攻對象當然是王明、博古和張聞天,但此時王在病中,張已下鄉,博古被降級使用,僅負責中央報刊。按照毛的攻戰路數,對他們將上一軍的打擊尚在好多步棋之後,他眼下首先要衝擊的目標是中央研究院。那個地方是他的“理論情結”最難以容忍的機構,因爲那裏的衆多理論家最讓他感到信心不足。正如高華所說,毛“從來就懷疑黨内那批理論家在内心深處並不承認自己,毛也猜度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認中共黨内有‘教條主義’一說。……毛澤東知道,對付這群‘紅色教授’,僅僅用説理辯論那一套糾纏不清的‘文明的方式’顯然是不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他們臭駡一通,使他們在劈頭蓋臉般的責駡中,斯文掃地,無地自容。”同時,“挑動青年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放火燒荒’,將青年的怒火引至國際派身上。” 23
但青年知識分子是為參加革命和追求上進而投奔延安的,他們並沒想到來此地充當毛澤東整人的打手。特別是中央研究院的成員,在張聞天多年來營造的黨風和學風熏陶下,他們的思想情調其實更親近國際派人士。張聞天,江蘇南匯人,早年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曾從事新文學創作和翻譯,卓有成效。後來他短期留學日本和美國,對經濟學有一定的研究。他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隨即前往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和任教。在中共高層領導中,張聞天屬於學養深厚,文人氣較濃的一個。不要說其他方面,僅就他擁有的文化資歷而言,即足以使毛澤東側目而視。張聞天當領導,一貫開明民主,他主持中央研究院,無論是理論課程的研讀,還是中央文件的學習,都允許學員自由討論,各抒己見。與毛澤東在理論問題上動輒設限的文化專制論調完全不同,他在《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倡:
大膽地創作、寫作、著述、介紹、翻譯,來打破各種限制,打破各種陳舊的觀點與標準,建立新觀點、新標準,以發展學術,提高學術;組織各種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團體,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辯論的生動、活潑、民主的作風;建立各種專門研究機關……應當提倡自由辯論與討論的風氣。爭論一時不能解決也不要緊,不必過早作結論。對某個文化人的缺點的提出,也要經過適當的方式。
對待文化人,他特別強調要尊重“其人格、其事業、其創作與意見”,主張“糾正黨内一部分同志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他還以文件形式發出指示說,“應該在實際上保證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給文藝家規定具體題目,規定政治内容,限時、限刻交卷的辦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24 正是在張聞天主持文教宣傳工作期間,從邊區到華北和蘇北的根據地,中共的文化工作一片活躍。特別是在延安,理論學習的空氣濃厚,文學創作繁盛,遠赴邊區的文化人一時間濟濟一堂,他們創立學會,出版刊物,排演節目,把延安的文化生活搞得分外熱鬧。但延安畢竟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並不是招納天下文化人的尊賢舘,過度喧嘩的學術文藝活動已引起毛澤東模糊的警惕。毛現在坐鎮中央總學委,他當年在長沙那種“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早已情調大變,屁股下的座位支配了他的頭腦,他自然也在從張敬堯或趙恆惕的角度觀察眼前的形勢,看待書生意氣的知識分子了。面對延安新文化的早春天氣,他的政治嗅覺多少已敏感出什麽不對頭的氣味。現在整風運動剛開展起來,延安的文事紛紜既引起他某種不安,也讓他揣摩到可資利用的潛能。
然而出乎毛意料的是,整風運動在最初點起的火苗並未燒向國際派,反倒讓毛澤東警覺到引火燒身的危機。這場火首先從張聞天曾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和博古現管的《解放日報》燒起。羅邁在中央研究院做報告動員整風,本是以號召幹部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爲主,改善領導作風的問題僅列為其次。但羅邁向來的“家長制”領導作風令下屬一直不滿,中國文藝研究室的特別研究員王實味首先站出來發表異議。他反對由研究院各級領導組成整風檢查委員會的決定,一是要求通過民主選舉組成院檢查委員會;二是要求自由辦壁報,院領導不得干涉。他的提議得到與會幹部的熱烈支持,會場上的風向隨之逆轉,批評的矛頭紛紛指向了單位領導。王實味不只帶頭挑戰本單位領導,他還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評延安社會“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這些文章在《解放日報》和壁報《矢與的》上登出後,丁玲、蕭軍、艾青等人也紛紛發表雜文和詩篇,有的表達文化人來到陝北後的失落和不滿,有的暴露了“抗日聖地”的諸多陰暗面。中央研究院以外的其他單位也隨之辦起不同的壁報,支持和響應王實味的雜文在壁報上大量張貼出來。反官僚和爭民主的風向一時間成爲整風的主流,中共的各級領導均成了衆矢之的。
這場小小的失火是延安的“土共”領地突然增添了一大批外來文化人而引起的騷動,也是毛澤東面臨的新問題。邊區政府收留前來的知識分子,把他們作爲“公家人”養活起來,目標是培訓為黨服務的幹部。正如徵召分了田地的農民子弟入伍當兵,是要他們為黨拼命打仗。黨組織接收這麽多年輕的知識分子,當然是要貯備大量可充當文化工具使用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初來乍到,還不太懂革命隊伍内的人情世故,青春的莽撞與農民軍棲居的黃土地一發生碰撞,就不可避免地碰出災難的火星。與其如高華所說,王實味事件昭示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不如說是延安之春發出的自由民主呼聲驚動了洞中的巨蛇。真正的蛇乃是毛澤東這條眼鏡王蛇,而所謂的洞,就是他深居的窯洞,是他與他的同僚所掌控的權位。王實味的雜文讓人們看出,這支革命的隊伍本來靠反特權起家,但掌了權的革命者現在也做起享受特權的醜事。這一指責正好有力打中了毛共的七寸。談到有關等級的問題,我們不妨把話再説回來,其實純粹就等級制這個制度而言,倒也算不上多麽不可容忍的事情。等級本來就是存在的,軍隊中若無官兵之分,軍官中若無將校之別,軍隊也就打不成仗了。等級乃是人類群體在世代的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秩序,不管其間經歷過多少矯正和變革,總的來說,等級秩序一直都在按優化的原則一步步進行改善。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錯就錯在只抓住等級秩序中有待改善的一面蓄意摸黑,控訴其罪惡,趁顛倒固有的價值秩序之機,以洩其真小人的怨憤,同時利用此怨憤建立其新的等級。為聚集暴力革命的人力資源,毛澤東組織窮苦者、低賤者打土豪分田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們怨忿富人的不平之心。爲吸收年輕的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則向他們列舉剝削階級的罪惡,特別就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作過分的煽動,激發他們的反叛衝動。然而吊詭的是,正因爲中共靠攻擊等級制和反特權起家,致使革命隊伍中要求平等的衝動最爲強烈,時或衝擊到中共自身的軟肋。中共既然最反對等級制和特權,爲什麽中共内部卻搞起等級制,中共的領導層也都享有特權呢?來到延安的這批知識分子本來就滿懷激進的社會義憤和強烈的民主訴求,現在目睹的現實卻令他們大失所望,無形中證實了“天下大老鴉一般黑”那句老話。面對這一切,他們怎能不感到氣憤!最近《蕭軍日記》在香港出版,讀者若仔細檢討散見其中的延安陰暗面描述,則不難理解王實為等人的不滿,更可看出延安當年的情況與今日中共集團全面腐敗之間的聯係。25 面對王實味點起的這場火,從羅邁到中央總學委,享有特權待遇的一群立即感到事情不妙。他們發現,整風已被知識分子的鼓噪扭轉了風向,若再不刹車矯正,群衆就要脫領導的褲子,割領導的尾巴了。因爲真正守護價值的“知識人”總會像蕭軍那樣,是“永遠不為既成的勢力——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所容忍的”,是“決定一生和這些庸俗的東西們戰鬥”下去的!而正是在此敏感時刻,毛澤東走出窯洞,蛇行到張貼壁報的現場。他觀察一番後,意識到局勢的嚴重,遂向身邊的隨從冷冷說道:“思想鬥爭有目標了”。
為立即扭轉風向,1942年4月3日,毛澤東指令中央發出“四三決定”。決定指出,整風運動必須在各單位負責人領導下進行,不得以群衆組織的形式左右整風的方向;整風不只針對領導,同時也要檢查下面的問題;每個人都得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毛的這一決定自然會令人想起此前十幾年他在“白砂會議”上的表現。那時候他不孚衆望,弄得紅四軍内諸領導對他群起攻之,他立即祭起“極端民主化”的帽子來抵制軍内同志對他的挑戰。後來他在古田會議上大獲全勝,軍内的民主訴求被壓制下去,從此他掌控軍黨大權,打消了職業軍人的威風。面對延安之春出現的危機,他現在祭起另一頂“自由主義”的新帽子狠狠向群衆扣去。現在他閉口不提“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句他多次說過的話了,爲了像鎮服軍隊那樣掌控輿論,他現在要徹底肅清文教宣傳部門的“自由化”傾向。既然已有王實味這個出頭鳥嶄露頭角,那就先把他定為鬥爭對象,殺雞給猴看吧。在中共隊伍中,一個人因言獲罪,被作爲典型大會批小會鬥,這似乎還是首次。
那時候的知識分子群中,多少還有人保持著“知識人”獨立思考的頭腦。因此在中央研究院,剛一開始批鬥王實味,絕大多數人均持消極抵制的態度,包括副院長范文瀾在内,幾乎沒有人主動跳出來充當打手。延安的知識分子一開始尚未喪失起碼的良知和廉恥,他們並不願意在批鬥會上去扮花臉。毛澤東於是把花臉的角色交給軍人去扮,讓文化層次更低的人去羞辱文化層次較高的人,這是毛澤東早在搞痞子運動時已運用過的手段。土匪出身的賀龍,領軍種植鴉片的王震,都陸續被派到中央研究院逞兇駡娘,他們仗著自己在前方流血殺敵的功勞,對“吃飽飯罵黨”的文化人發出強烈的斥責。接下來凱豊奉毛澤東的旨意取代失去威信的羅邁之職進駐中央研究院,他對衆人採取分化策略,說王實味是在搞陰謀,問題嚴重,必須嚴厲打擊;其他人即使有錯,均屬自發性質,只要坦白檢討,便不予追究。獲得豁免的羔羊為自己僥幸過關而順從了強奸輿論的淫威,他們於是一個個改換腔調,組成討伐隊伍,都把矛頭對準了王實味那頭待宰的羔羊。被稱爲“小資產階級的” 知識分子就這樣上了土共的賊船,從此陷於弱勢,致使他們至今都未能克服這一先天軟骨的弱點。他們的抗日熱情和革命理想固然有其可嘉之處,但自從白吃上邊區政府的小米粥,又寄希望於革命勝利後的個人前程,那熱情和理想就難免折損分量,在受到侵蝕後漸生劣質化之變。西方社會中“知識人”守護價值的素質在他們身上本來就根基淺薄,蘇聯的“知識階層”所承受的壓力在他們身上又成倍加碼,從此構成他們革命生涯中的難以承受之重。他們實際上已降格為受到脅迫的群衆,一旦鬥起黨所指定的對象,自然就會變得一個更比一個兇狠,在越鬥越升級的趨勢下,爆發出“群衆覺悟”的戾氣。被批鬥者的罪行也就隨之罪加數等,罪惡到一定要被打翻在地,再加上一只腳的地步。連艾青這樣發難過官僚主義的詩人,現在為開脫自己的罪責,也在批鬥會上對王實味惡言咒駡,說王“實在夠不上‘人’這個稱號”。艾青自己夠得上嗎?當他不把被批鬥者當人看時,他自己首先就已經不是人了!
毛澤東很快就把王實味的思想言論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王實味最後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他在搶救運動中遭到逮捕,此後一直長期關押。1947年中央機關撤出延安,王實味身繋縲紲,拖累行軍,在途中被作爲累贅大刀砍殺,扔入枯井了事。
六
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爲什麽能在黨報《解放日報》上刊登出來?這是毛澤東必須追究的問題。首先要怪總負責人博古把關不嚴,他放手丁玲主持了文藝欄目。其次要怪丁玲趁延安之春的氣候,推出了王實味等人以及她自己的一系列揭露陰暗面的雜文短論。毛澤東早就對《解放日報》以及延安其他報刊的輿論導向不滿:一不滿他自己的講話和活動沒及時得到突出報導;二不滿王明、張聞天、凱豊等人的理論文章一直在照登不誤;三不滿過多報導蘇聯的消息,把中共的黨報辦成了《真理報》的中國版。現在弄出了王實味這類自由化的問題,他自然要動手整肅延安的報刊。毛先是急派陸定一進駐《解放日報》,接著撤去楊松的主編之職,由陸定一擔任,楊松不久即因積勞和憂憤而病逝。陸在毛指導下對該報進行全新的改版,改版後的《解放日報》實權緊抓在陸和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手中,博古完全被架空為掛名的社長,黨報從此成爲毛澤東控制輿論的傳聲筒。按照高華的綜述,從此以後,黨報和延安的其他報刊都得嚴守毛氏“新聞學”的五個核心原則。一是“黨性第一”的原則,即把報紙辦成黨的宣傳工具,並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二是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即反對有聞必錄的新聞教條,不利於黨的新聞即使是事實,也不許報導。三是“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因此堅決要杜絕資產階級報紙“搶新聞”的做法。根據黨的需要,有些新聞可儘快發,有些則可緩發或根本不發。四是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自從《解放日報》改版,該報以及新創刊的《學習》專刊便承擔起指導整風運動的任務。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報紙也成爲整肅“異端”知識分子的工具。批鬥王實味期間,在《解放日報》和《學習》上就闢出專欄,大量刊登討伐王實味的文章。五是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閲讀的原則。毛澤東師法斯大林控制新聞傳播的成規,在消息知情權上製造出等級制度,“幹部級別愈高,閲讀限制就愈小,由此逐級而遞減。” 26 減到老百姓的層面上,就只被告知黨允許他們知道的事情了。延安的報刊上不再有任何言論自由,批評和異議被徹底消聲,黨組織忌諱的各種消息全都禁止報道。一個掩蓋真相和製造假相的工程從此便按照毛氏“新聞學”的核心原則運作起來,直到今日的《人民日報》以及各級黨報,毛共宣傳機構的苦心經營從未間斷。可以說,中共政權能夠維持到今天,並且還在繼續往下維持,在很大的程度上便有賴這項瞞哄工程持續而有效的運作。
黨組織不只通過報刊過濾消息,製造所謂“本質的真實”,限制黨員和非黨群衆的知情程度,更通過組織他們學習下發的文件統一所有人的認識。學了文件還要考試,再通過回答問題檢查每個人是否知道或接受正確的答案。自整風運動開始,在延安的幹部群中,一個改造思想的學習集中營就這樣逐步建立起來。幹部改造思想的過程,也是黨組織被人格化的過程。從中央總學委到各分區學委,這些機構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即可代表黨組織檢查每個人所寫的“反省筆記”,對作檢查的人反復發出拷問:你與黨是否保持“一條心”?如果你對黨只有“半條心”,甚至懷有“兩條心”,那你就得作更深刻的檢查,把你的想法和歷史交代清楚。黨報的號召聲如天穹罩在每個人的頭頂,毛澤東更親臨現場作動員報告,要求參加整風的幹部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他以狡賴的口氣威逼說:“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鉄的紀律非執行不可。……我們的‘緊箍咒’裏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 27 毛澤東現在已高踞代表黨組織説話的位置,而且正在把自己修煉成黨的化身。他說他“也要寫一點”筆記,身爲最高監督者,誰有資格檢查他的筆記?他又懇向誰作檢討?那個所謂“要寫一點”的表示,不過敷衍一下,作出虛應罷了。私下談話中,毛澤東一貫聲稱:“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的。”“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 28 毛澤東深知,認錯就是向對立面低頭,低了頭就得下台。因此他死不認錯,不認錯就是他能夠讓自己保持一貫正確和不可觸犯的“反導裝置”。毛的防禦是進攻性的,他要堅持自己不認錯,就得不斷督促別人認錯,督促更多的人認錯,督促他們認的錯越多,則他的一貫正確才會確立得越加牢固。從某種程度上說,迫使幹部檢討,特別是迫使那些與他對立的高級幹部檢討,已成爲毛澤東經常要喝上幾碗的安心雞湯,甚至成爲他滿足其獲勝心理的變態樂趣。
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島》中披露,政治犯進入勞改營的第一關就是不分男女,一個個全得脫光衣服,接受管理人員的檢查。通過剝奪囚犯的羞恥心,監獄當局將囚犯的人格和自尊完全踐踏到腳底。檢查反省筆記則是迫使檢討人把他們的自我像裸露身體那樣剝光,他們被要求向黨組織袒露個人隱私,坦白錯誤思想,交待說過的錯話,再加上反復自責自貶,直到組織認可,檢查通過,才算在政治上得到救贖。高華指出,“毛澤東的‘新’就在於融理論灌輸和暴力威懾於一爐,配之以強有力的組織措施,給廣大黨員,尤其是知識分子黨員製造了一座強大的壓力場,使其在反復震蕩中蛻盡‘舊我’,換上一顆全新的靈魂。”我覺得用“換上一顆全新的靈魂”來描述改造思想的結果並不確切,經過謝覺哉那種連煮帶蒸的思想改造,29一個人的自尊自信已受到摧毀,他的靈性也嚴重殘傷,最終被馴服成黨奴,徒具形骸而已,還談得上有什麽靈魂?謝覺哉向來被尊為中共元老,不可思議的是,他在整風運動的威逼下,竟下作到如此自輕自賤的地步:他一邊做檢討,一邊還滿懷興致,賦詩品味自己的受罪,足見學習集中營對參加學習者的摧殘和奴化之深。謝覺哉幾乎是帶著自虐的樂趣來描述他靈魂自殘的過程的,他給自己繪製的漫畫肖像反映出毛澤東卑劣的紅俗趣味:毛的確樂意看到,受到集訓的幹部都把自辱和受辱以及辱人作爲雜耍公開演示出來,最後閙得上上下下都沒有人格。
毛澤東善於使用酷吏型的人物,在蘇區打AB團時,他重用李韶九,放縱李濫捕亂殺。如今整風開始,他把整人的大權交給康生,任憑這個陰謀家差使他手下一批低俗的打手搞出種種折騰人的鬼名堂。比如像填寫“小廣播調查表” 這樣猥瑣的項目,就是此類小奸小惡之流挖空心思炮製出來的東西。“小廣播”是整風運動中發明的新政治詞彙,泛指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中所謂“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當面不說,背後亂説;開會不說,會後亂説”,以及散佈有害言論,洩露黨的機密等過失。通過學習黨報和文件,幹部被告知只許說什麽,只許怎樣想。再通過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幹部更被告知什麽言論和什麽事情不准你說,也不准你聼,甚至不准你想。每個人的言論都應與黨的宣傳口徑一致,若有所違反,就應老實交待出來,填入“小廣播調查表”。填過“小廣播調查表”的幹部從此在思想上給自己上緊螺絲,黨不允許說的話就再也不敢說出口了。幹部們隨聲附和的操練逐漸中規中矩,久而久之,已經養成習慣的口頭表達會反過來支配他們的頭腦,使他們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正是學習集中營改造思想所要取得的效果。自由主義是錯誤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等等,全都是錯誤的,只有毛澤東同志絕對正確。
毛其實並沒有他自己真正確立的正面價值,他只是通過把對立面全貼上“錯誤”標簽的“反動修辭”(rhetoric of reaction)來反證自己的正確。這就是說,只要毛能做到徹底否定對立面的這主義那主義,他自然就會在絕對的否定中正確起來。他的否定力量來自認同庸眾和發動群氓,所謂“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就是靠壓倒性多數力量的支撐,從低下的平台上逆反崛起。毛澤東並不諱言他的“土共”本質,他對蕭軍說過:“中國黨是在老百姓中間產生的,中國老百姓落後它也落後。”30 落後的老百姓才真正是毛澤東及其毛共的群衆基礎,是他們幸存和壯大的社會生態。其實包括很多投奔延安的年輕知識分子,也大都根基較差,再加上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長期受訓,久而久之,遂蜣螂轉丸,趨於土化。在那個知識分子人數本來就很少,水平多比較低的年代, 31 真正有水平和有氣質的“知識人”,恐怕是很少有興趣投奔延安的。細讀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記,可從側面一窺延安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況。有位擔任翻譯的蘇聯工作人員名叫Aleyev,他評論延安知識分子的一番話被弗拉基米洛夫錄入日記:
在我看來,最優秀的年輕人在1940年以前均已離開特區。大多數留在此地的求學青年均出身小資產階級,在1936年到1938年之間來到特區時,他們還不足二十嵗。那時正值抗日高潮,他們投奔延安,多出於浪漫的激情和一時的狂熱。其中有些人完全因謀生無路才跑到這裡,想找機會讀幾年書,好求得一個穩定的飯碗。很多加入共產黨的青年都相信他們能統領時潮,隨著共產黨的發展和壯大,他們更會飛黃騰達。
他們在此地的學校學習,日益習慣乏味漫長的開會和毫無目的的批評,逐漸都蛻變成批鬥會上整人的鬥士。他們慣作漫無邊際、空洞雜亂的發言,或無聊終日,言不及義。
不管談起什麽話題,他們總是重復說:“黨叫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我時刻準備為中國革命付出任何犧牲!”
學生們在這裡學不到什麽有用的知識,對於種種政治議題,他們的觀念模糊不清,僅限於尋章摘句。他們喜歡談論馬列主義,好引用教科書的説法,卻抓不住其中的要點。
對中國歷史和革命運動,他們同樣認識模糊,甚或完全無知。對蘇聯也幾乎毫不了解。所有的學生都可吃到免費的小米稀飯,只要他們願意學習,就會一直學習下去,也不必參加工作。其中有不少人還夢想到蘇聯長期留學。
他們的知識都很淺薄,特別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學問。然而他們卻好泛論各科話題,希冀重要的工作崗位,輕視事務性的工作。很少有人選修醫學或無綫電操作的課程,因爲他們覺得從事此類工作難以快速高升。
直至他們進入特區之後,才終於發現從此便斷了與家人和親友的聯係。與外界通信是犯忌的,事實上也很少有人敢與親人通信。想家的人會被人恥笑,因此他們只能把思念暗藏心底。
傳統的廉恭有禮在這裡不復存在,而代之以特區外根本不通行的言談話語,其中充滿了乏味、做作和粗魯的黨化詞語。
說得好聽一點,特區培訓出來的黨政幹部僅有低水準的基本知識。有些學生連鐘錶都不會看,算術也很差。這些未來的黨政工作人員大多數沒有實際經驗和專業技能。他們普遍落伍,一門心思只想當領導。32
王實味已徹底打倒,蕭軍也被迫出走,素質本來就比較差的眾知識分子都在幾經折騰後乖乖順從了黨組織的教化,自覺步入庸眾群氓的行列。按照毛澤東講話的要求,共產黨的幹部也好,受黨教化的知識分子也好,現在都得從“工農兵”群衆的基礎上提高,既不許把“工農兵”提高到本應發揚光大的傳統文化——毛貶斥為“封建文化”——的高度,也不許提高到本應學習的西方文明——毛貶斥為“資產階級文化”——的高度,按照毛的指示,知識分子都必須“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 33 這一“提高”的方向與其說是要把低水平向高水平提升,不如說是硬要把高水平向低水平拖拉壓抑。正如毛通過把黨内對手都打成各種錯誤路綫的代表來樹立他自己的絕對正確,對“極卑之人”的毛來説,只有把黨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全都拉低到工農兵群衆的“高度”,才足以平衡他長期以來的不平之心,才便於把他自己擡上“極高之人”的尊位。這種通過向下看齊以求個人發達的路綫,用孔子的話來説,可謂不折不扣的“小人下達”。後來做了林伯渠夫人的朱明就是在這一形勢的逼迫下極盡其自誣之能事,向黨組織委屈交心,寫出了《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那篇奇文。34
七
她原名王鈞璧,1939年投奔延安後改名朱明。出身富裕家庭的朱明從小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與不少追求“進步”的青年大致相近,她也是滿懷參加革命的熱情投奔到延安。朱明的反省檢討很有代表性,按照高華的分析,應是在領導的誘導下,經過反復加工,鄭重推出的一個思想改造懺悔書範本。那時候延安出產的工農兵文藝作品《白毛女》中有一衆所周知的警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從當時整風運動的恐怖情形來看,毛共控制下的延安社會才是真正把人變成鬼的地方。什麽人配稱爲人?什麽人可稱爲鬼呢?我想,任何一個不願意做鬼的人都會承認:說人話——也就是說實話真話——的人才配稱爲人。人而不准說人話,卻被迫去說假話謊話——也就是鬼話,那人就被逼成鬼了。毛澤東及其控制的中央總學委發起的運動,不多不少,堪稱一場逼人做鬼的運動。凡是發自良知的見解,出於常識的判斷,一個心智正常的人對是非、善惡、美丑的自然反應,按照毛共的黨性要求,都必須整個地顛倒過來。黨要求你放棄你原有的價值選擇,踐踏你本來的情感趨向,你原來不以爲然的説法,你現在必須接受和贊同,你實際上並不喜歡的人和事,你現在必須無條件地表示你非常喜歡。按照說鬼話的準則,凡是人話否定的人和事——比如朱明原來對湖南農運中的痞子舉動很反感,認爲中共宣傳蔣介石不抗日的説法是誣衊——經過思想改造,均一一予以矯正,被定性為錯誤看法和反動思想,並將其歸結為朱明的階級出身所導致的偏見。經此矯正,朱明開始昧著良心說話,從前她對痞子在小姐少奶奶的床上打滾很反感,現在則肯定那是革命行動;淞滬戰役中她親眼看到國軍拼命打擊日寇,現在則相信蔣介石要準備投降日本,只把槍口對準共產黨。由此可見,矯正的效果就是讓黨和非黨的幹部,以及投奔延安的青年人全都睜眼説瞎話,矢口否認中共的罪惡,全面抹黑中共敵視的黨派和人群。
朱明在政治上與黨發生抵觸的根源既然被歸結為她剝削階級的家庭出身,她在家中受到的一切熏陶和教育也就都屬於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情趣品味,而必須嚴加檢討了。於是臨帖練書法呀,聼古典樂曲呀,讀唐詩宋詞呀,以至做一個大家閨秀應懂得的禮貌修養呀,現在全都成爲她必須告贖的原罪。現在她要入黨,要把自己改造成“新人”,就必須放棄她曾經認爲是美好高雅的東西,就要把Aleyev針對延安青年的表現所批評的那些粗俗言行奉為革命的規範,就要緊跟他們的步伐,在討論會上大量使用那些“乏味、做作和粗魯的黨化詞語”積極發言。而要做到這一點,她還得唾棄自己的父母親友,從血統上徹底否定自我。為表白她脫胎換骨的決心,朱明向黨組織檢討說:“今天我明白了,黨為什麼珍惜無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和革命後代以及先烈遺孤,因為不僅他們的思想有傳統,就連他們的血液也是乾淨的,黨為什麼不珍惜他們呢?”“我呢?本來是站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現在也開始願意下來做無產階級的牛了。把自己的思想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我這時才瞭解到馬列主義的真理的力量。”一個人一旦徹底否定自我,就會自輕自賤到沒有限度的地步。早在紅衛兵肆虐之前,朱明已率先抛出激化階級鬥爭的“血統論”了。
經過恬不知恥的自我鞭笞,朱明終獲黨組織的寬恕而得到政治救贖。但即使把身段放低到這步田地,朱明還是不太滿意,不很放心,就她追求進步的目標來看,是非要從血肉上與一個能代表黨的人物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足以讓她感到此身的安頓有個牢靠的依附。於是她以她二十來嵗的妙齡,心甘情願嫁給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年邁的林伯渠同志。對革命隊伍中的女同志而言,向黨“獻身”的行動,現在有了雙重的含義。朱林式的婚姻結合在當時的延安,多少已形成很多外來女青年選擇配偶的模式。成千上萬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女子,包括來自上海的江青在内,就這樣“沿著無產階級的方向”,盡可能地“提高”了自己的水平,提高到各級領導幹部的床笫上……她們不再像王實味那樣追究特權和等級制的問題了,因爲她們業已順著政治正確的階梯爬上各自可能到達的高處。然而不幸的是,高處自有其不勝寒之處,黨内的鬥爭也時常波及諸領導夫人相互的關係,她們之間的嫉妒和惡意時有踫撞,一遇到合適的氣候,便會釀成“夫人政治”的惡鬥。1954年春,毛澤東與江青在西湖行宮休養期間,朱明不知出於什麽具體的動機,從上海發出一封揭發攻擊江青的匿名信。該信經浙江省交際處轉交到江青手中,江青接信後十分惱怒,浙江公安廳立即著手破案偵查,牽連得涉嫌受審者竟達八百人之多。直到1961年林伯渠去世,朱明寫信給中央反映林伯渠死後的遺留問題,才被發現其筆跡與那封未結案的匿名信一模一樣。朱明在招供後立即畏罪自殺,時年僅四十二嵗。
思想改造不但沒能提高黨與非黨幹部的品質,反倒敗壞了他們的人格;不但沒有加強黨内外的團結,反倒加劇了同志們之間的衝突和敵意。高華尖銳地指出:
為了服從現實生存和政治發展的需要,根據地內的許多黨員學會了隱瞞真實想法,而隨聲應和上級的指示。根據地內的人際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基於共同政治理想而結合的“同志”關係,慢慢向人身依附的關係轉變,冷漠、猜忌、互相防範逐漸取代了同志間的親愛、坦誠。口是心非、投機鑽營、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之輩漸漸充斥中共黨內。由於人性畢竟非強力和說教所能完全改變,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現象,具有雙重人格的黨員在整風審幹後開始出現。35
朱明即為一“雙重人格”的典型。一個人僅為了向黨組織積極表現,就不惜寫下出賣自己和親友的坦白,她/他還有什麽事做不出來?在毛澤東和黨的“教導”下,朱明久已養成揭發他人隱私的習性,只要屬於她認爲不利於黨和毛主席的人和事,她都會毫無顧忌地大膽揭發,發展到後來,竟揭發到毛澤東夫人江青的頭上。這裡面想必還有什麽複雜的私人恩怨,那已非我們局外人所能猜測清楚,但不管怎麽說,整風運動的遺毒後來在朱明身上惡性發作,顯然是促使她寫那封匿名信的重要動因。高華書中還特別提到一位爲人正直的高級幹部,他名叫王世英。王在整風運動中向劉少奇抱怨說:“回到延安,我覺得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願做的不願說的,也得去做去說……感覺沒有在秘密工作時那樣純潔。”劉少奇卻認爲王世英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劉進而教導王說:“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皮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36 那還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從劉少奇能說出這種歪話的事實即可看出,劉的人格扭曲及其靈的殘缺已發展到不是人而是鬼的程度。黨的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攫取黨權者個人的或團夥的利益,擎起 “黨”這面招牌,權鬥的一群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污衊對手,惡鬥到蔡和森所謂“無惡不可為”的地步,甚至到毛澤東所謂“惡在究竟,仍不為惡”的地步。劉少奇在整風運動中之所以能後來居上,一躍而高踞黨内的二把手地位,正是因爲他勇於和善於搞黨内惡鬥,為毛澤東及其毛共的利益幹了不少極壞的“好事”。劉最終的下場固然十分可憐,但就他為黨的利益而一貫不擇手段的惡行來説,他的慘死也未嘗不是現世的報應。
註
19參看黎東方:《細説抗戰》。頁33-34、178-188。
20《彭德懷自述》,頁245-246。
21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p. 25, 64-66.
22參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05-308。
23 同上,頁315。
24 朱鴻召:《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74。
25 蕭軍在1941年6月24日的日記中就記錄了他耳聞目睹的特權現象:“下午去看芬,在醫院中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1)李伯釗自己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2)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 蛋,餅乾代早餐。(3)毛澤東的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4)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十幾元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是四元或五元。”見《蕭軍日記,1940-1945》上卷,頁200。轉引自麥啓的評論《蕭軍日記:延安檔案》。
26 參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365-376。
27 同上,頁398-399。
28 沙葉新:《檢討文化》,載《隨筆》,2001年6月。
29 謝覺哉詩曰:“緊火煮來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不要捏著避火訣,學孫悟空上蒸籠;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內夾生;煮要暫兮蒸要久,純青爐火十二分。”包括以上所引高華說,均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423-424。
30 見《蕭軍日記,1940-1945》上卷,頁136。轉引自麥啓的評論《蕭軍日記:延安檔案》。
31 胡喬木說:“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餘人,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約30%。”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9。
32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p. 48-50.
33 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59-860。
34 我從網上下載了該文的全文,同時也參考了高華書中所引的段落,見其書頁427-436。
35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436。
36 同上,頁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