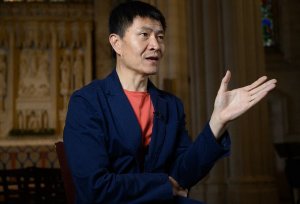的确是杂感,拉杂想到,拉杂写出。
一、 藏汉之别
这问题是小孙提出的,当真是后生可畏,其实这小家伙水平远高于老芦,只是他写文章的口气比较平和中正,又有点学院派的文绉绉,没有老芦行文情绪色彩激烈,所以不会让人觉得痛快罢了(NND,真是老少错位)。但此子洞察力非凡,前程远大,日后必将成为一大天王。谓予不信,请拭目待之。
小孙指出的藏汉之别,北徙小友已经解答了原因,那就是信仰的有无。有信仰才能抵挡万能的二杆子,才不会轻易被权势者愚弄。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信仰,成了行尸走肉,古话 “哀莫大于心死”,就是为咱们后世子孙定身度做的。
再说得具体些,汉藏的区别,在于人家有一个僧侣集团。这就等于汉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乃是社会的精英脊梁。我党在汉族地区的成功,乃是用金钱美女(light说的“钱杆子”)收买了知识分子这个精英脊梁造就的。如我在《未来中国社会走向预测》(最先在本网站贴出,原题为《小马过河谈国情》)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精英脊梁乃是社会稳定第一要素,牢笼了它就能“纲举目张”,保持社会稳定,此乃李世民早就作出的发现,如今我党不过是师古人旧智罢了。
但这一套绝对无法在藏族佛国成功,我党绝无可能在那儿复制内地“奇迹”。盖人家的精英脊梁有信仰,而信仰是无法被收买的。因此,同样是自发骚乱,在内地发生与在那儿貌似而实质不同。第一汉人没有离心倾向,第二内地民众骚乱基本没有知识分子介入,而没有精英集团的组织领导,那就只会永远是此起彼伏的自发骚乱,不会成为同步的燎原烈火。其实若论规模与暴烈度,内地发生的无数次自发骚乱未必弱于拉萨此次骚乱,发生率就更非后者之比了,但它们的潜在危险度远不如藏民地区。
这就是我为何反复建议我党退回到当年的十七条协议上去,迅速迎回达赖喇嘛,藉此造成他与手下激进少壮派的分离,并由此笼络住西藏的僧侣集团。其实那地方完全是月球表面一般的废地,毫无经济价值,只有国防价值,咱们只要如大清时一般,让它作为中国的保护国,有国防军在那儿驻扎就够了,除此之外一律不必多事,何必去背那出力不讨好的包袱?
但此策现今的党国领导根本听不进去,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当年那群共党邪教志士,而是一群经过我党二杆子强大负筛选出来的人渣,绝对没有能力理解“信仰”是怎么回事,绝无可能知道信仰的顽强抵抗力,绝对不相信“金钱+暴力恐吓”不是万能的,绝对不相信没有人不会倒在“糖衣炮弹+真枪实弹”之下。蠢党非但看不出达赖喇嘛不是二杆子可以战胜的,还竟然蠢到以为达赖的死亡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枢钥。此所以竖子不足与谋。
二、 达赖与我党的关系犹如当年康梁与我大清的关系
阿苗在楼下提醒我达赖对西方作的宣传如何偏离事实,我当然知道。既然是宣传,就必然有欺骗成分,只是程度有别。西藏当然不是达赖口中的那个“香格里拉”,人间乐园,但更不是我党笔下的那个剥皮抽筋挖眼的人间活地狱。人家过去当然是实行农奴制,那又怎么样?人家实行的是人道(或准确说来是“佛道”)的温情脉脉的旧式农奴制,毛共实行的是从苏联进口的野蛮血腥残暴的农奴制。西藏在“民主改革”后发生的社会大倒退,并不亚于内地在“人民公社化”之后由千年自由耕作制跌入共产农奴制而出现的社会大倒退。要明白这点,只需去看看张戎毛传中引用的班禅喇嘛给人大常委会的十万言(?)书就够了。请爱党同志务必记住,班禅可一直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千万别骂错人。
更何况人达赖多次向国际社会宣称,如果他返回西藏,不会再复辟原制度,还要实行民主化。世界屋脊能否实行民主化当然可以讨论,但拿“复辟农奴制”的魔鬼面具吓唬人,这套早就老掉了牙,建议爱国同志换换戏码。
我曾在电视上数次看过达赖接受西方记者采访,仔细聆听和观察了该同志的每一句话与每个表情,不能不由衷折服。而让芦某能如此倾倒的政治家,除了他这世上还真没有。他对西方人心态之熟悉,对采访记者的巧妙驾驭,简直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他非常精通如何去巧妙地歪曲事实,迎合西方左右派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式,彻底俘获他们,把全世界的同情都争取过来。如此毫无实力舞台,更无国家资源支撑,全靠一己聪明才智进行外交,与我党强大的三杆子(枪文钱)周旋,还能取得国际宣传战的全面胜利的伟大政治家,自有人类以来大概也没有几个。当年康梁之所以能在国外把慈禧抹黑得一塌糊涂,无非是我大清不知道世上还有争取国际舆论这回事罢了。人家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党则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因为永远不可能出现达赖那种具有大智慧的国际政治家(敢情这“活佛转世”还真有点道理?要不平民怎么会生出这种天才来?),我党在国际社会中只能是当年老佛爷在列强眼中的那个颟顸昏庸怯懦残暴形象。我党绝无可能在外交领域里战胜这伟大的国际政治家。中国除了达赖喇嘛,谁也不配做大英雄,要服气,不服气不行(改编自敬爱的林副统帅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时的亲切教导)。我党连李大牙那种上辱祖宗,下羞子孙的烂痞都有本事推出来做外长,还配做梦与达赖在外交战场上驰骋?!
三、 骚乱必然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压服只能压而不服。”他还忘记了一条:“收买有可能买而未收。”他还说:“小道消息发达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却忘记说:“骚乱多半是群众没有表达怨气的法律渠道的结果。”我党迷信三杆子威力,陶醉在收买知识分子的成功中,对空前的社会危机视而不见,当然民间骚乱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就是必然的。有无国外教唆都一样。岂不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是变化条件。”若社会不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谁有本事去煽起骚乱来?怎么不见隔壁的爱党人士去把美国人民也煽动起来,来他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诸位怎么只知道被动防御,不敢主动打出去,白白浪费蹉跎了深入美国虎穴的立功良机?
即使是常态社会也照样可能出现骚乱,美国和欧洲在60年代社会普遍出现骚乱就是证明。人家和咱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家的社会制度保证了社会危机能够得到和平化解,所以用不着如我党一般怕进了骨子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魂不附体,惊呼:“救命!万能的CIA来了!”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可能极大地低估了爱国同志们除了“网上声能”之外的其他能量。前两年洛杉矶不是发生过非洲美国人发动的大规模骚乱么?说不定那就是英明的党中央通过著名N重间谍梅草庵发动隔壁爱党人士组织动员黑阶级兄弟取得的伟大战果,是不是啊?
四、 中央情报局倒海翻江的大神通
本人不是独坛那些华裔美国爱国贼,是尊重客观事实的独知。我当然知道美国CIA在60年代初资助训练过西藏的自由战士们,令他们越境回国去发动反共游击战——这如今已经是世人皆知的解密档案了;我更知道CIA组织武装训练回回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的事实;甚至也在西方报纸上看到CIA保镖护送吾尔开希抵达美国的消息。这些事实恐怕连爱党激情有余、理智毫无的党朋都不知道。他们拿手的就是转贴“西点军校高官承认最怕毛泽东的革命化军队”的劣等小说,再由某“爱犬女郎”出来作伪证,言之凿凿地说她认识的西点高官证实了那无耻谎言。
但那是冷战时代,和毛泽东扮演亚洲共运掌门人,向印度支那、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尼大规模输出革命、颠覆人家的合法政权的伟大革命行动比起来,CIA那点猫腻实在是上不得台盘的小儿科。世间只有因爱党而彻底丧失了神智的党朋,才会有脸说1989年北京百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是CIA煽动的结果。这完全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放肆侮辱——难道他们竟然会认为“太阳最红,CIA最亲”?
五、 信仰双重论
此文写得实在涣散杂沓,还是回到小孙提出、北徙解答的那个重大问题来吧,到底该怎么看待信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孙、北二同志因为阅历不同,似乎有很大分歧。
老芦是在狂热的邪教宣传中长大的,当初也曾是狂热的信徒,因此深知这信仰的可怕,见怕了信仰如何扭曲人性,使得本来是温文儒雅的读书人旦夕之间变成青面獠牙的妖魔。在沉痛深思历史教训之后,便不能不回溯到孔孟之道特别是宋明理学那些魔道上去,找到了国人在民族危机降临之时集体“义令智昏”祸国殃民的文化传统原因。
针对这个弊病,我自上网以来反复抨击只讲“大义”、不计后果的民族传统,提倡功利分析,指望国人建立理性思维习惯与责任伦理观念,在事关国家前途、苍生气运时不要再干那种哗众取宠招来重大灾难的烂事。同样是为此,我写出了长达九篇的《“犬儒“篇》,痛驳胡平“以道易天下”“反对自由主义”的儒家及毛共传统,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就是《与其“义令智昏”,不如“见利忘义”》,觉得目前国内席卷一切的拜金主义与物质主义虽然弊端无穷,却恰是消解毛共将万事万物政治化,把全民改造为政治动物的背时国症的良药。
小孙小北辈的成长经历恰好与我相反,人家是在毫无信仰,只有物欲横流的时代长大的,自然就觉得信仰非常可贵,起码不会同意芦老邪对所谓“道德”的反复嘲笑诋毁。
愚以为,这说明了信仰的“二重性”(咱们只好借用马列术语了)。两代人看到的都是事实,但都只是部分事实。例如如今网上信仰最坚定的人就是王希哲,您说那种花岗岩脑袋一旦当了国,或至少变成国民主体,那还了得?但问题是若一个民族只知纸醉金迷醉生梦死,那还能有什么前途?
具体展开来说这“前途”。我整理的全集中有一集题为《反革命书》,其中反复破除的一个迷信就是“只有革命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我指出,事实与此完全相反,社会进步只能由统治阶级让步实现,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会适得其反,招致社会大幅度倒退。这其实说得不全面,全面来说应该是以下两条:
1) 社会进步只能由统治者作出让步,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来实现。
2)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统治者作出让步,就必须由知识分子组织率领民众理智地、有意识地、有克制、有限制地自下而上地向统治者施加压力。
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进步得以发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它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没有考虑到在缺乏民众压力下,统治者照样可以作出主动或被动让步,这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讲过了。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国家经济繁荣了,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初那个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统治者觉得可以苟安一时,因而再也没有作出主动或被动让步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改革,取得社会进步,自然就需要知识分子率领民众主动向统治者施压了。
但要做到这点的前提乃是知识分子必须有健康的信仰(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更必须有高度的责任伦理观念,这才能避免重蹈89年学运领袖们的覆辙,和我党又勾结,又斗争,将要求的上限始终保持在统治者让步的限度内。但这根本就是脱离国情的空想,因此是绝无可能实现的。中国社会除了经济成长外,就再无可能取得重大的社会进步,此所谓“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绝不会有前途”。
在我看来,这就是汉人最大的问题,咱们要么是“聪明过份”,要么是愚蠢疯狂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因此永远只会处在“有信仰时极度危险,无信仰时默默腐烂”两种极端状态之中。
关于作者
相关文章
最近的帖子
-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三十一 記者來了2 月 1, 2026 | 本站首发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三十一 記者來了2 月 1, 2026 | 本站首发 -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三十、收到《起訴書》1 月 31, 2026 | 本站首发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三十、收到《起訴書》1 月 31, 2026 | 本站首发 -

-
 鄭惠芳:冬日的臺北1011 月 30, 2026 | 本站首发
鄭惠芳:冬日的臺北1011 月 30, 2026 | 本站首发 -

-
 刘同苏:美国基因与基督精神1 月 29, 2026 | 本站首发
刘同苏:美国基因与基督精神1 月 29, 2026 | 本站首发 -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二十九 離開深圳1 月 28, 2026 | 本站首发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二十九 離開深圳1 月 28, 2026 | 本站首发 -
 卢比奥在参院作证:为确保最大程度的合作,美国已做好在委内瑞拉动用武力的准备1 月 28, 2026 | 时政
卢比奥在参院作证:为确保最大程度的合作,美国已做好在委内瑞拉动用武力的准备1 月 28, 2026 | 时政 -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二十八 重操舊業1 月 27, 2026 | 本站首发
周遠志:渾濁的婉兒河——一個坐臺小姐日記(长篇连载)二十八 重操舊業1 月 27, 2026 | 本站首发 -
 美议员:张又侠落马后,习近平不太可能加速其攻台计划1 月 27, 2026 | 时政
美议员:张又侠落马后,习近平不太可能加速其攻台计划1 月 27, 2026 | 时政
转型译丛
《零八宪章》十周年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
作者专栏
| 北 明 | 毕康 | 蔡咏梅 | 曹雅学 |
| 陈树庆 | 陈卫 | 陈永苗 | 程映虹 |
| 丁子霖 | 杜 光 | 顿珠多杰 | |
| 樊百华 | 傅国涌 | 付勇 | 高洪明 |
| 高智晟 | 巩磊 | 巩胜利 | 顾乃忠 |
| 郭宝胜 | 何清涟 | 何与怀 | 胡显中 |
| 黄钰凯 | 江棋生 | 姜福祯 | 焦国标 |
| 康正果 | 李大立 | 李对龙 | 李海 |
| 黎建军 | 李 劼 | 李金芳 | 李昕艾 |
| 黎学文 | 李元龙 | 廖亦武 | 林傲霜 |
| 林欣薇 | 刘 荻 | 刘京生 | 刘军宁 |
| 刘柠 | 刘贤斌 | 刘晓波 | 刘在中 |
| 刘正清 | 吕耿松 | 马萧 | 茆家升 |
| 孟泳新 | 闵良臣 | 莫之许 | 牟传珩 |
| 欧小戎 | 欧阳懿 | 裴毅然 | 綦彦臣 |
| 秦伟平 | 秦永敏 | 彭小明 | 任天堂 |
| 桑杰嘉 | 邵文峰 | 邵江 | 沈良庆 |
| 施 英 | 孙德胜 | 田奇庄 | 铁 流 |
| 王德邦 | 王 康 | 王力雄 | 王天成 |
| 王维洛 | 王怡 | 唯色 | 卫子游 |
| 温克坚 | 武宜三 | 吴 严 | 吴 庸 |
| 吴祚来 | 肖雪慧 | 小乔 | 徐琳 |
| 徐友渔 | 杨 光 | 杨宽兴 | 杨子立 |
| 杨支柱 | 野 火 | 一 平 | 依 娃 |
| 逸 风 | 应克复 | 余 杰 | 余世存 |
| 昝爱宗 | 曾伯炎 | 曾建元 | 张博树 |
| 张大军 | 张 辉 | 张铭山 | 张千帆 |
| 张祖桦 | 张裕 | 张智斌 | 张善光 |
| 张圣雨 | 张耀杰 | 张镇强 | 赵常青 |
| 赵思乐 | 郑 义 | 郑贻春 | 朱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