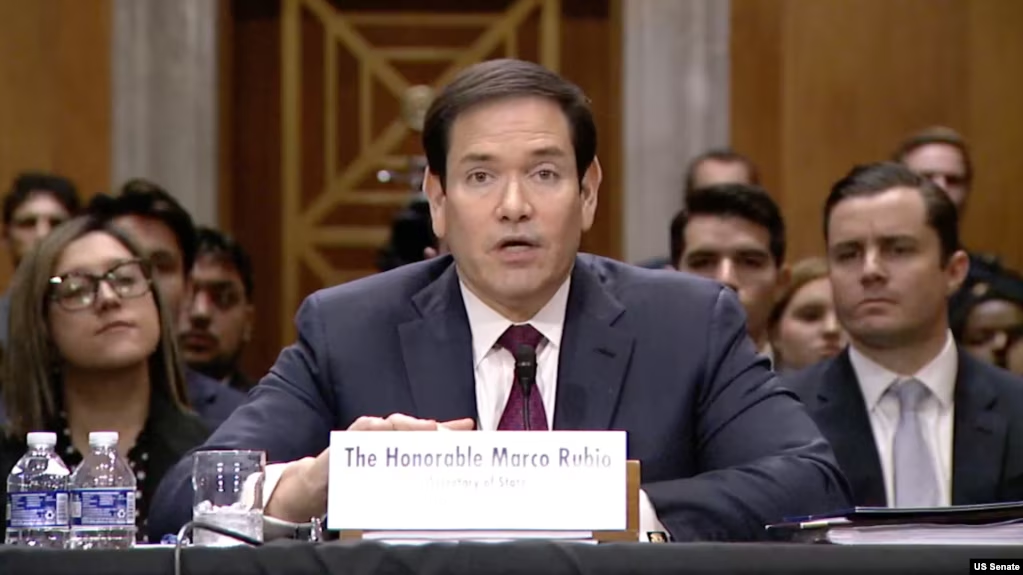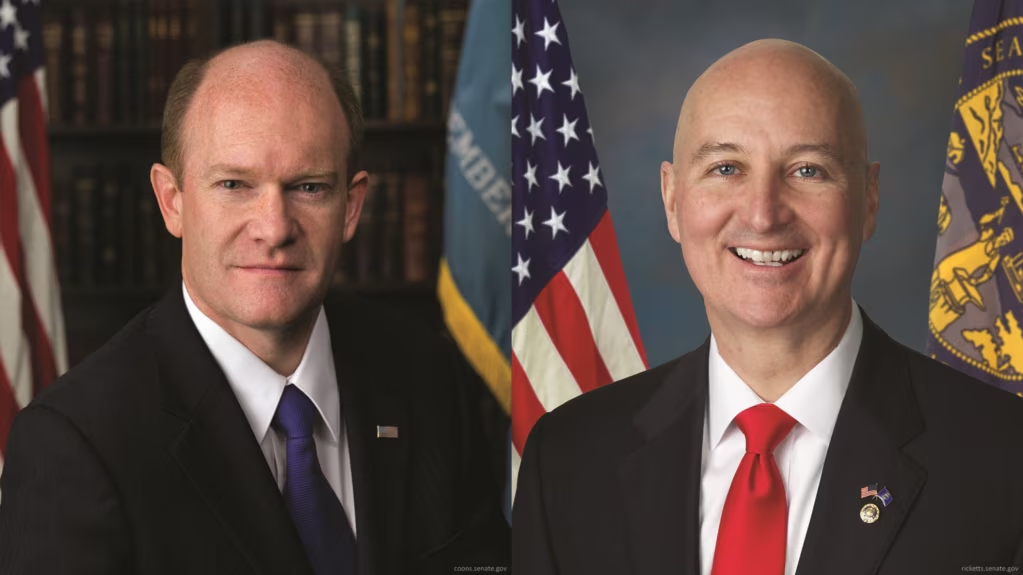如果一种赞誉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那样的赞美当然一文不值。
有一次,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问国内的民间学者,你在这么多问题上都有相当精准的分析和准确的预见,为何不见有任何荣誉和承认呢?对于国外学者来说,这是发生过的,比如911之前,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就以《文明的冲突》一书预见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从而享誉全球。
当然,这样一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如果一种赞誉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那样的赞美当然一文不值。而为赞誉赋予经济价值的能力,只能来自于主流社会。在一个后极权的国家,虚弱的社会无法为自身赋予有效地价值。而只有国家和政权控制下的空间中,才是主流社会,才是真正的资源集散地,才能真正赋予一项赞誉无与伦比的社会效应。任何一种真正的成功的赞誉,也就是政权加持过的金瓶掣签,都必将是属于主流世界的。而在体制之外,无论是企业、民间组织还是赞誉,都不过是一种小众的互相肯定。
国内的余世存先生曾发起当代汉语贡献奖,这项民间的奖项将对当代汉语的贡献授予那些真正推动话语变革的社会异端。这项奖项也要对抗极权的话语垄断,为民间的话语引领时代而努力。很可惜的是,这项奖项的获奖人本身也极少提及这样一项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奖项。
而对于维权律师的嘉奖中更能够轻易的看到主流的话语霸权,那些民间组织的颁奖可以短暂的获得得奖者的附和。而长期范围来看,没有体制加持的奖项都将快速褪色。即便是最彻底的人权律师高智晟,人们对他讲述最多的,竟然还是获得过司法部的某奖项。而如今已经不见踪影的公盟,在评选“公民”奖项的时候,也热脸贴冷屁股的将当时的红人韩寒纳入其中,期望贴近主流而增加价值,虽然韩寒本人最终没有出席颁奖活动。
在这样逼仄的现实里,不仅谈民间的独立自主性是乌托邦的事情,就连一个基本的价值认可与赞誉都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否后来进入了反对派和体制外,那些曾经获得成功赞誉的案例,这些赞誉基本来自和体制紧密相连的官方机构或者体制关联单位。即便是学者,没有主流社会的肯定,很难没有出书大卖的机会,没有全国讲座的机会,没有研究的课题。无论有多少的真知灼见,能收获朋友间的一个友情鼓励已是不易。
在这样的社会中,体制外的反对派谈成功和赞誉都是笑话而已,没有生活的全面溃败已经实属不易。
美国的学者麦克亚当等人研究发现,运动参与经历对人生具有持久的影响。那些有过运动参与经历的人,后来更容易参加社会运动。不仅如此,运动参与还持久地影响个人生活。比如,那些运动积极分子更容易离婚、更容易丢工作、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等。
在美国的非主流的基本生存尚且如此全面的失败,何谈中国的反对派。对一个反对派而言,谈成功不过是来自主流社会的羞辱。作为反对派,还是承认永远而且全面的失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