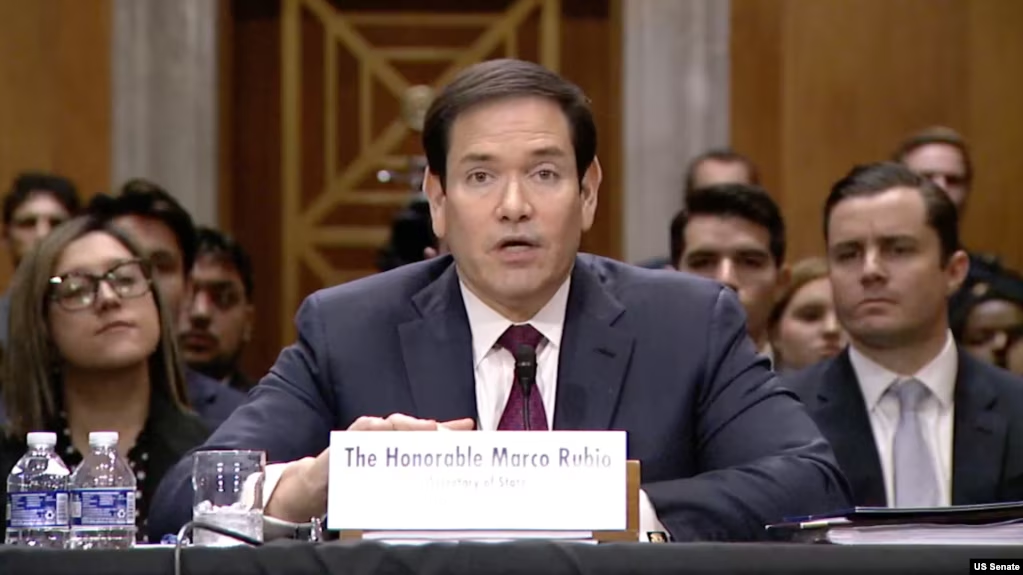引言:作为西学概念的式微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由西学输入的。在西方政治学术中,民族主义是罗马帝国体系崩溃后原帝国民族区域的政治构建情绪与政治实践,如德国与意大利的建国历程。欧洲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地理上的确定性,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帝国主义遗传性。如英国的保护公民原则,实际是对罗马帝国的效仿,1850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宣布:“世界上任一个地区的任一英国公民都要像罗马帝国的公民宣称‘我是罗马公民’那样称自己是英国公民,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手段保护自己免遭外国人的侵犯。”[参见赵丰等译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P340,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民族主义在地理确定性、帝国遗传性两大特征之外,另一个特征是反启蒙即其浪漫性,或曰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拉尔夫等文明史家看来,浪漫主义“或许代表了一种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动”[同上书,P342,在第二十章《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立(1815-1870)》之内]。进入二十世纪晚期,欧洲一体化的设想仍然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其帝国遗传性(特别是在西欧)却发生了变异,民族主义在这种趋势下逐渐式微,尽管东欧在自号“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体系崩溃后不断出现独立诉求。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特征淡化,首先有赖于其地理上紧密性而致的市场共同化,而后则是道德反省,比如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虽然统一后努力谋求领导地位,但是德国对于屠杀犹太人的真诚的反省(此前称之为“勃兰特之跪”的细节是其标志)成为本质上回归欧洲的前提。
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仍然是德国内部的一支政治力量,然而欧洲在“市场加道德”机制下的统一趋势已经将前者边缘化。是建立仍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市场一体化的欧洲呢?还是恢复罗马帝国的赫赫武功或曰建立“第四罗马帝国”呢?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至少来说,前者是民族主义的替代品。不过,欧洲在本身的民族主义式微之后,他们在焦虑地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经意间国际化了。
一、种族主义怪胎,帝国遗传变异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地理确定性之上很难形成侵略性的帝国特征,尽管有组织甚至有中共意识形态集团背后操纵的民族主义能屡屡掀起国内“抗日”、“抗法”等社会运动。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质而论之,它是帝国遗传变异后的种族主义怪胎。勾稽历史,种族主义是帝国衰败时期一种政治思维,这从东汉帝国结束后持久混乱的历史看得出来,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语[参见王涛等《中国成语大辞典》,P343,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出自西晋的一位官员和政论家江统的文章,文章名为《徙戎论》。至今成为成语的该句的后半句则是“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虽然职任孝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朝太子洗马的江统将少数民族迁出中原、发回本土的建议,未得西晋最高当局采纳[参见张宏儒等编《廿五史纲鉴》(上册),P55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元末至今,仍流传着月饼来历的故事,称曰“八月十五杀鞑子”。鞑子,是指“非我族类”的蒙古人。至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时,类似的种族主义心理形成了革命纲领,即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参见李治亭《清史》(下),P1806,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02年版]。由于这一口号的种族主义倾向太过尖厉,而不利于日后国家的重建,所以,不久之后,革命党人修正了其种族主义目标,称曰:“故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共官吏也。”[参见李侃等《中国近代史》,P344,中华书局2004年版]
用阶级冲突来冲淡种族主义情绪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奇观,但是,这种浅显的策略之变本身并没有改变底层社会积之已久的政治心理,正如当今执政党主导的政府政治在外交方面虽然与西方世界保持了密切联系,但在其党的宗旨方面并没放弃埋葬(至少是战胜或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一样。随着阶级意识的伪问题化,种族主义情绪又借助民族主义概念“复活”为底层社会心理。并且,“底层”的概念也不只是指引车卖浆者流,也包括了受过相当教育的心灵结构扭曲的知识分子。“革命”的世界观、复仇的泛民族主义心理之教育体系,是造成那类人心灵结构扭曲的主要动力。对满族作为古老通古斯族(中国西周时代称之为“肃慎”)的历史考证,在文化心理上重复了“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历史文本,尽管时至今日满族基本上被汉族所同化。比如,就满族先系女真人是否炎黄子孙问题的讨论,种族主义者的观点异常显明:“满洲人系外来通古斯人”,“不是中华本土原生的炎黄子孙,这些不是炎黄子孙的化外胡虏占了中国,统治奴役了所有炎黄子孙,剧烈破坏了中华文化,打断了文明进程。即是外来的,又是不同种类的,还是极端落后愚昧野蛮反动的侵略统治,不叫亡国叫什么!”[参见百度“女缜(真)是否炎黄子孙”条目,post.baidu.com/f?kz=101474567,19k.2006-6-16]
且不说清代的反动统治绝大部分是由于因袭明朝制度之故,即便是其屠城政策也是对汉文化的效法。汉文化无论在其扩张期还是内敛时期,均以屠城为恐吓对手的手段之一。唐帝国对楼兰的灭种政策诗性化为“不破楼兰终不还”,明帝国的合法居民在李自成张献忠反叛时期也遭受了李张的屡屡屠城。仅就清后斯的洪秀全反叛来看,太平天国进入南京后不仅杀了四万曾经抵抗的居民,而且还阉割了三千男童。虽然太平天国杀人的绝对值比后来日本侵华时南京大屠杀要少,但是其缺德程度远在后来的日本人以上。日本人有战争暴行的共同特征,如强奸女性,但尚未敢复制太平天国的阉童行为。
作为种族主义变种的中国民族主义,有时甚至藐视他们所尊崇的国家形态的附带利益,比如用中国传统政治斗争形式谣言来宣泄积忿。这种宣泄,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谣传新疆在内地做饮食生意的商人要对汉族人发动“生化恐怖袭击”,说是他们将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放在羊肉串里,让汉族消费者食用。
对于这样的谣言,国家机关虽然没有进行追源,但它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种族主义的劣根性及其狂热性。仅就常识而论,艾滋病毒与乙肝病毒是无法存活于温度达到摄氏百度以上的烤炙食品上的,还有,艾滋病毒根本无法通过饮食途径传播。好在现代人们具有了类似的常识,而不致于产生大规模的恐慌。
二、国际压力下的生存窘境
在界定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特性后,需要说明的是:用近代政治包装的中国民族主义从出生那天起,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比如关于外蒙问题,中共方面的态度是:认可民族自决,等到全国统一政权出现后,再吸纳外蒙回归。
共产主义的反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种族主义特质,把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中国共产主义精英集团夹在了中间。作为宣泄的突破口,这个集团在取得全国统一政权之后很快与苏联国际体系决裂,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得不在两种世界霸权的压力下度日,所谓第三世界,也不过国内民族主义与国际霸权压力之间的一个缓冲而已。而无论毛时代对“两霸”的反对,还是邓时代的弃苏向美,乃至于今日与美战略关系的模糊化,其中无不以判断美国的实际影响为民族主义要务。形象地说,闻美国盛则心绪忿忿不平,闻美国盛而不久则窃窃生其喜色。当然,整个世界的重要国家或地域性国家集团无不以美国的盛衰为外交政策变动依据,只不过是民族主义文化(而非止情绪)影响下的中国过份敏感而已。
过分敏感,之于个体,是忧郁症的表现;之于中国的特质民族主义,其政治忧郁症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往往张皇失措,因此根本没形成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责任大国之地位。
就目前整个世界的政治研判而论,关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大体有三种判断:
(一)相对衰退说。美国的霸权将很快消失,这是因为“新力量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不是美国自己衰落了,而是实体变强了”,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参见理查德•哈斯:“美国霸权结束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载于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4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18日]。
(二)地理优越说。支撑强国续存的要素有三,是人为土地、人口和可耕地数量的协调配比。在这个协调配比之外,还有三个辅助因素,分别为丰富的资源和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高智商的战略人才[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未必更好”,载于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4月19-20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23日]。罗保•肯尼迪经过历史比较与现实分析,得出的结论说:“美国在国内表现不佳,在全球各地则表度表现。但如果——非常大胆地假设,抛开这一点,只看其幅员、人口和食品供应之间的等式,美国的相对地位则好得不能再好了。”[同上引]
(三)世界过渡说。这种判断是基于美国国家战略失误及战略惯性而作出的,即单边主义失败而美国又必须防止真正竞争对手的出现,因此它自己破坏了现有的游戏规则[参见皮埃尔•科内萨:“美国对欧洲构成威胁吗?”,载于法国《外交世界》杂志2008年4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30日]。由于美国本身的“主动破坏”,全球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界不会充斥黑暗和危险,反而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参见法里德•扎卡里亚:“他者的崛起”,载于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12日(提前出版),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5月5日、6日、7日]
依中国民族主义的观点而论,他们欢迎相对衰退说,但事实上此说即能实现,也非短期内出现;对于地理优越说,世界无人否认,但这不能以否定中国“和平崛起”的机会为前提;那么,最好是让世界过渡说成为一种新的认知模式。
远远超乎中国特质民族主义的“全面底层化”现状的极少数精英分子,将世界过流说扩展为“西方的焦虑”。西方的焦虑固然存在,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几乎不为极少数精英分子关注,因为他们更愿用自己的焦虑情绪来比衬“西方的焦虑”。他们认为:“8年前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西方支持我们办奥运会,希望办奥运可使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那时的中国远不像今天这样强大,在申奥成功后的这些年,中国已经朝着西方当初希望的方向,不断深化改革、进步发展。而今天西方很大一部分势力却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参见曹理达采访时殷弘等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焦虑”,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5月12日]
中国极少数民族主义精英的焦虑之存在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它与对民族主义的“品种改良”的诉求相一致,因为现代民族主义作为对全球化发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它需要中国“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有效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参见郑永年:“在压力下重建民族主义”,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4月2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23日]。不能适应全球化的民族主义是国家崛起的阻力。这样的判断虽然是一项新的常识,但是正如西方世界的物质输入初期往往被冠以“洋”(如火柴曾叫洋火、煤油曾叫洋油)一样,它仍需要一个艰难的知识蜕变过程。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一方面要看执政集团本身如何对待民族主义情绪,即不再把义和团主义当作国际表述手段;另一方面,还要看全球化的温和程度,即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如果过于激烈反而会驱使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更强烈地与它对抗。
当然,可以预见的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对抗只可能是全球化的一个个别侧面,因为文化互溶性或叫软实力的影响远远超乎国家意识形态集团的主观愿望。这也是为什么郑永年向国内输送“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参见郑永年:“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转型”,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5月7日]之新常识的原因所在。
三、民族主义的文化性与经济性难题
既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衡量指标之一,那么积极地以软实力来影响世界也自然成为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之一。如此,有利民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包装就成为必要的国际战略选择,何况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要求整个世界学习有“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以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呢?
以孔子学院建议为代表,中国似乎领导着一个叫做“脱美入中”的世界潮流[参见韩方明:“推广中华文化的契机”,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3月5日],然而孔夫子的思想能够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暨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幻觉,因为孔夫子的政治伦理恰恰与现代人权观念相冲突。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孔夫子的思想与新黑格尔主义十分接近,他们的国家至上的政治伦理不仅压抑人权,而且会为法西斯主义借“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结构勃兴提供文化性前提。除非“孔夫子的思想”只是一个文化商标、一个壳子,而后为了全球化目标,人们再往里填入新东西。而就人们一直常识化的“孔孟之道”来说,也是很有问题的,比方说,孔夫子主张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而孟子则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不合民心的君主(和国家体系)。
中国历史的文化有着自身难以协调的内在矛盾,仍是“孔孟之道”问题——为什么一个制造暴君的道德标准(孔子理论)与一个制造暴民的道德标准(孟子理论),竟然被合并一套“统一”的价值观了呢?还有,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追求早在110年前就发生了,但那场称为戊戌变法的运动何以失败了?关键的问题就是变法集团陷入了文化悖论,他们想利用“改装”后的孔夫子思想为自己提供文化合法性,但最后却被自己的虚构(即“改装”)所打倒[参见綦彦臣《宿醉的王朝:1860-1889晚清三十年,P196-203,“两个逗号,绊倒了康有为”,九州出版社(北京)2008年版》]。设使中国还有政治改革的话,那么它必然要与世界文明一起走向未来,而不是什么复兴孔夫子的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体,即如有远见的学者所指,必须“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政治民主”[参见党国英:“中国改革:携世界文明走向未来”,载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18日]。
放下针对孔夫子提供的政治伦理检讨了不论,也不必讨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那些“属于少数精英的特权”的政治问题,只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成果分配——人权改善差距”这样一个结构,人们不难发现:(一)改革的经济成果被少数人占据了大部分,通俗地讲,贫富差距极度拉大,造成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政治危局;(二)社会主义的国家福利性与市场化存在严重冲突,通俗地讲,“社会主义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伦理与企业环境不可能协调,高额税赋不仅导致了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而是“血汗工厂”的基本动力[参见綦彦臣:“血汗工厂问题之我见”,载于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6月号“经邦济世”专栏]。
社会主义的国家福利性必然以国家便捷地取得高额税收(财源)为基础,因此,在倒挂的联邦税制之外,国企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迅速地膨胀,而正是这样的膨胀,实际上恶化作为人权指标的公民经济权利。依据国家公开的权威性数据而计算:(在2006年年底)全国国有土地加国企的总价值是79亿,十三亿人口人均国有财富6万元;假如这部分财富增值按GDP每年10%计算,每个公民年获“不劳而获”的资本红利应该是6000元;以五口之家作为家庭标准,每户应得年利3万元。而实际上呢,对每一个家庭或个人,这些都是“虚拟收入”,因为民族主义的国家结构不仅有强行的政治代理功能,强行的经济代理正然是牺牲掉了大部分人的经济人权。
经济人权被牺牲的结果是“政府的钱多得花不完”,比如2007年,“全国财政税收增长31%,达到5.1万亿元。从1995年至2007年,虽然GDP年增长速度为10.2%,国家财政税收年增15.9%,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仅8%,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增速度仅6.3%。”[参见陈志武:“新形式的‘国进民退’不利经济转型”,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3月3日]。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导致经济人权畸缺的最根本原因。
结语:难破解的诡谲
就世界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来看,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自由主义并一定对立,并且它与自由主义一样具有浓重的平民情结,强烈地反对传统特权。“自由主义承认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实现自由目标。但自由主义乐于迎接未来,民族主义则如果说不是尊崇过去也是欣赏过去。”[同前引赵丰译拉尔夫,2001]。在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则无如此幸运,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特别以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为能事、为合法性之一。究其历史原因,一则是由于东汉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独立风格渐变为无赖之风,所谓“盗嫂受金不咎也”之类的表现;二则是明清以来,皇权统治毫无理性,出尔反尔,所谓“今诏直言明日罪之”之类的表现,更加人身消灭也频频发生。
中国当代政治的无赖之风以毛泽东立梁漱溟为反面教材而最为典型,而皇权传统之未变以江泽民时代镇压宗教及钳制言论为全球化文明中的反动标本。这些都为民族主义性格从种族主义变种蜕变为反文明、反理性的思潮提供了现实支持。中国要想从具有种族主义特质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带有内部伤害倾向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承认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基石的地位,至少要阻止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无端攻击。然而,就目前的政治理论生态来看,尚未发现民族主义有“软化”自己的倾向,自由主义一方也没有出现与民族主义和解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