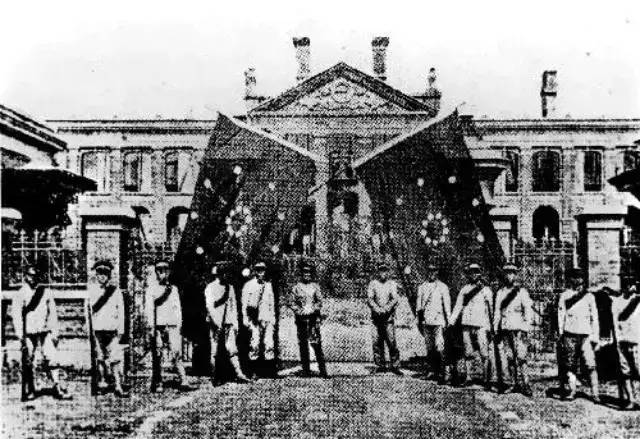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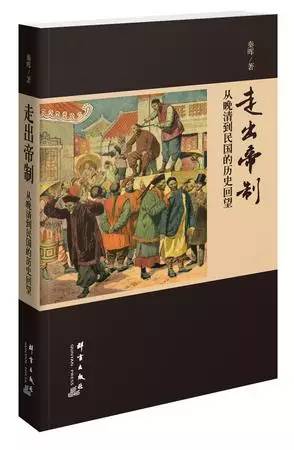
如前所述,革命党人确实以“我国今日为异族专制,故不能望君主立宪”作为废君革命的主要理由,甚至明言“中国而欲立宪也,必汉族之驱并满洲而后能为之”。但真换了汉族皇帝(如后来的袁世凯)他们就能接受吗?孙中山当时就提到,以现在的政治如此腐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可见当时激进主义确实有市场。除了推翻“异族”外,革命党人主张民主共和也还是有追求“彻底”的因素—其实,就是绝不接受“异族”君主这一点,本身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激进”,我们知道欧洲搞成了君主立宪的各国,在“封建”时代接受“外来国王”如同家常便饭,就拿公认的君主立宪第一样本英国而言,众所周知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从外边请来个荷兰人威廉三世取代了他的正宗英国人岳父。后来立宪英国更是接连出了两个“外族王朝”,即源于德国的汉诺威王朝和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当时“德国人”乔治一世国王因不会讲英语而不愿出席枢密院会议,形成惯例后使枢密院脱离国王干预而演变成后来的内阁。显然,“异族”君主的存在甚至还是英国君主立宪得以顺利发展的因素之一。而中国的革命党不接受君主制也不仅仅因为清朝君主是“异族”,如前所述,汉族君主他们也是不接受的。
不过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革命派虽然连汉族君主也不愿接受,立宪派却是接受君主而不在乎其为“异族”的。当时国内革命党的影响远不如立宪派,假如清廷甘愿转变为“虚君”而接受立宪,立宪派的力量加上朝廷,应该完全能左右大局,革命是很难发生的。但问题在于清廷这样做的可能几乎没有。而说实话,清廷之所以不可能主动做“虚君”,也有不得不然之理,而且这主要还不是出于满人的“恐汉症”,正如革命党不接受君主主要不是因为“仇满症”一样。
其实这不需要太多的引证。我们看看世界上成功通过君主立宪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国家,无论是西方的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等,还是东方的日本、泰国,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却仍然稳定地得到臣民的尊敬。反过来说,他们王室的地位主要以“德高望重”或某种宗教光环为基础,甚至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如代表某个家族的纹章)也能约定俗成地被认为不可侵犯。这样的王室当然不一定要掌握实权,而没有实权也就不能为害,即便时政多弊,也责不在君,公众要求革新时政,但并不怨恨王室,也不支持谁去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正统主义”而非“皇权主义”。实际上那些王室在历史上就经常“大权旁落”,却仍然能够“皇图永固”。
而那些历史上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从我们周围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直到“圈”外的沙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埃及等等,都没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它们都是或者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走上了共和民主的宪政之路,或者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极权制度,因而至今仍然面临民主化的问题。唯一在君主立宪道路上走得比较久的是伊朗(波斯),巴列维王朝的“日本式立宪”(类似清廷的“预备立宪”)和自由派的英国式立宪斗了几十年,最终也是同归于尽,而被霍梅尼式的“神权共和国”代替了。
所以我认为过去我在《传统十论》中讲的一段话还是对的: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早在辛亥革命中就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另一方面千年怪圈在此之后仍然延续。如今有人责怪辛亥革命太激进太反传统了,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才适合国情顺应传统。其实,辛亥的局面完全可以用传统逻辑来解释,倒是君主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悖。试观英、日等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传统上王室不仅没有我们的这般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更受敬畏。不说是“万世一系”,但起码没有“市井之间人人可欲”。即使在自由平等之说盛行的今天,即使是激进的左派执政,人们也还尊敬王室(正如即使是保守的右派执政,也还尊敬工会)。
而我们那神秘却不神圣、令人恐惧却不敬畏的传统王朝,本身就有“汤武革命”的传统周期。清朝至辛亥已历时260多年,即使无西学传入,也是“气数”该尽了。若无西学影响,也会改朝换代。有了西学影响,清朝之后便不再有新王朝,尽管仍然有专制,但若还打清朝旗号,这本身就已违反传统了!我们已经看到,在真实的传统中,国人之所以尊崇君主,与其说是基于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说主要是慑于“法术势”。因此立宪制度下失去了法术势的“虚君”是很难得到英、日等国立宪君主所受到的尊重的。那些国家在近代立宪制度之前的历史上就常有不掌握实权的“虚君”,也形成了尊重虚君的传统。而我们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大权旁落,哪怕是旁落到至亲如母(如唐之武则天)、弟(如宋太祖之于赵光义)、岳父(如西汉末之王莽)、外祖父(如北周末之杨坚)之手,便难免性命之虞。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要么是命运悲惨的废君,而“虚君”比共和离“传统”更远。废清皇室在民初还能保有一定地位而没有落入墙倒众人推的没顶之灾,从历史上看已属难得了。
要之,法道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它除了导出众所周知的“贤君”、“王道”理念外,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所以我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是毫不奇怪的。如果说共和理想在政治上显得很激进,那么它在“文化”上倒似乎很“保守”。它的很多内容可以在不满“秦制”的古儒传统价值中找到支持(注意:这里说的是在价值观中找到支持,不是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宪政”已经被古儒发明了)。
可见传统“秦制”本身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悖论。它与我国历史上“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况是对应的。那种把清亡后出现混乱局面简单归结为“西化”与“激进”所致的看法是肤浅的:如果清亡后的混乱是因为西化,那以前的历代王朝灭亡时产生的混乱又是为何?换言之,清亡后的乱世究竟有几分是现代化“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几分只是“治乱循环”传统怪圈的一环?
辛亥革命推翻了什么王朝?
这里我还要说:过去我们把西方历史上所谓的dynasty中译为“王朝”,西方人也同样把“王朝”英译为dynasty,现在看来这很值得商榷。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中有人说,中国改朝换代时的社会大动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有篇文章就反驳说:改朝换代是每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像英国历史上就有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前后相继,法国也有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华洛瓦王朝、波旁王朝新陈代谢等等。这显然就是把他们的dynasty更替和我们的“改朝换代”混为一谈了。
古汉语中的“王朝”一词有褒义,指的是上古“三代”作为“诸侯国”的宗主,尤其是指西周。“王朝”就是周天子的朝廷,它与后世的“汉王朝”、“明王朝”一类说法是有区别的。而周天子的那个“王朝”在“封建”制下延续800多年,与英国从今天可以一直上溯到征服者威廉的一连串dynasty实际属于同一个王系,倒有几分相似,但与“金雀花王朝”、“都铎王朝”这样的一个个的dynasty就大不一样了。至于秦以下历“朝”,与西方的dynasty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西语中的dynasty,据说词根出自古希腊语,意思就是权力、能力(power, be able to),这个词本身原来并不涉及权力的来源,无论选举的还是世袭的都可以用。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掌权的往往连续来自同一家族,于是这些“权力家族”就被通称为dynasty。像罗马帝国的所谓朱利亚·克劳迪“王朝”、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等等。这时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变成私相授受了,但形式上还要经过国会(元老院)选举这一程序。私相授受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可能授给外甥、养子、侍从,甚至是前帝看中的某个“贤人”(即类似中国所谓的禅让),而不一定是儿子,更不一定是嫡长子。到了罗马帝国晚期乃至中世纪,世袭已经成为常规,选举的形式也往往没了。国人把这时的dynasty称为王朝似乎已经很像。但实际上,由于这时的国王其实不过是诸侯的盟主(有点类似周天子),实际权力有限,而且在“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规则下,国王实际上只有一些附庸(封臣)而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所谓臣民,甚至往往都不怎么征收“皇粮国税”,而主要是靠王室自己的领地(有点类似西周时天子的“王畿千亩”)为生。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下的王统却显得十分稳定,贵族们尽管争权夺利,却对王统无非分之想。传统时代难有王统的更易,近代化中保留王统的几率也很大。
就以英国而论,自1066年诺曼征服者威廉占领不列颠后,号称是经历了诺曼(1066—1154)、金雀花(亦称安茹,1154—1399)、兰开斯特(1399—1461)、约克(1461—1485)、都铎(1485—1603)、斯图亚特(1603—1649,1660—1714)、汉诺威(1714—1901)、萨克森—科堡—哥达(1901—1917)、温莎(1917年至今)等一连串“王朝”(即dynasty),但实际上,这些“王朝”都是从征服者威廉这一条“根”上出来的,这点从未变过。
例如诺曼王朝末王斯蒂芬死后无嗣,他的堂妹玛蒂尔达作为诺曼王室的唯一合法后裔,嫁给了封地在法国的安茹伯爵格奥弗里,其子继位为英王,就成了安茹“王朝”的首王亨利二世。而安茹伯爵以金雀花为徽章,安茹王朝因而也叫金雀花王朝。该王朝的末王理查二世承袭祖父之位后,因“独断专行”引起臣下不满,他们乘他去爱尔兰时支持其堂兄(太上王的另一孙子)兰开斯特公爵取而代之,称亨利四世,这就算开始了“兰开斯特王朝”。不久那位太上王的又一个孙子约克公爵起而争位,并一度取得优势,这就是“约克王朝”。而兰开斯特王室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公主卡特琳改嫁威尔士贵族欧文·都铎,其孙子又娶了约克王室的公主伊丽莎白,于是兰开斯特与约克这两个竞争的支派又重新合流,新王亨利七世以都铎家族的纹章为王徽,就算建立了“都铎王朝”。都铎王朝的末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身未婚,临终时指定亨利七世女儿玛格丽特公主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婚姻所产生的后裔詹姆士一世继位,王徽也改用了斯图亚特家族的纹章,于是“斯图亚特王朝”宣告建立。这个倒霉的王朝碰到了英国革命,一度被共和派推翻,11年后又“复辟”,但复辟后的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信天主教而被革命后英国的新教人民罢黜,人民请来他信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她的夫婿荷兰亲王威廉作为夫妇“双王”,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但这一“革命”并未导致“改朝换代”。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尽管实质上已经是虚君共和、议会民主,形式上却不仅有国王,而且连王徽都没改。与历史上王室女性夫婿继位后就改以夫家族徽为王徽从而开始“新王朝”的习惯不同,威廉夫妇尽管政治(宗教)立场与先王不同,却仍沿用妻家的(即先王的)纹章,也就是延续了斯图亚特王朝。直到1714年,由于安妮女王无嗣,王位改由斯图亚特王室公主索菲亚和她的德国新教徒丈夫、汉诺威选帝侯的儿子乔治一世继承,并换用了汉诺威的王徽,于是出现了“汉诺威王朝”。而这个“王朝”的末王不是别人,正是大英帝国全盛时代的象征、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
“光荣女王”是个“亡国之君”?
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想象,两场“革命”都没有“改朝换代”,而风平浪静、作为英国历史辉煌顶点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竟是个“王朝末世”—这个英国历史上如此声名显赫的伟大女王、在位长达64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君主,如果按中国人的“王朝”概念,却应该算个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不是吗?汉诺威王朝就是在她手中“灭亡”的:由于她的丈夫是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因此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继位后就改用了父亲家的纹章,于是建立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由于这个王朝名称来自德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成为敌国,王室为了显示民族立场废除了萨克森的称呼,改用时任国王乔治五世继位前温莎公爵的纹章。于是英国又出现了延续至今的“温莎王朝”。
显然,1066年以来英国的王系血缘至今一脉相承,历时已近千年,只是不一定由父系、时而由母系延续而已。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不在乎“外来的”国王;但另一方面,这些“异族”国王必须多少传承原来王室的血缘成分,绝不轻易中断这种血缘的“王统”。尽管王室也有内乱,有王位的争夺,包括像兰开斯特家与约克家争斗导致的“红白玫瑰战争”那样的大混乱,但这一切始终都是征服者威廉后裔这个王系内部的事,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外人”从来就不会参与。所谓赵钱孙李都来“群雄逐鹿”、“问鼎中原”、“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这样的事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统的中断和改易,除非发生来自异族的征服才有可能,如1066年征服者威廉统帅的诺曼人入侵,消灭了土著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王国,又如更早时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不过像这样的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已经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的更替,即黄宗羲所谓的“亡天下”,而不仅是“亡国”了。
不过除了1066年以前那几次“亡天下”,那里似乎也无国可亡。更多的情况下上述“改朝换代”只是王室的家务事,社会上波澜不惊,通常不过就是换了个王徽而已。像“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有谁记得她是“汉诺威王朝”的“亡国之君”?笔者曾经问过几个学历史的英国留学生:贵国最近几次“改朝换代”在什么时候?皆曰不知。又问:1901年(汉诺威王朝终结)、1917年(温莎王朝开始)在英国发生了什么事?答曰:1901年?我们在同布尔人打仗,1917年那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问:我说的是英国国内。答曰:国内?没什么事啊?他们没人会想起那两次“改朝换代”。实际上那也的确不是什么事。
总之,在英国人的传统中,国王就是那家人干的,别人没那个命,想都别想。那家人的事大家都很感兴趣:从戴安娜的车祸到威廉王子的婚礼。但我们各家各户的事他家管不着,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他家也不能管。即便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今天,英国人也不会有像我国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但另一方面,我国帝王那种权势他们也是闻所未闻。今天的“虚君”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年的“实君”也实不到哪里去,连征税那样的事也要跟纳税人商量过才可以征。所以“改朝换代”在他们那里算不上什么事。一千年来英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包括1215年的大宪章、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和英国革命,都与“鼎革之际”无关。
英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政治变革、制度转轨、社会动乱。黑死病曾经导致英国人死去三分之一,“封建”时代的英国对外有过百年战争,内部有过玫瑰战争,后来革命中还处死过国王,发生过内战,但那与“改朝换代”都没有什么关系。暴力的英国革命与和平的光荣革命都没有导致改朝换代,包括仅仅是更换王徽这种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也没有成为这种革命或动乱的结果。
最后,尽管“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这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英国(传统上特指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而且那确实是农民与他们的贵族主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显示出英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但是英国的这种“起义”也不会与“朝廷”为敌,不会是“官逼民反”,更不会要求改朝换代。把这种民间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与专制帝制下民间社会与朝廷官府的冲突混为一谈、甚至把“庄主(地主)”带领“庄客”(佃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也说成与英国的“农民起义”性质一样,是很滑稽的。事实上,所谓“农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这种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几乎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不仅英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在所有“封建”的民族,包括我国传统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从未有过。
“半封建”帝国的宪政之路
也不仅是英国,“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东欧的波兰,历史上只有皮亚斯特(960—1386年)和雅盖洛(1386—1668年)两个“王朝”,而两者间“改朝换代”的方式是皮亚斯特王朝末代女王雅德维嘉嫁给立陶宛王雅盖洛,从而实现了“波立合并”。以后的雅盖洛王朝诸王都是这位皮亚斯特王朝女王的子孙。其实说“嫁给”是按中国的习惯,与欧洲中世纪很多政治婚姻一样,更确切的说法是雅盖洛入赘波兰,他不仅定居波兰成为波兰国王,而且放弃立陶宛传统多神教,皈依了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换句话说,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只是王徽从母系换到了父系而已。
在雅盖洛王朝时期,波兰的“封建”越来越甚,王权越来越小,最后发展成贵族共和国,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完全不论家族。雅盖洛王朝就这样被“自由选王时期(1573—1795年)”取代。但有趣的是:自由选王实行两届后,第三、第四、第五三届国王当选的都是雅盖洛家族的人,此后就再没有该家族的人当选了。所以通常雅盖洛“王朝”被认为延续到1668年,与自由选王的贵族共和国有将近百年的重叠。在这个时期雅盖洛王室的国王完全按共和制原则选举出任,而且与非王室的人交叉当选。换言之,波兰不仅两个王朝的“改朝换代”波澜不惊,从王朝到共和也是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仅没有“革命”,连“改良”的痕迹也不明显。你甚至不能说波兰搞的是“君主立宪”,因为它的国王并非“虚君”,他由选举产生,实际等于总统。但他又绝非“实君”,实权操于议会。只能说这时的波兰是个“有国王的共和国”。
如果换成我们中国的概念:明朝灭亡后朱家皇室子孙不仅安然无恙,还可以通过选举多次“复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制度也具有“半封建半帝制”特点的俄罗斯。
俄国历史的早期也是完全“封建”的。她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延续了736年之久(862—1598年),期间经历帝国分裂、蒙古入侵、实际霸权在诺夫哥罗德、基辅、弗拉基米尔、莫斯科之间多次转移,但王公与后来的沙皇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直到末王费多尔死后无嗣,王朝才告终。经过15年混乱后,贵族会议选举留里克王室的亲戚米哈伊尔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被俄国革命推翻。因此俄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也只有一次因国王无嗣导致的“改朝换代”,而且前后两个王室仍有亲戚关系。
但有趣的是:俄国后期三百年里逐渐由“封建”向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演变,贵族政治没落,皇权官僚政治兴起,王室外的人们乃至平民以武力争夺皇权的“群雄逐鹿”现象也随之发生。这一时期的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民变”领袖都曾有“问鼎”之志。而这是“封建”制下的西欧和俄国前期从未有过的现象。但是处于“半封建半官僚制”下的沙皇俄国与基本上是官僚制集权帝国的中国仍有区别: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皇权觊觎者只是假冒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自称拥有真沙皇,而反指莫斯科的沙皇为鱼目混珠,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威而追求“改朝换代”的。而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到了近代,俄罗斯也一度有过和平的君主立宪机遇,尤其在1905年,沙皇和维特首相,乃至民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革命派”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既难说服庄稼汉,又难说服小市民的。当时沙皇—维特的立宪计划实际上是“半英国式的”,与立宪民主党的计划虽有距离,但比清末朝廷的“次于日本式立宪”和民间立宪派“英国式立宪”的距离要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谈判破裂,专制政府进行镇压,宪政进程出现逆转。虽然此后这一进程又缓慢启动,但时机已失,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庄稼汉还是小市民都失去了耐心,革命大潮于是席卷而来,和平立宪的机会丧失了。
经历了流血无数的“改朝换代”和更严酷的古拉格时代之后,俄国度过了70多年,终于又走出了斯大林体制,而且总体上还是和平的。虽然有8·19政变、有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乃至车臣那样的局部战争,但是无论与沙俄帝国崩溃后死亡数百万的惨烈内战,还是与大清帝国垮台后的民初动乱相比,苏维埃帝国的解体后遗症应该说是轻得多。至今20年来俄罗斯的宪政民主之路坎坷曲折,但并未出现实质性逆转。可以说从近代以来,这个进程在俄罗斯就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西欧)更坎坷。这个现象并不是“宿命”的,但无疑,俄罗斯的“封建”传统介乎西欧与中国之间,使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出现几率。
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欧洲的“封建制”当然有基督教“文化”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但它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封建”这种制度、而不是基督教这种“文化”决定的。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专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逻辑,而不信基督教的“封建”国家,比如据说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属于“印度文化圈”的泰国(包括我国傣族的西双版纳)却有类似的逻辑。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除少数例外通常也是“虚君”,却长期受到遵奉,“万世一系”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没有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现象倒是真的。明治维新本身如前所述,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区别很大,却有浓厚的“周秦之变”色彩,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发展下去,日本走向民主固然难矣,但成了“实君”的天皇恐怕也再难“万世一系”。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下克上”已经多次发生刺杀首相,谁敢说进一步就不会发展到刺杀天皇?只是这段历史很短。倒是到了战后在美军占领期间,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日本成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虽说是“英国式的”,其实从天皇恢复为虚君而受到国民稳定的拥戴来看,又何尝不是回复了“传统”逻辑、走上从“封建”到君主立宪的道路呢?
总而言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权的“敬畏”乃至敬爱,在传统时代它的“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现象,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它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就比较容易。而专制帝制就不同了。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以及人的恶习只有“1.软弱,2.懒惰,3.愚蠢。其他一切(上面提到的除外)无疑都是美德”的批语。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秦制”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为系统和典型。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虚君”不是犯傻吗?传统时代“改朝换代”,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么容易?
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遵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以后之“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搞的也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就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过,如果和平宪政的可能不大,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那么既不立宪也不革命,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传统”求复兴,或者充其量搞点“洋务”,船坚炮利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其实早在戊戌以后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不过近年来在“革命派”“立宪派”都被认为太“激进”、太“西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奇迹”鼓舞人们重兴“传统”,“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的潮流中,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实际上已经相当时髦。所以我们还要重新分析一下:在过去的很多成说已不成立的情况下历史能否完全颠倒过来?为什么在和平宪政可能不大的情况下,人们又不能继续容忍帝制,以至于使革命成为一个未必“必然”但却是大概率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