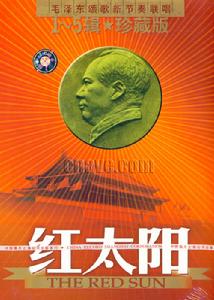
齐国上大夫晏婴老师曾说过,“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所以我们现在讲究礼貌性上床,礼貌性上床的同时还要礼貌性叫床,女人的呻吟对男人来讲就是床上最美妙的颂歌,颂歌一定要认真诚恳发自肺腑,不能无病呻吟敷衍了事,最近流行的那几曲颂上之歌,叫声里的职业性、风尘味实在太浓,一听就不是烟花柳巷里未成曲调先有情的佳作,充其量只是路边大保健里的叫卖声,这种颂上之歌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鸡之谈,阉人不知男女事,法海不懂许仙爱,自然也就写不出好的颂歌。
自古以来,颂上就是一件听上去不那么高级的事情,也是一件令人矛盾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颂,风骨全无,不颂,则有可能尸骨全无,在风骨和尸骨之间,人们往往选择保全后者。即便是颂,他们也尽量表达的不那么露骨,婉转曲折,含蓄内敛,类似于“毛主席赛过我的亲爷爷”和“斯大林是我爸爸”这样的词句是没有的。颂,不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地位都比较低,《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历来就有“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的说法,而十五国风指的就是从十五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谣,那时候的统治者听取民意、了解民情的方式不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听听民谣,只不过时代发展至今,颂歌已经上床了,但民谣还在路上。
古代统治者对民谣的政治功效和社会舆论影响非常重视,从周朝开始就专门设有“采诗之官”,这里的“诗”就是指民歌民谣。采诗官巡游各地,替统治者采集民歌民谣民女,以体察民情、政治得失,“过则正之,失则改之”,可以说采诗官就是情报官,负责输送各类民间信息,使统治者兼听则明。当年东德也有这样的部门:斯塔西,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他们也相信“监听则明”,四处窃听,发现不满言论立即查办,当时斯塔西的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同样是信息采集,一个是补察时政,向统治者建言献策,一个是清除异己,告诉统治者天下太平,这就是古代的民谣,这就是东德的颂歌。
到了汉武帝时,汉朝正式设立了乐府,是进行音乐管理的行政机关,汉乐府所采集到的民谣流传至今,有不少都是反映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比如《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到了唐朝,唐诗不仅承继了汉朝乐府诗的叙事特点,还丰富了表现手法,多了浪漫和写实。白居易老师和元稹老师等人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主张恢复采诗制度,发扬汉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作用,新乐府时期出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佳作,就不一一赘述了。白居易老师为什么和元稹老师一起合作呢?这并不奇怪,当年大唐盛世,娱乐业飞速发展,很多社会名流醉心于青楼之上,这其中就有一向以“苦大仇深”的诗歌示人的白老师,当然也少不了多情的元老师,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令无数女子为之宽衣解带,都是青楼资深VIP,两人自然有机会相遇,据说二人还交换过小妓,那么交换一下彼此的想法一拍即合搞了新乐府,也就说得通了。回到现在,历史惊人的相似,唱过“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你还给傻逼织毛衣”、写过“那一年的寒风中,你化了很浓的妆,第一次牵我的手啊,却装作老练的模样”的卢中强也跟两个朋友一起搞了个“新乐府”,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搞在一起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神州大陆是没有青楼的。卢sir之前做的是民谣在路上,这次做新乐府心很大,目测有D杯,我看过他们其中的一个项目“新乐府|昆曲”,真的是很好,女主角特别好。
生活需要批判的一面,但也需要歌颂美好的一面,就像白居易老师既写过“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样描写社会悲惨面的诗句,也为自己心爱的两个家姬樊素和小蛮写过“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样歌颂美妙少女的诗句。只不过颂歌的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创作者心甘情愿去做,而不应为了某种目的或迫于某种压力去做,李白当年虽然是受唐玄宗之命为杨贵妃写颂词,但见了杨本人后确实感觉倾国倾城,于是写下了千古佳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同一时期对杨贵妃动了真心谱写出美妙颂歌的还有唐玄宗以及安禄山,唐玄宗亲自写了《霓裳羽衣曲》当作颂歌献给杨玉环,一向以批判为主业的白居易老师称赞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还有一次贵妃出浴,酥胸半露,玄宗摸着她的胸脯说:“软温新剥鸡头肉。”,安禄山老师则接下句说:“滑腻初凝塞上酥。”,不用再多举例子了,什么叫真爱,什么是真颂歌,显而易见。
贵为天子还要自己亲自写颂歌的很多,除了唐玄宗还有汉高祖,“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喜欢自带颂歌的还有曹操,外出考察时情绪来了,就给自己写了个颂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说,现在热衷于写颂上之歌的人一定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要动不动张口就喊爹啊妈的,粗俗不堪,不仅颂不了,反而成为笑柄。
宋代谢灵运曾说,“士颂歌于政教,民谣咏于渥恩”,在贵国的“颂上文化”里,知识分子历来是主力队员,不论是王朝更替的血腥残暴,还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迫害,都使他们在风吹草动时活得小心翼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一直在延续,即便遭遇了不白之冤,也一心等待上面的“平反”,对于“文革”他们还有“娘打孩子”的说法,拒绝面对真相,到了现在更是期待“改良”、期盼“明君”。对于那些选择创作颂歌的人,我倒觉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毕竟做出了选择,只是水准有待提升,反而是那些既不敢面对当下现实,又要装出一幅推动社会进步的嘴脸的人很可笑,他们一直躲在自己的幻想里,活在虚假希望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建议这些人多听听民谣。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不敢说人话的人,自然只会唱赞歌。如今颂歌已是满天响,民谣却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