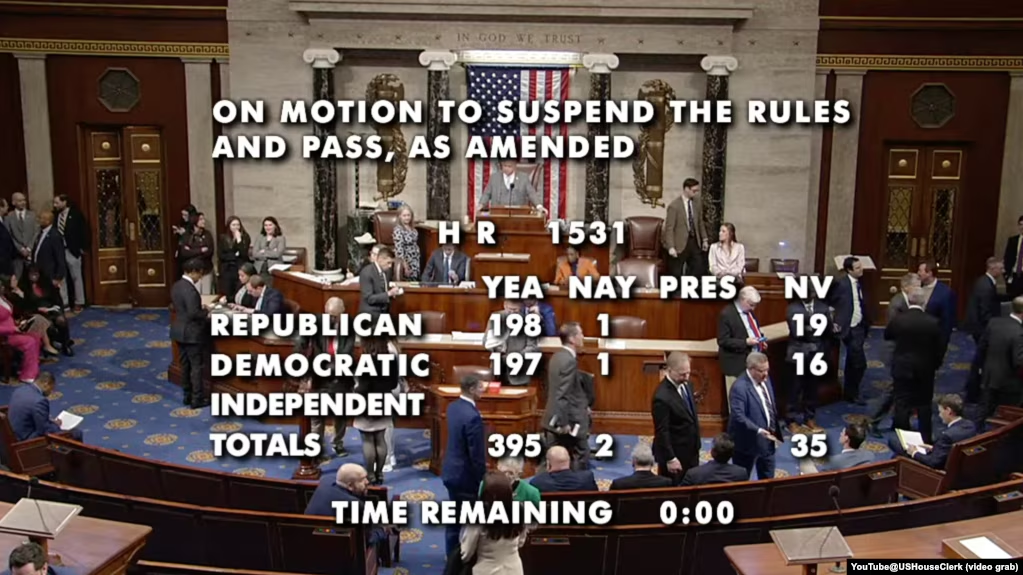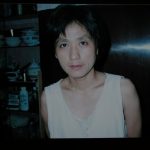当一个时代的青苔,覆盖上一个时代的陈迹,是谁独自叩响人类命运的大门,把足印留在人迹罕至的青苔上?
门内是苦难,门外是迷茫。在一个民族饱含悲剧命运的土地上,他曾荷戟彷徨。比他稍早的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描述同一段历史说:“我像近卫军的妻子,在莫斯科的钟楼下恸哭”,索尔仁尼琴没有痛哭,他像野草一样,“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在这生存之上,他以思考作墓碑。
就已经发生的一切而言,索尔仁尼琴的批判是世界性的;就暴政的现代性而言,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他是“政治上的终身持不同政见者”。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亡者斯塔尔夫人曾说过:“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而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之际,法国左派仍然天真地认为,只要为了崇高的理想,集中营也就显得不那么残酷了。
生于“十月革命”之后的索尔仁尼琴,对现代专制有着惊人的洞察与惊心动魄的体验:“古拉格”指前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而“群岛”则喻指劳改制度渗入到人民生活与政治的各个领域,“群岛”成为前苏联的“第二领土”。索尔仁尼琴依靠记忆与观察,对前苏联法制作出了最精确的描摹。
索尔仁尼琴不是先知,但他是证明与救赎。他一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劳改营、平反与恢复名誉,以及随后而来的被批判与驱逐的流亡岁月,在亲身见证苏东剧变之后,又经历了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的激进民主与经济休克,以及普京时代的复苏。整个20世纪的复杂与迷茫,几乎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隐喻。
“我终生研究和描述俄罗斯辛酸的历史”,在叶利钦时代,索尔仁尼琴对自己有着贝克尔评论罗兰夫人一样的浩叹:“假如罗兰夫人知道自己的理想落实到现实的层面上,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的话,当年她就不会有勇气走上断头台了。”他对俄罗斯的精神救赎在其晚年回到“十月革命”之前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反思录》在去年被普京推荐为地方行政官员必读书目,在此书中他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向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寻找救赎。
索尔仁尼琴回到从前的救赎,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想。当“历史终结”的迷雾弥漫于世界之时,回顾索尔仁尼琴一生,迄今为止,对计划经济以及产生于其上的集权体制的批判非常有效,然而正如自由主义批评家所述,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目标是表达出平等个人主义者的迫切愿望以及由法国大革命推动的合理结果,尝试以另一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努力虽然在苏联遭受挫败,但历史的正当性必然寻求新的路径,这一路径正是索尔仁尼琴难掩的失落与迷茫。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在这个传统上,他与其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脉相承,“他向那仿佛是人类理智和心灵所不可了解的无边苦难低头,一躬鞠到了地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其杰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题词:“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个杰作,公元2008年8月3日,这粒思想的麦子死了——享年89岁——但愿他已原谅仍在矛盾中蹒跚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会自动变得更好,凋谢的理想仍然写着人类命运堪忧。假如理想曾经欺骗了我们,那么,让我们仍然仰望星空,让我们仍然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