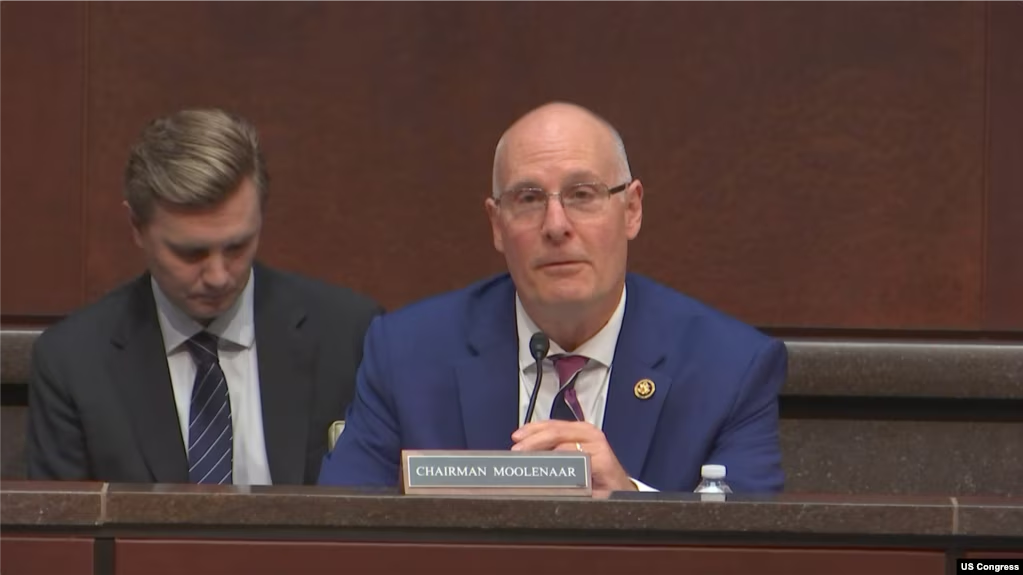吴玉仁(推特图片)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吴玉仁
受访时间:2015年11月15日
受访人简介:吴玉仁 艺术家,出生於1971年,江苏常州人,现居北京,从事艺术创作。2010年5月,因从事“艺术维权”遭到报复,涉嫌“妨碍公务”被逮捕,在羁押十个月后,于2011年4月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得释放。
马萧:请您谈一谈您在这个新调的监室里的生活体验。
吴 玉仁:我在这个新的监室被羁押了将近九个月,一直没有被调号,直到被释放。这九个月时间,我所在的这个监室两次获得全看守所文明号,这种评比每个季度评选 一次,相当有两个季度都是文明号。另外,我在这里创作了更多的艺术作品,比如,用奶糖做牙齿,用肥皂做成牌九,用一些废弃的塑料饭盒的边角料做成刀叉,等等,我还在监室里举办了一次个人的艺术作品展,把所有的作品都展示给其他在押人看。
在看守所,除了要和牢头以及其他在押人协调好关系,如何和管号的狱警相处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在里面过得更舒服一些,获得相对更大的生存空间,狱警是决定性的因素。
狱警其实也是有准备的,尤其是对待那些重点监控的在押人,他们会提前调查、分析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其实每个在押人在分配监室之前,管号的狱警就已经把他们整个人研究、琢磨透了,他们会把那些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人想办法弄到自己分管的号里,但这不是普通的狱警能够做到的,而是那些有一定级别或者资历很老的,总之,在看守所内有话语权的狱警才能够做到。
我在这个新的监室呆了近九个月和那个管理我的狱警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地步,在我同他的接触中,我能感觉到这些狱警就是这么做的。这位狱警是一位老狱警,警衔 和看守所的所长是平级的,因此,看守所发生的很多重大事情,所长都会同他沟通、商量,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位狱警在看守所的职务却并不高,很可能是受到排挤被调到看守所来坐冷板凳的。
当时,这位老狱警知道外界舆论对我的关注度非常高,知道我在国内外非常有知名度,想当然地认为我的作品有很高的价格,对他会有利用价值,于是,就想方法设法 把我弄到他分管的监室。很快,他就提出来要我给他画几幅国画,我虽然最早学的是国画,但那时我早已经不画国画了,甚至连油画也很少画了,我这时主要是创作装置艺术,显然,这位老狱警在艺术领域完全是一个外行,以为国画最值钱,他也只能懂到这个地步,所以让我给他画国画,后来,我也确实给他画了,九个月时 间,给他画了几十幅国画作品,时间一长,这个消息便在值班狱警内部传开了,这个楼道里的其他狱警也纷纷过来找我,向我索画,我也很爽快地答应给他们的要 求,这样,整个楼道的狱警都对我敬重有加。
我是所有监室里唯一一个能够在审讯和“放烟茅”的时间之外,能够自由进出监室的在押人,每天平均可以踏出牢门六七次,专门出去抽烟、喝茶,每次出去抽五、六支烟,然后再回到监室,并且是不同的狱警来请我出去抽烟,有时甚至还会“撞墙”,这个狱警刚刚提我出去抽烟,回到监室还没有落坐,另外的狱警又请我出去抽烟、喝茶。
一 般的牢头也能够在这些时间段之外被狱警提出去,但一天最多也就一两次,早、晚各一次,主要是向狱警汇报监室里各个在押人的表现,说直白一点就是向狱警揭发、告密,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牢头每天能够被提出去两次,就说明他和值班狱警的关系已经相当不错了。而我之所以被提出去,完全是因为另外的原因,因为 我能够给那些狱警提供各种对他们自己有价值的资源,要知道,每次提我出去抽烟,至少要经过三、四道铁门,每道铁门都要开锁、上锁,因此也算是一个工作量, 被提的次数一多,时间一长,我甚至能够凭直觉就能知道谁又来提我出去抽烟、喝茶了,因为每一次他们开铁门、一路走过来,每个狱警拿钥匙开铁门的声音、走路 的声音都不一样,很容易就很猜出来谁是谁,我就经常在监室里和其他在押人一块玩这种竞猜游戏,一猜一个准,很少猜错过。
在一个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一个人对事物的敏感度会大幅度地提升,有些平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会关注的东西,可能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会变得异常敏感,这就好像一个盲人,他对声音会特别敏感,一个盲人的听力通常会比一个正常人的敏感度高出许多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弥补他失去视觉所造成的缺陷。因为长期被封闭在监室里,难以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在押人听力的灵敏度都会提升不少。
对于那些狱警来说,除了想让我给他们画画,他们提我出去还有一个目的,他们也想听我讲故事,和我聊聊天,打发他们自己的时间。其实这些狱警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同样所知了了,他们在这里工作相当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坐牢,因此,他们也希望从我这里获得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作为交换,他们也会向我透露他们所了解到的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在某天有多少多少人在看守所外面抗议对我的非法拘禁,等等,这些东西原本是要对我严格保密的,但相处时间久了,他们也不在乎这些。
在看守所,笔、墨、纸、砚,这些全都是违禁品,香烟、打火机也是违禁品,但是这些狱警都给我提供,我所在的号相当於我的工作室,不仅如此,狱警还专门把监室顶楼的一个房间腾出来,给我做工作室。
除了给这些狱警创作画作,我同时也会给自己创作一些东西,还有写日记,甚至我每天晚上做的梦,我都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除此之外,我在监室里面的另外一项重 要活动,就是给其他在押人讲课,因为我自己就是这间监室的牢头,在押人的日常生活由我来安排,我就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些看守所没有规定的生活事项,给他们讲授历史课,主要是1949年以来发生的真实历史,这是一项专门针对看守所规则的反洗脑课程。
因为号里的监控设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因此,这些课程内容虽然属於违规现象,但一开始狱警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间一长,我才知道,虽然那些监控设备 不能同步录音,但监室内同样有声音监控,在靠近铁门处有专门的声控装置,专门接收号里发出的声音,所以,有时讲课时狱警还会善意地提醒我,“呦,老吴,又在发表反动言论,离门远点,别说这些反动言论。”
后来,还有狱警专门提我去监控室抽烟,监控室的墙上是一块电子屏幕,一块大视频,所有监室的画面在这里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视频下面,是一排电脑,这些电 脑既连结警察内部网,又同时连着每个监室的声控装置,如果警察想要知道某个监室的犯人在说什么,只要在电脑上点击那个监室号的声音控制键,这间监室内的声音就通过喇叭口同步地播放出来。一旦接触到这些真相,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因为每个人的隐私通过这种极为严密的监控程序都在警察的掌握之下。
我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还会经常制作一些小道具,使每堂课听起来更生动、更形象,比如,当我讲林昭的故事时,我在备课的时候,专门用肥皂制作了一枚相同比例 的子弹模型,上面沫上国画涂料,这个模型看上去就是一枚发着青铜锈迹的真实子弹;再比如,当我讲到夹边沟劳改营的故事时,我就专门画了一幅中国地图,然后,将夹边沟在这幅地图上的什么位置介绍给其他在押人,告诉他们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诸如此类。
在看守所,其实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刚被送进来的人,就要想着如何应付密集的审讯,要权衡是批捕还是不批捕,等到被正式批捕以后,每天又要想着如何应付法院的审理,如何给自己辩护,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判多少年刑期,等等,每个流程都是环环相扣的,人一旦被送到看守所来,他的命运就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所以每个人每天都会很焦虑,焦虑这些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还要考虑家人的处境,等等,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其实每个人都会带着一种病态的眼光来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为什么在看守所里面很多牢头都会经常虐待新人,殴打其他在押人?其实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焦虑,舒缓自己的内心压力。
而我则通过这种给其他在押人讲课的方式,把同监室的其他在押人从这种焦虑感当中解脱出来,同时也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尽量让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得有内涵,有意义,把枯燥乏味的看守所生活转换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我在里面还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在监室里,所有人都不许打人,不许说脏话,从牢头自己做起。因为我自己就是牢头,所以这个规定实际上是约束我自己,同时也束缚 其他在押人,如果谁有违反,就要受惩罚,但也不会像其他监室一样,随意地虐待在押人。主要的惩罚手段是罚值班、劳动,扣减食物,如果更严重的话,在“放茅烟”时,其他在押人可以押烟,但被惩罚者不允许抽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抽,听一些受到过惩罚的在押人讲,这种心情比死还难受。(“放烟茅”:值班狱警每天会提每个号的犯人出监室,抽一次烟,烟是由看守所提供的劣质香烟,主要用来缓解在押人的压力。这也视狱警的心情而定,如果狱警的心情,可能三、四天才 放一次茅烟)
我在里面关押了近九个月,但我所在的号没有发生过一次打架事件,仅有的一次还没有打起来,看守所是最容易引起打架斗殴的,其他号三天两头就会出打架事件。本来,狱警也是经常殴打在押人的,等到我所在的号的规矩立起来,并且得到有效的执行以后,狱警殴打在押人的现象都逐渐减少了。
至於说脏话,我会作个区分,平时的口头禅、口语,是不追究的,主要是针对那些有针对性的、带有侮辱性的恶意攻击、并有可能导致打架事件发生的谩骂行为,用来预防纠纷事件进一步升级。
在羁押十个月以后,因为警察确实找不到我“袭警”的证据,又不敢拿“艺术维权”的事情对我进行审判(那样的话,政治影响会更大),因此,我被“取保候审”,於2011年4月3日获得释放。
4月1日, 刚好是愚人节,“国保”专门来找我谈判,说“上面”有意要释放我,让我写一个“悔过书”,他们好交差。我本来就没有“袭警”,而且还是受害者,又遭到栽桩陷害被羁押了十个月,即使涉及到“艺术维权”的事情,也是政府强制拆迁不予赔偿,违法在先,哪里有错?“悔过书”又怎么写?因此,我拒绝了警察提出的要求。
于是,警察又退了一步,说让我写一个“保证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出去之后的头一个月不能呆在北京,这倒没有问题,我正好可以回老家探望一下父母, 他们都为我的安全担心;第二是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第三是不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两条其实都是有弹性的,因此,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份“保证书”,这样,才最终获得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看守所创作的作品最终是如何带出来的?
吴玉仁:我出狱的时候,是全裸着身体出看守所楼道的,我把衣服全部留在看守所,和刚进去时一样,连肛门都要检查,“国保”担心我从里面带东西出来,专门给我准备好了衣服,让我穿上,因此,我刚出来时,什么东西也不能带上。
但是,我事先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我让那些提前获得释放、政治上又不是太敏感、警察不会太在意的在押人,把我的一些东西提前带出看守所,交给我的太太。
还有,因为我和楼道的狱警关系不错,因此,我把自己的财物、在里面写的日记,以及创作的一些艺术作品,还有在里面买的一些书籍,都提前交给了那些可以放心的 狱警手里,等到我出狱以后,我再约他们出来吃饭,然后把东西交还给我。即便如此,我也只能陆陆续续要回来一些,有些他们认为敏感的、可能会给他们造成麻烦的东西,他们就不予退还,比如,我在里面写了两大本私人日记,他们就没有退还给我,还有,我在里面买的一些书籍,上面我作了笔记,写到一些批评共产党的句子,他们也没有退还,不过,大部份外界寄送给我的明信片,以及我在里面创作的一些艺术作品,短短几个月时间,我创作了几百幅画作,比如,一些人物肖像画、 监室内的场景画作、给在押人讲课制作的一些道具,他们都部分退还给我了,我曾经拿这些东西举办过个人的艺术展。相对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因为据我的了解,狱警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要冒风险的,他们如果大包小包地往看守所外带东西,会引起看守所武警的怀疑,而武警和狱警分属於不同的体系,因此, 他们每次只能偷偷地带一点东西出来,尽量不惹人关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监狱系统监控的严密程度,只是对於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视觉上的盲区。
现在,“国保”经常会找我喝茶,谈到当下的政治形势,他们总是空洞无物地说现在国家如何好。我对他们讲,我们都是成年人,你觉得你们能改变我的想法吗?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和眼光完全不一样,一句话,我们之间的区别在於对美的体验,在於我们双方的审美观念不同,这也导致了对政治判断的不同。我对他们讲:在艺术上我是个精英论,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我比你们警察更像马克思主义者,我总是强调工会、强调福利制度,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认为每个人在政治权利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除了机械地完成“上面”交办的工作任务,你们其实什么也不信。作为人、公民、艺术家,我必须不断地思考和追求事物的真相,就必须不断地反洗脑,当所有的谎言最终被戳破之后,就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在思想上的分歧,同时也让我们对你们所宣传的东西产生根本性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