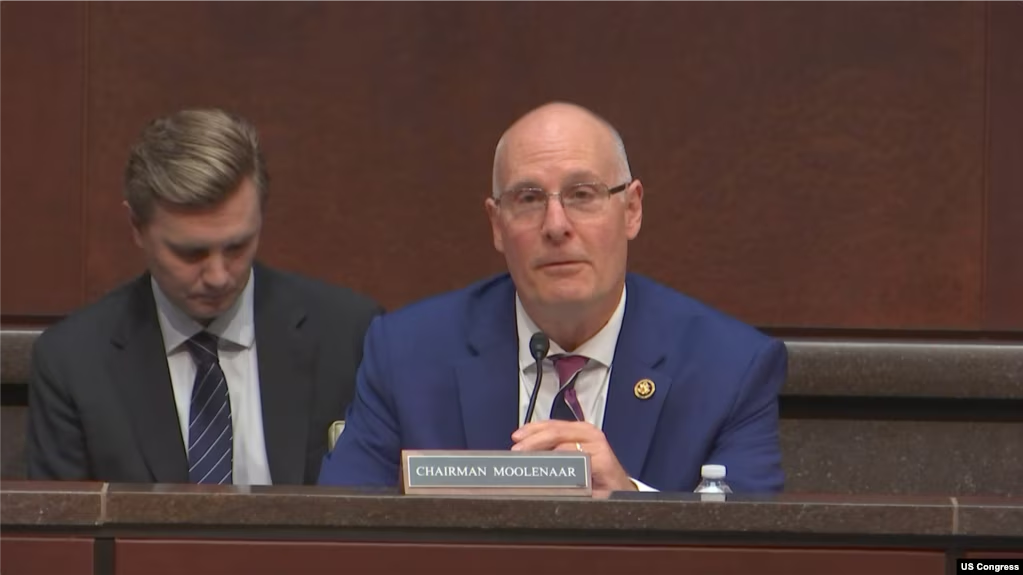纽约 — 纽约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锦霞,长期参与海外中国民运和关注香港前途的活动,是“纽约香港关注组”的创办人,被她朋友称为香港在北美地区的一个“桩脚”。近20年来,杨锦霞从不缺席香港七一抗议集会,今年她如期前往。在出发前几天,她在纽约长岛的寓所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以下是这次专访的实录。
问:听说你马上要回香港,今年香港的七一活动会有什么特点?
今年七一的另类打压
杨锦霞:当然是香港20年的回归。报纸上也说了民阵去申请(集会场地),但他们不给抗议场地,他们说因为要庆祝回归。所以实际上有一点打压,不是说一点,也是另类的打压。还有,在终点站他们通常会举行一个很小的仪式,已经走到终点了,他们也不给许可。所以,今年当然是比较紧张啦,一方面中共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你们有这么多人上街。
问:香港学生的本土意识越来越高,他们有的已经不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这对今年的七一抗议活动会有什么影响?
杨锦霞:我不能代表所有香港年轻人。是的,中文大学学生会代表在六四时说了,他们不参加了,但中大还有其他一些人参加,六四晚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所以做一个统计,没错,是有多一点的年轻人有所谓的独立的想法,但实际上很多年轻人也没有直接说我们香港要独立。并没有正式统计的数字。所以七一他们到底会不会上街?不晓得。
香港年轻人的困境
我觉得,年轻人在香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政治上、社会上,甚至对到底这个民主社会会怎么样,对他们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所谓走向本土,或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独立,有的说自决,我觉得自决是比较合理一点。香港人可以决定香港的命运,也不会说要独立。
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到底有没有声音在里面?现在,中联办常常介入香港的事情。以前,在英国人统治时也没有这样多介入所有的一切;还有人大释法,很多不同的事情,都令很多香港人,很多中年人,有这个困境。所以现在有更多人移民到加拿大或美国,有传媒做了特辑,回流到香港的,现在也要走了,为了小孩子。
因为讲到生活上,当然首先是房价,越来越疯狂,纽约曼哈顿可能是世界第一高,但纽约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住。但香港是个非常小的地方,现在公寓啊、房地产啊、公共房屋,都可以被炒、被推到很高的价钱。
普通的大学生生活,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根本没有办法出来独立,结婚、生小孩子。他们面临的就是这个困境。薪水追不上生活的指数。然后,每天一百多中国移民进来香港。应该是150个,从大陆移民到香港。这个已经是10几年来的事情。也不是不欢迎他们,但是地方就这么小,住屋就这么小。然后引起很多的事情,奶粉的事情啊、买金子啊,珠宝啊,什么都去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紧张,这种压迫力很大。
问:这跟全球化有关,也跟中国对香港的承诺有关,是否按照当年所说的50年不变,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你跟香港年轻人接触很多,那么香港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
港人要有自己的声音
杨锦霞:当然最基本的,基本法的一国两制,到底……我引用黄之锋最近常常说的,现在变成一国一又二分之一制,以后可能是一国一制。这个承诺本身以前是可以让香港人去处理香港的事情。可是,从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正英,每况愈下,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中联办要介入,这个情况人大要释法,我们有没有声音?甚至传媒也会被打压,这个不能出新闻,这个不能说,有很多记者自我约束,要不要写这个?老板会不会不高兴?到底这些老板后面有没有中方的背景?
香港年轻人希望自决

所以年轻人的想法是,有一些走在前面的年轻人,他们当然希望,至少希望是有自决,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就是说我们有声音。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才4、50岁,我们不要全部都是你们来控制我们,那个空间越来越狭窄,对于不同的政治方面、民主方面,社会方面,每个阶层上,教育,民生方面,奶粉、房价,还有大白象工程,很多事情政府用了几千万上去,搞所谓的建筑、搞一些公共的设施,但是最后很多地方,贫穷的人还是很多;一些老人家,在一些旧区,7、80岁老人家无依无靠,靠捡纸皮、卖东西,社会上很多不同的打压,他们的生活非常有压力。所以,年轻人当然希望香港有民主。
楊錦霞组织了2014年10月1日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集会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楊錦霞组织了2014年10月1日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集会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问:可是现在看一下整个国际环境,不要说香港,就是美国、英国,在政治经济层面上都无法抗拒这个崛起的政权,那么你认为香港怎么才能实现年轻人的希望,使情况有逆转呢?
雨伞运动——总要有人出来发声
杨锦霞:从两年多前的雨伞运动,你就能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个心,我不只是说那些学生领袖,有这么多人出来79天,出去了在那边占领了那么久,睡在街上,他们心里希望有这个反弹,希望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走出多一步。
没错,中国现在不是最大也是第二吧,但是总归要有一些人来说出我们要争取的事情,纵然就是那么一小撮,纵然就是一两个年轻人,就是要继续去做。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很多人也是坚持,为了那个国家的繁荣,还有民主,才会有那一天。所以在我本身是很支持那些年轻人的。就是说,我能够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帮助。
问:你的好朋友说你是民主派在美东地区的“桩脚”。你是个微生物学家,在大学教书,你是怎么变成一个活跃人士,为什么会对香港的前途和中国的民主化这么关心?
从微生物家到活跃人士——六四是一粒种子
实际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同龄人差不多。就是很简单的,那时候就是八九六四嘛。那时候,我20几岁,刚刚在美国念硕士班,刚好有机会回香港。我在美国南部读书,以前没有网络,所以当时回到香港我很感动,看到北京的学生和全国的学生,那时刚刚五月尾,事情刚刚发生,然后六四我也在香港参加,我人生的第一次游行啊,还有“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所以,我想那时候是我刚刚年轻的时候去感受到这个气氛,觉得我能为香港做什么,我那时候也没打算会留在美国,还在读硕士班,也不知道会做教授,人生的事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所以希望能够关心多一点。
其实八九以后我还是在(美国)南部,没办法帮助太多,做太多事情,但是后来到了纽约,读完博士,通讯比较发达,认识比较多的同路人,渐渐比较活跃,然后帮助很多不同的活动。总之来说是八九点起的一个火,一个种子啦。
当然八九以来20几年中,有高有低,后来的一波不止八九那一代,就变成维权,维权律师,需要的话我也会做。所谓“桩脚”就是有个点在纽约。如果香港有一些议员,不同的党派的人过来,希望这边的香港人了解多一点香港的事情,我就帮忙联系。
低潮时很多人会离开了,不再关心了,这个也会发生在纽约。很多人都移民了,变成美国人了,他们会觉得,关心一下就好了,也不会再去做了。但总归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啊。
问:香港的雨伞运动对你冲击很大,为此,你成立了纽约的香港关注组,英文叫“NY4HK”。
成立“纽约香港关注组”
杨锦霞,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雨伞运动刚发生时,我刚刚那个学期是放假做研究,我也知道占中的事情,因为我那个暑假回去香港,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纽约这边一定要出一份力,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准备了一些丝带啊,叫我小孩子帮忙,就是“一个人团队”啦,觉得能够做的就做了嘛!
很感动的是有一个全球团结组织(Global Solidarity),一些义工串联着每一个地方,不止美国,还有加拿大,还有欧洲啊,澳洲啊,消息传得很快,通过互联网和脸书。在纽约也是这样,我很惊讶,第一次在时代广场做的一个活动,就来了很多人,我们也没有申请,就靠一些民运人士来帮我,连麦克风都没有,后来有很多人来找我,通常都是年轻人,他们说,有什么可帮你的,我都来不及回应。有些你会觉得他们一定是很关心政治的。你错了,他们坦白说,嘿,安娜,我不太了解政治的。有的是在这边长大的,有些是刚来美国的,有的是从宾州、华盛顿来的。我很感动。
我一直是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组织。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以前的所谓的“美港联”也差不多都瓦解了,因为都没有开会什么的。我都不太愿意重新再去组织一个正式的组织,因为现在世代的年轻人不需要捆绑在某一个麾下,这个不太适合。
我就一直想说,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松散的组织,你们有个脸书,用一个资讯的方式,或是有些香港的议员,或者是学生领袖过来,我们就聚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没有会员制的,这个方面也吸引到很多不同的年轻人、学生,还有专业人士。
他们都到10月1日最大的时代广场的集会。我有美术设计师,帮我设计海报,我有人帮我去印刷东西,我有人帮我去弄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他们做的事情。有个小孩说,我们叫什么名字?就叫纽约支持香港,这就好了。当然从5、60个很积极的,现在变成只有十几、二十个人,但我们感情都很好,也会常常聚在一起。
问:今年是六四28周年,我在采访六四活动时总能看到你,也采访过你多次。28年来,连大陆来的很多民运人士现在都不出来了,你还是一直参与。除了你对中国民主和香港前途的关心,我看见你墙上的十字架,是不是也有一种宗教情怀在里面?
我人生中有“三信”
杨锦霞:我在人生中相信三个东西,我是天主教徒,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科学,因为我算是做科学的,虽然我科学没有做得很出色;第三样,不是最小的一样,这三样都一样重要,就是民主。这是我相信的东西。
我在香港长大,我也得到了某一方面的自由。长大以后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这让我想到,民主是很重要的基本支柱,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有民主,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可能会减低一点。
也不是在民主国家所有的事情都是公义的,但至少在法律上,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你被指控,警察抓你,你在被证明之前还是无罪的,这就是法治。香港也有法治,但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大释法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警察打人,7个警察已经坐牢了,很多这些不同的事情都是要靠发出这些声音去逼迫他们,所以必须关注这些事情。司法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人大介入,去解释法律,就冲击了法律的底线。
我相信上帝、科学和民主,这个相信很重要。如果我不相信民主,我每年就不会再去了。去参加是个悼念的活动,心中有团火,支持民主的理念,从八九,到维权律师,到雨伞运动,这些都是要关心的。
问:所以你会把对香港前途的争取跟对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支持,相互联系在一起?
杨锦霞:对。我说对,不是一个字可以解决的。我们香港小孩子说,“大中华左胶”,胶是荒谬的意思,是方言。 他们觉得以前八九那一代,是希望香港有民主中国就有民主,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对中国仍有感情
现在慢慢的年轻人觉得,我只关心香港,我只要香港好,跟你们大陆分割。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要跟你们分割。我还是对中国有感情的,我还是觉得香港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中国垮掉对香港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的。就是说这个小地方,我不觉得自己好就可以了,因为世界很小,每个地方已成一体了,都变成地球村了。我了解他们,我会赞成他们的一些想法,但不会百分百赞成,不赞成香港独立。
问:你对今年的七一有什么期待?
杨锦霞:希望多一点香港人继续出来,把声音带出来,走出来,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好像去运动一样。但是心里面要记住,我觉得,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就是继续要支持、继续努力,不能说我不搞政治的,我是个普通的人,要关心,在适当时侯你就是一个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