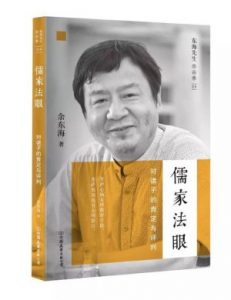
有厅友转发了孟晓路两段话,不无见识,不少问题,分别予以批判。第一段话说:
“清朝之后民国到现在,经学就演变到一个新阶段即现代经学。现代经学就是用西方的理论去理解去诠释经学,这就是反向格义以西解中的西化经学。在这个阶段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就是中化经学跟西化经学的对立。中化经学就包括前三个阶段,汉唐外王经学、宋明内圣化经学以及清朝小学化经学,这都是中化经学。中化经学跟西化经学对立,经学就更加分裂了,经学的本来面目就更加地被掩盖了。这种西化经学,已经彻底丧失了中学的宗旨,走向了经学之反面。我们说古文学以陈迹代立法、宋学以内圣代外王、小学化经学以文字代实践,皆愈来愈偏离经学之真;然无论如何,这都是在中学自身内的逻辑展开,其世界观立场毋庸置疑仍是儒教的中国的世界观。那么西化经学,已经脱出了中学之轨道,其世界观立场完全皈依了科学教西方的世界观。西化经学用异己的反华夏立场的解释系统去解释经文,已经彻底把经学消灭掉了。所以到现代经学这一阶段,经学就消亡了。”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
其一、如果说,以西解中的西化经学,是指以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诠释经学,至今不存在西化经学。真正的西化经学或难免肤浅化,但绝不会彻底丧失中学宗旨而走向经学反面。
五四以来盛行的是以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立场观点批判、反对经学。注意,平等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反儒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国际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马列主义是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统一。
它们与经学的文化政治立场和基本观念相悖相反,对于经学都持反对批判乃至诬蔑之态度,焉能谓之西化经学?西学与北学(马学)之别,是人本与物本之别,正邪之别,不可不辨。
唯从習时代开始,马家对儒学有一定认同,勉强可称马化经学。
其二、说“汉唐外王经学、宋明内圣化经学以及清朝小学化经学,这都是中化经学”云,这个论断未免简单化。汉唐经学侧重于外王,明经学侧重于内圣,清经学侧重于小学,侧重程度较高,称之为外王经学、内圣化经学和小学化经学,勉强尚可,称宋经学为内圣经学,则期期以为不可。孔子之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经学最得孔学之正。虽于内圣有所侧重,那是时代的要求,佛道过旺的时代环境使然,并非程朱于外王有所不明或轻视也。
孟晓路第二段话说:
“宋朝经学复兴,然为与长于形上学明心见性之佛老争能,亦将经学偏向个体形上心性发挥,从而偏离汉唐经学以外王为框架之大路,走入个体化心性化内圣化之小径。所以到了宋朝,经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经本的组织、解经方式以及内圣外王的关系上,汉宋都有很大不同。宋学经本系统发生了极大变化。为了将儒学内圣化,先将心性儒学要典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与同属心性派之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专向个人心性修养发挥,构建心性化四书学体系,并以四书学诠释五经,将五经四书化,从而整个经学都心性化内圣化了。在宋人这个四书五经之经本系统里,四书表面上是五经的绪论和预科,但在实际上四书的地位已在五经之上,宋学重心实在四书,五经反为可有可无之陪衬。”
上述话语问题很多,概言有三。
其一、宋儒高张内圣学,并非为了与佛老争能,或者说,与佛老争能并非根本目的。在佛道两家的冲击之下,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无数英才,皆归两家。宋儒“将经学偏向个体形上心性发挥”,是为了努力抵消两家消极影响,尽快培养儒家人才,以更好地保卫大宋保家卫国。注意,程朱心性学虽是外受佛道刺激,并未吸收两家理义。程朱的心性学是纯正的内圣学,是返回孔孟之本而开出来的,是将孔孟内圣学进一步精细化系统化。
其二、以外王为大路、内圣为小径之说严重错误。外王固然是大路,内圣更大,更加根本。外王扎根内圣,内圣开出外王。内圣外王并非并列关系,更加不能颠倒,大外王而小内圣。
其三、称四书为“专向个人心性修养发挥”心性儒学要典,偏见也。五经各有侧重,书礼春秋侧重外王,诗易乐侧重内圣。但这种侧重并不大,四书之侧重就更加轻微化,内外两学几乎已经平分秋色,既是心性要典,也是政治要典。
另外,去年8月,也有微友转发孟晓路一段话,我也有过简单批判,一并录此共赏。孟晓路说:
“天下诸教实可分为经教、子教与器教,儒教是经教,佛、道、耶、回是子教,科学教是器教。经教是一统,子器是多元。故唯经教可统摄诸教,诸子器不可当此也。经教政教一体,为在朝之王官学,负有全面建构文明之责任,子教唯是教,为在野之百家学,生存于经教文明之养育中,不参与政治经济制度之建设与运转,唯在教的方面作为经教之补充。”
东海曰:分类不错,唯子学有正邪之别,宗教有中西之分。在王道礼制之下,邪学邪教和西方宗教可以享有言论信仰自由,但不配为“经教之补充”。对于它们,儒家有引经据典进行驱迷辟邪的责任。
2021-8-22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