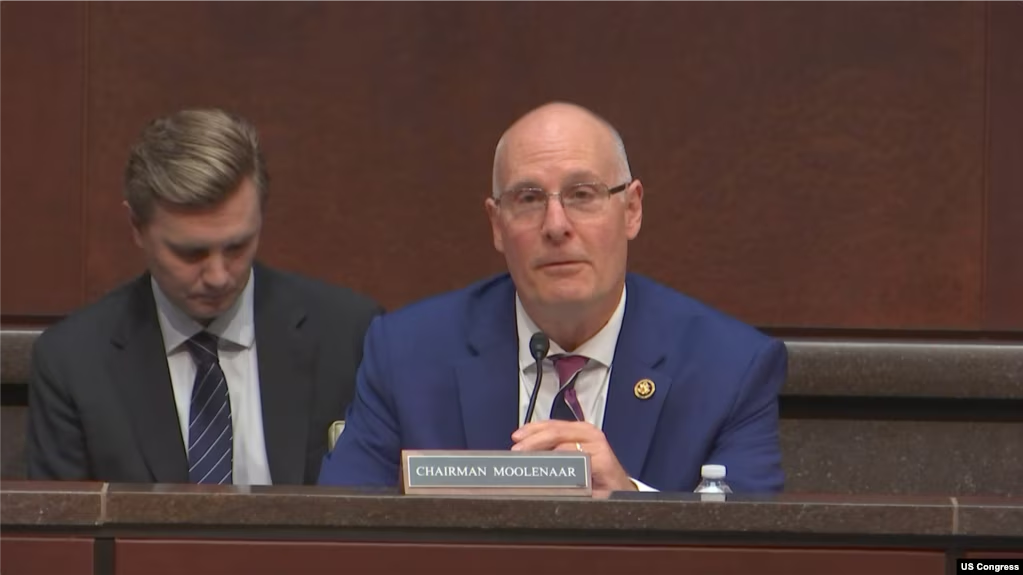对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关注的人,可能知道有两个同龄的青年经济学者:王小强、王小鲁。他们都是赵紫阳属下陈一谘领导的“体改所”成员、两个文才出众的笔杆子。他们命运也有相同之处:都在八九学运前夕出国留学,逃脱了六四之灾。后来也先后回国重操旧业。王小强扎根在香港,王小鲁则被樊钢邀请回到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五十九岁。
王小鲁对灰色收入的再次调查
王小鲁最为人推重的研究,是中国的“灰色收入”问题。新近发表的一份有关《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透露中国社会有高达九点二六万亿的巨额隐性收入,其额度竟已占了中国GDP的百分之三十!令社会震惊。报告以大量数据及事实作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论证,揭露中共专制下官场种种黑暗面。
这是王小鲁继二○○七年发表《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报告后,又一新成就。中国的灰色收入问题由来已久,并且盘根错节,为害极深。但是如此巨大的漏洞,在中共各种统计年鉴中,从来找不到任何相关的统计数字。
二○○一年,经济学家胡鞍钢曾向媒体披露,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与财政支出流失、黑色经济收入、垄断行业租金合计约为一万亿元左右。这些资源相当部分流入个人手中,成为灰色收入。
二○○二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根据统计局发布的二○○二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七百五十二元,推算出城市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一点五万亿元。二○○二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十万亿社会财富中,发现“一点三万亿不知归属”。十多年来,由一万亿、一点五万亿、二万亿,灰色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并不断的得到验证。
王小鲁带领的课题组,对二○○五年中国居民收入进行了调查,二○○七年他们发布的结果引起世人震惊:二○○五年匡算的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应当是十三点五万亿元,而按统计推算只有八点七万亿,前者比后者多出四点八万亿元。这些“隐藏的收入”绝大部分都来自高收入阶层,大部分应当属于灰色收入。
揭开中国豪客到处摆阔之谜
王小鲁发现,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百分之十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三十一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九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百分之十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五十五倍,而不是按统计资料推算的二十一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准。
王小鲁最新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从二○○五年到二○○八年的三年间,游离于统计资料之外的隐性收入,用甩开GDP增速近二十个百分点的速度一路飞奔,膨胀了百分之九十一,其中,百分之二十位于收入金字塔上层的人们拿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此一数字在中国老百姓中引来的哄动与不满是巨大的。
就在许多工薪阶层抱怨收入一直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之时,调查显示超过两成的职工五年来没有涨过工资。此外,不少农民工及城市贫民面有饥色,住无安定,却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另一面:楼市持续火爆,“房价收入比”一直在反常的十倍以上;海量的个人资金涌入股市,大笔个人存款涌入国外银行,以至流失海外的巨额赌资都在数百亿之上;全球唯一的七星级酒店(杜拜帆船酒店),最低每晚消费二千美金,六成客人都是中国人。澳门赌场,中国的暴富者(不少是公款赌博的干部)一赌千金面不改容,流失海外的巨额赌资在数百亿之上…这不是中国人有钱,也不是中国政府有钱,而是贪官污吏掠夺的民脂民膏!
然而,今年北京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却出现“规范灰色收入”提法,反映了中共高层的心中,根本没有把灰色收入界定为非法收入范畴,更从来没有打算以法律手段来杜绝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敛财方式与犯罪行为。在一些代表的非议下,虽在字义上改以“非法收入”称之,可是如何从制度上防止这种法收入的蔓延恶化,却无一字交代。
官员非法收来源无孔不入
灰色收入的来源,王小鲁分析指出:
第一,财政资金存在严重管理漏洞。通过“条条”管道分配到各地的数千亿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投资专案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有些专案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二○○三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的额外付费,相当于贷款额的百分之九。二○○六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二十二万亿元,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业者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一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藉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世界银行二○○六年进行的中国一百二十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代名词)。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最低百分之零点七,最高百分之二点三。如果以百分之五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准,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二○○六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五十五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五千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帐、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二○○五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十六点三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且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四到五倍,差价每公顷五百多万元。除去其中零点五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外,其余十点一万公顷土地少收五千四百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
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十万元,合计二千零八十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大多数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并严重缺乏监督。
第五,垄断行业收入。二○○五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八百三十三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八,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达一万亿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以上内容中有数据的项目,数额已接近三万亿元,占了四点四万亿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落马贪官披露灰色收入黑幕
中国社会如今是权力越大,灰色收入的途径也就越多。中共党员及身居要职的各级领导,很多都在外挂名兼职收取高薪高佣,具过百以上虚职衔者大不乏人;再加上专案审批和职称评定的灰色收入,不少官员连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如鞍钢的原料主管,其海外的灰色收入就直接进入自己子女的海外帐户,所以查起来相当困难。据说,十年间国企在海外流失的资产达九千亿人民币。
贪官一旦被查,往往会出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甚至超出认定贪污受贿的数额。原合肥市委副书记许道明、原合肥市商务局局长江黎夫妻俩,二○○八年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审期间,曾大曝官场“潜规则”。许道明说:“不算购物卡,光是计划生育奖励,每年有三四千元,外贸每年几千元,可发不可讲的,每年少说也有几千元。逢年过节每个部门都能给千儿八百的。”江黎也透露“各种收入特别多”:一个是大家都有的,但不在统计表上显示;还有单位内部创收奖,以工会、机关党支部名义发的钱,一概都不算,工资条上也不显示,到香港参加徽商大会,四天时间发了三千港币。江黎特别说明,一些活动发的钱非常多,但“都是奖励一把手,不让别人知道”。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受贿五百一十七万元,另有四百八十万元无法交代来源,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萧作新更是创下了一千二百万元不明财产的天文数字。而现行《刑法》对属于灰色收入的“不明来源财产”最高刑期为五年。虽然界定了不明财产的内容,《刑法》却没有对“不明财产来源罪”划定具体的量刑标准,使一些贪官钻法律空隙,降低了犯罪成本。
今年二月,震动全国的文强案进入最后的审判阶段,文强对于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出异议,“灰色收入部分认定太少”。公诉方称他在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十多年时间里,红包收入只有二点四万元。文强说,“远不止这些”,全局几十个下属单位送的礼金一年就有四、五十万元,几年下来也不少。
文强强调自己“灰色收入”被算少,与朱胜文、许道明江黎夫妇大曝灰色收入很多的说法异曲同工,均期望通过钻法律的“空隙”,最大程度减轻自身责任--法律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灰色收入意味着并不违法。
可以想像,当“灰色收入”这个钱袋能够装起越多的贪腐财产,违法者就越容易消减自己所应承担的罪责。事实上,这已成为近年来不少腐败官员普遍采用的一种腐败招数和套路。广东韶关市“业绩”工程背后暗藏的正是一系列精心设计、极尽“灰色”化的腐败手法--如替人“办事”并不马上受贿,而是逢年过节收“礼物”,通过“时空转换”淡化贪腐痕迹;再如遵行所谓“不主动索要钱财”等权钱交易原则。这些“变形”的“灰色收入”使得叶树养最终也拥有高达千万元的来源不明的财产。
中共的灰色收入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还侈谈什么公平公义,侈谈什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吹嘘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什么“顺应各族人民过上好生活新期待”,就算真能涨点工资,搞点关乎民生的门面工程也不会有实质意义,因为党官共干们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及改变利欲薰心的贪婪本性,要他们抑制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清廉勤恳致力于“为人民服务”,无异是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