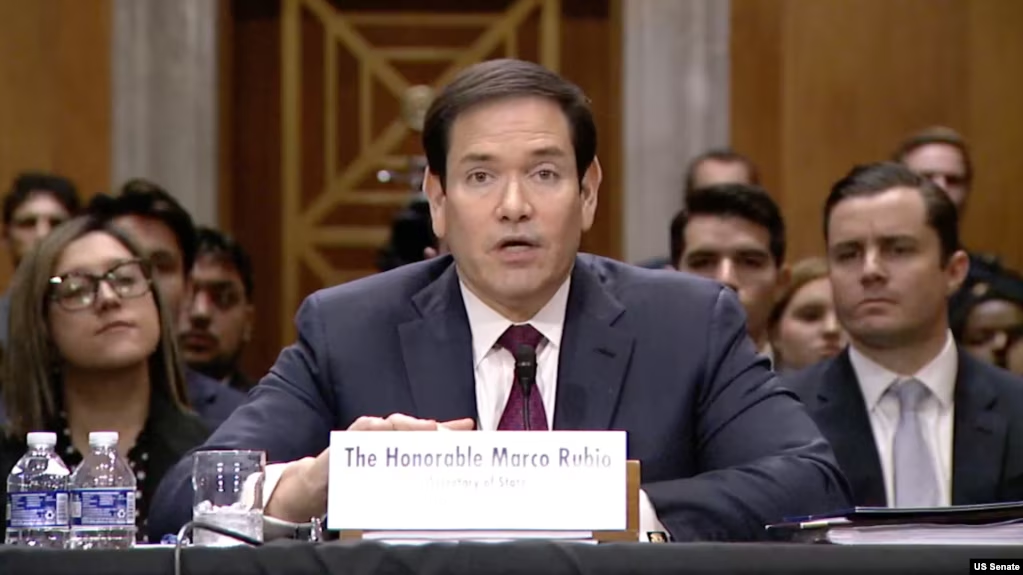在诺贝尔和平奖宣布颁授给刘晓波之后,笔者曾一再表示诺奖的刺激,说不定对中国政改带来微茫的希望。这种看法,有人指为「太乐观」了。
近日,收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谈话稿。原稿有几万字。吴在86至87年间,曾参与赵紫阳组织的关于中共政治改革计划的研究,并且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份的起草人之一。在这个谈话稿中,他相当细致地分析和评估中共政改的前景,而结论是:中共体制内向民主转型的「希望很渺茫」。
吴教授觉得政改希望渺茫的原因,是因为自1989年以来,中国整个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文革后,中国社会中的精英和大众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改革。但89年后,这个共识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稳定,大众要的仍是政治改革。现在凡是和现体制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甚么大改变,按现在的制度搞下去就行了。但大众却感到现况非常差,难以容忍。这种共识破裂状况在20年里不断深化。体制内转型就是精英推动的转型,「很难想象体制内的精英还愿意从内部再去推动变革。」
第二个变化是贫富分化越来越大。若政治向民主转型,现有的贫富分化就要被政治变革所改变。民主是制约贫富分化的制度。尽管民主制度下也有贫富分化,但富人影响力是金钱,而穷人的影响力就是选票。相对来说,穷人总是多数。民主是穷人可以用选票来制约富人金钱力量的制度。因此,当专权政治处于贫富分化非常大的情况下,民主化就难以推行,因为民主化会使富人失去许多东西。尤其是中国今天的富人,大多数并非自己创业致富,而是依靠当官的特权致富的。掌权者本身就属富有阶层,一个小小科长就可能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源控制在手里。20年的经济转型,使国有资源基本上已私有化,而私有财产是子女可以继承的东西。在1989年以前,掌权的人不像现在那么富有,权力也不一定能由子女继承。民主化要把现掌权者的财产搞掉,谁会跟自己的利益过不去?
另一个变化是,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权力网的纠结关系。比如说「我爸是李刚」,一个小小的李刚,副科级干部,有中宣部维护,有河北省维护,整个政权基本上都维护他。这就是说,从中南海,至少到市县,已织成一个严密的关系网。上下级的手脚都互相牵制住。
吴教授认为,温家宝8月份以来,多次提到政治改革,一是内容空洞,二是高调,三是没有实质内容。他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实际上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说的。但怎么改?改甚么?他没有讲。温家宝在美国说,民主就是让一切人自由发展。这个调子非常高,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民主没有出现过。西方民主也不是一切人都可以自由发展的。民主不是万能,它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是定期由人民普及而平等地竞争性地选举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只唱高调,不讲民主的最低要求。
如果温家宝真要推动民主转型,他至少可以把赵紫阳十三大报告中的政改内容再讲一次,比如党政分开、差额选举,「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党领导只是政治领导,不包括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是这些实质内容,也是政改的最低标准。23年来,中国政治不仅停滞,而且倒退,因此这种最低标准仍有重提的意义。温家宝只空言政改却无具体内容。
吴教授认为,刘晓波得和平奖,象征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二、三十年所走道路的不满在增加,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认识到,通过经济介入促使中国政制改变的可能性很小了,于是开始增加外部压力。估计在未来5到10年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也许会使中国增加颜色革命的机率。
100多年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形容一些政治人物「灵魂充满了卑鄙,口袋充满了赃物,嘴巴充满了谎言」。100多年后,这样的人物,又在中国重现了。除了危机迫使他们释放权力之外,怎能期盼他们会自动作民主转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