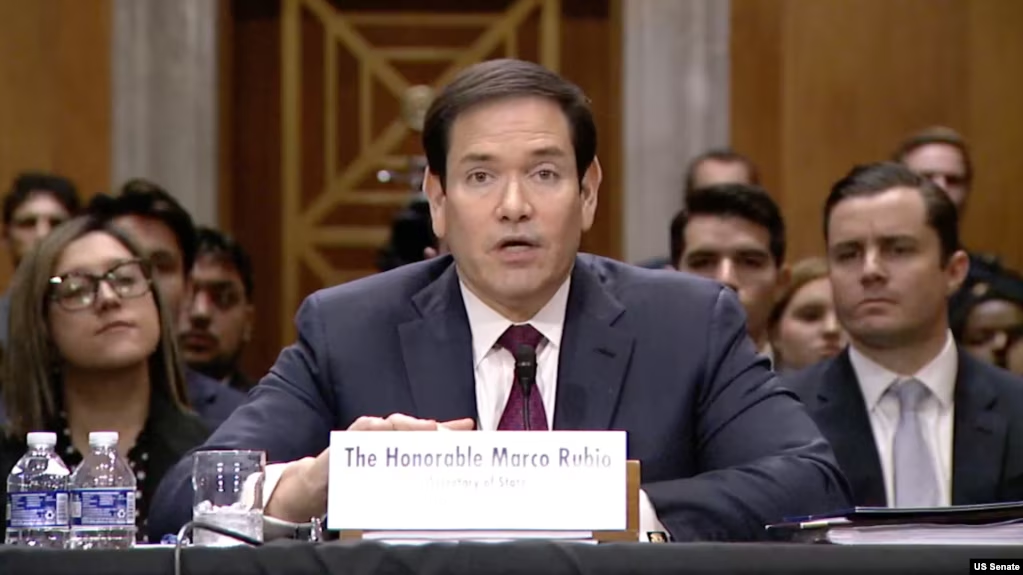早在“六四”血腥未散之日,我就确立了必须实行全民和解的坚定信念,并不顾当局“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和民众强烈盼望复仇的愤懑,于1993年在《和平宪章》中系统表述了这一理念,提出了如下战略主张:“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经济起飞带来的巨大利益造成的分配不公,社会沸腾,当局也完成了革命——王朝的循环,在意识形态上从奉行“斗争哲学”到转向鼓吹“和谐哲学”,这里虽有进步因素,但仍存在根本问题:难道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最高追求乃至唯一追求吗?
人类社会当然以和谐为好,但和谐并非是最高价值,更非唯一价值。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可正义也不是唯一价值,包括和谐在内,其它价值也是需要的。光讲和谐,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为“美好理想”,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利益、升斗小民的生存需要就不可避免地被“和谐”了。只有以正义为基础,和谐才是社会可普遍接受的。
和谐只表示一种社会次序,仅此而已,古今中外任何统治者对它都乐于接受,帝制中国的历代“天子”不说了,德国、日本法西斯和已经作古的苏联莫不如此,为达成目的,它们可以杀人如麻。在它们统治之下,为了“和谐”几时不是文字狱盛行、思想犯成堆、少数民族遭迫害、下层民众被任意剥削压迫。也就是说,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结果只能牺牲思想自由和大众合理利益。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殊死反抗是必然的,太平盛世走向末日也是必然的。故曰“焚坑能久治,秦政应至今”。
只有正义成为最高价值,使每一个人公正地得其所应得——准确地说“随时随地争取得其所应得”,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因为这种情况下,和谐虽不是最高价值,却是良好的结果,它不是社会的终极追求,却因为社会矛盾不会压抑到爆炸性状态而导致大动荡,从而能确保长治久安。换言之,正义至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平博弈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其虽不可能呈现静态的和谐状态,但却可以获得持久的动态平衡;它会有无穷的社会麻烦,却不会有根本性问题。因为正义至上首先要求制度正义,而正义的制度是不可推翻的,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而会受到大多数人的维护。
那么,今日中国要从强求和谐走向追求正义要经过什么阶段?首先,民众为了不至于被‘和谐’,必然要求有说话有表达意见及要求的自由,并将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这在荷兰是早在1581年就做到了的事情,法律的这种规定则叫做权利。权利是什么?权利不是支配他人的,是用来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确保公平正义的最低保障线,权利至上也就是实现生活正义的前提。须知,人类社会越先进发达,利益博弈就越复杂,每个人就越需要随时随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理利益,如同价值只能在自由市场中实现,正义从宏观上说也只能在争取权利并运用权利中实现。没有权利至上,正义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进一步说,有了权利,正义也不可能100%实现,但权利毕竟是实现正义的最好工具。正义作为人类的最高追求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今日中国当局权力至上,广大民众为了实现正义则必然要求权利至上,为此中国社会已处于严重的分裂状况,近年来的一系列中小城市暴乱就是典型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越坚持高压,民众的愤怒就越不可遏制,社会离和谐就越远,自然离正义也越远。正因此,我在90年代初于《和平宪章》之中就提出了“全民和解,权利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原则,现在看来,中国已没法不走这一条路,或者说这是中国下段历史不可逃避的定数。当局暴力维稳不可持续,而少数民众暴力革命的愿望也一无群众基础,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无能为力。相反,人权入宪表明当局在意识形态上已向普世价值投降,民众争取权利的斗争则日渐高涨,这样官民之间也就出现了在权利基础上实现和解的现实可能性。权利是法律概念,只有立法加以保障才有可能普遍实现,使保障权利的法律具有至上性,正是官民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要把希望寄托在当局开皇恩大赐上,只有发动全民来争取才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其实梁启超早在近百年前就精辟地指出过,只有虽断续却持续的国民运动才是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可喜的是,坟墓活埋12年的鄙人重返人世后发现今日中国民众已经普遍认识到权利至上的价值意义,全社会的公民意识都在觉醒,维权运动已成不可阻挡之态。这表明:中国已离全民和解不远,良性互动有望开始,和平转型的历史阶段正在到来!
2010.12.21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