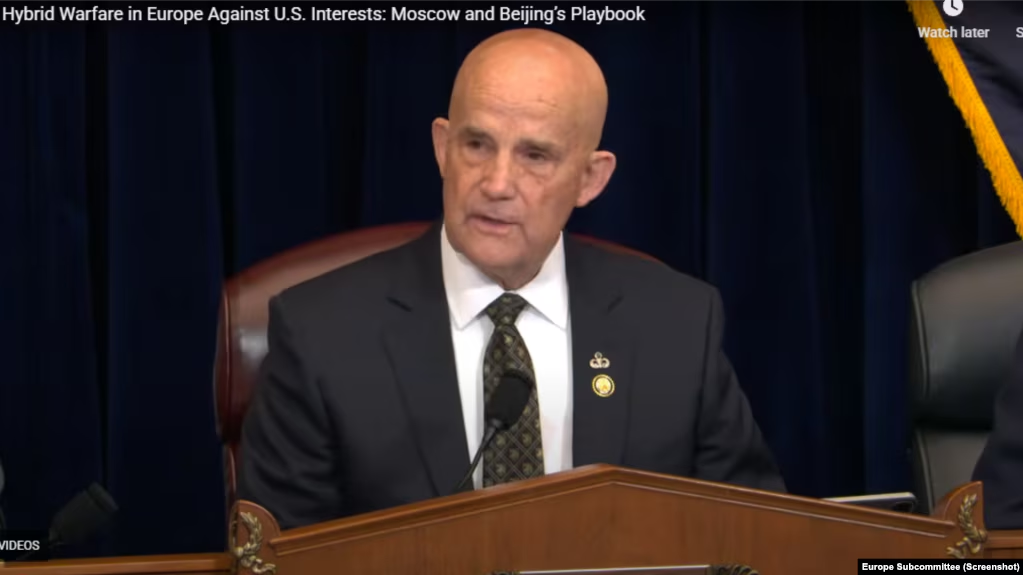1980年前后常常读到一些忏悔文字,某些良知苏醒的人们对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痛心疾首。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随权力的节拍起舞,直接间接作过帮凶,或者曾经落井下石。对这些忏悔,虽然不大愿意接受——心里总会反问:你当年的良心去哪了呢?不过,即使谴责,对这些当事人多多少少还是心存谅解,因为在政治高压的特定时空环境里,在阶级斗争中被强迫站队,不“跟党走”就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任何人都难保不在这种状态下被动做出某些蠢举。当时情非得已,事后能忏悔,也还算是良心没有被狗吃光。从长远公共福利的角度看,这些人的忏悔对防止后来人再犯类似错误不无价值。读过这些忏悔录,心底下不自觉有了个乐观的预期,以为这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智识阶层,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对政治权力会多些警惕,少些奴性,起码在面对政治迫害时,会变得审慎一些,至少会设法远离政治迫害的臭水潭。哪里知道,我的这种乐观在现实面前显得竟是那么幼稚,对权势摇尾巴的那种奴性在某些人身上是深入骨髓的,并不一定非得需要政治高压才会表露出来,即使在没有政治压力的情形下,也会主动向权势献媚。
无论以年龄还是以职责而论,退了休的高铭暄先生都没有再随权力节拍起舞的必要,什么不做,也没谁能把他咋样;继续其溜须拍马的事业,既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弄不好还会溅一身污水。对国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迫害人权案件,高铭暄先生没有江平、张思之、贺卫方们的道德良知,也就算了,保持沉默袖手旁观并不难,只要高铭暄先生不再继续参与迫害人权,公众也就没有功夫去拷问一具“冢中枯骨”的良心。然而,已经退了休的高铭暄居然竟然突破底线,不仅干起落井下石的下流勾当,在遭到当局重判11年的刘晓波先生伤口上撒盐!说什么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是应该的,而且,他还危害到每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当迫害人权被“正读”,不仅不受批判,反而受到鼓励,我们每一个公民就随时可能陷入“文字狱”。
2010年10月25日,官方媒体发表了《所谓“因言获罪”是对刘晓波案判决的误读——刑法学专家谈刘晓波案与言论自由》。高铭暄以所谓的“刑法学泰斗”的身份,给迫害人权的官权帮忙,从所谓的刑法学角度,断言刘晓波遭受11年重刑是应该的!在刘晓波将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夕,高铭暄作为刘晓波的同胞,不仅不为之高兴,加以祝贺,反而跳出来卖弄他那些“刑法学识”,意图十分明显,是要搅黄这桩好事。如果说高铭暄先生在法理学上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我们无话可说。但是,高铭暄先生的一番“宏论”,实际上是谬论!而且是包藏机心的谬论!
首先,高铭暄有意识地偷换概念,隐瞒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高铭暄列举欧美国家处罚煽动暴力的案例,以此类推共产党处罚刘晓波的非暴力主张为正当,这是有意混淆暴力与非暴力的界限。在引征西方国家的法律时,高铭暄只谈西方国家也有煽动颠覆这个罪名,却不谈西方的这种刑罚只惩罚那些煽动以暴力方式颠覆政权的言论。众所周知,高铭暄引征的美、英、德、意诸国,都是实行自由选举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像刘晓波那样煽动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政府”根本就不是罪行,而是权利,是在为公共利益作贡献。在欧美国家,批判政府,批判执政党,不论言辞多么激烈,只要目的是主张以和平的自由选举更换政府,就完全属于言论自由,与罪恶不搭界!如果刘晓波像共产党当年那样,煽动以暴力革命的方式颠覆政府,我想,是不会有哪个欧美国家指责共产党迫害人权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也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他。
人们之所以尊敬刘晓波,同情刘晓波,声援刘晓波,重奖刘晓波,谴责囚禁刘晓波,正是冲着他的善良,冲着他的和平主张。但是,对这至关重要的一点,高铭暄只字不提。主张暴力还是非暴力,是保留有煽动罪的欧美国家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暴力是欧美国家构成煽动罪的要件。一辈子靠卖弄刑法学“知道”混饭吃的高铭暄对此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就是他的“知道”有所不足,靠以“知道分子”的身份给官权背书混上刑法学专家头把交椅的高铭暄就更被证明是伪专家。如果是知道而有意不说,则是诚信存在问题,是道德和人格存在缺损,就不仅是伪专家,而且是做为人都不及格。高铭暄“研究”刑法学不是一天两天,能列举出那么多国家煽动颠覆罪的掌故,据此判断,他知道而不说的成分应该占据主导,这就是在有意欺骗舆论!欺骗国人!
其次,高铭暄还有意隐瞒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行为犯”与“结果犯”的不同。欧美国家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经历过漫长的进化史,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里,仅仅言论或学术观点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就可能被判死罪,如著名的布鲁诺被火刑烧死——高铭暄先生为什么不引这个案例来证明今天当局迫害人权很“进步”?在欧美,公民权利与公权力在保障言论自由与维护政权安全问题上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博弈过程,最后才形成今天蕴涵于《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公民权利优先于公权力的人权原则。历史上,英美国家确实存在过惩罚颠覆性言论的一页,然而,这些国家最后都没有把对言论自由的迫害带入当代。我们有什么必要重复人权在这些国家的曲折经历?难道因为俄国曾经有过歧视农奴的制度,就能证明共产党搞的歧视农民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合理的吗?难道因为欧美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血汗工厂,今天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某些红帽子资本家剥削压迫农民工的“打白条”行为就正当吗?难道因为英国曾经发生过圈地运动,就能证明今天的剥夺农民土地、暴力拆迁都是正当必要的吗?
就历史言历史,欧美国家保障言论自由的传统与惩罚颠覆性言论的传统博弈的结果,无一不是言论自由夺得了最后的胜利,高铭暄先生为什么闭口不提呢?英美等国已经有百余年没有过惩罚煽动罪的判例,为什么也闭口不提呢?在判例法国家,没有判例也就等于没有这个法律,法典上的煽动罪条款只表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个东西(这点高铭暄等可能难以理解,因为这些人习惯于看到历史被反复涂改,没有涂改掉在他们眼中就是没有作废)。“即刻危险规则”,也就是高铭暄的“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是在保障言论自由与维护政权安全两者博弈过程中的产物。这条规则是法律实务工作者在研究过许多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例后得出的结论,可以理解为刑法学领域的科学成果,提出来后很快就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被国际刑法学界确认为言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分界点,并通过“约翰内斯堡原则”被确认为国际惯例。按照这个国际惯例,煽动颠覆政权罪的构成要件,必须是存在迫在眉睫的暴力,必须要有看得见的即刻就会发生的危险。只有煽动性言论根本不足以定罪处罚。即刻要发生的危害结果是这个罪成立的要件。也就是说,这个罪名属于“结果犯”,而非“行为犯”。但是,中国大陆立法、司法机构和以高铭暄领衔的所谓刑法学界,在决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代替原来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却无视国际惯例,以中国特色之名,行反刑法科学之实,明里废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暗地里却保留了隐藏在“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背后的以“行为犯”对公民言论论罪的法律解释,以“行为犯”而非“结果犯”解释和适用刑法105条第二款。这是以野蛮的潜规则代替文明的国际通行规则。
正是在以“结果犯”,还是以“行为犯”来解释和适用煽动颠覆罪这个关节点上,以高铭暄为首的所谓大陆刑法学界违背了法律学人应有的良知,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偷偷地迎合邓小平们维护其特权地位永远安全的需要。高铭暄避而不谈的是,大陆现行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以“行为犯”解释和适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明文规定。以“行为犯”适法,只是潜规则,是违反国际惯例,并进而是违反刑法科学的。正因为违反国际法才使公民受难国家蒙羞。高铭暄对刘晓波有罪的论断,是以“行为犯”解释和适用煽动颠覆罪这条潜规则为前提的。如果按照“结果犯”来解读刘晓波的所谓犯罪证据,根本就不足以定罪。高铭暄如此深藏机心,偷梁换柱,媚合权势,就难怪要被“喉舌”们捧为所谓的刑法学泰斗了。但是,这种以给权势谋划如何剥夺民权为业的“泰斗”,实质上不过是泰斗级的奴才罢了。
再次,高铭暄以相对主义暗中悬置宪法原则,模糊正义与不义的界限。高铭暄得出的两个结论:“一是言论自由是一种可以根据危害结果来衡量的可以限制的权利;二是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否之标准,是根据在一定环境下的言论给现实秩序造成的危险的性质和程度来确定的。”其内核是相对主义。按照这种方法论,公民言论自由权成了相对的,不再具有对公权力的优先地位,同时也把政府处罚言论自由权力的边界模糊化,实际上是把界定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边界的权力拱手交给公权力。高铭暄用相对主义这个工具,在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上偷掘了一个豁口,不仅能“证明”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是正当合法的,而且在暗中为今后公权力的进一步胡作非为保留了一扇进出方便的后门,威胁到我们每一个人。以相对主义解构普世的人权原则,就是高铭暄用来“正读”对刘晓波以言治罪合法所依仗的方法。在高铭暄手中,这种相对主义已经成为使用得得心应手的工具,成了正义与不义的转换器。通过它,他能很方便地把正义读成不义,把不义读成正义,能把刘晓波的爱国和善良读成罪恶,能把举世公认的迫害人权读成维护国家安全,也能把落井下石这种突破底线的极端无耻读作面不红心不跳的答记者问。
刘晓波对共产党统治状态作完全负面的描述与评价,不过是一个公民从自己的角度所作的观察结论,是在行使批评和监督执政者的公民权利。出现在《“因言获罪”是对刘晓波案判决的误读》中的高铭暄,显然忘记了刘晓波打从八九年毅然归国的时刻起,就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他所反对的充其量只是共产党,他如何推翻自己国家的政权?除非这个国家不是他的,与他无关。作为一个被迫害了二十二年的政治犯,一个为民主呐喊奔走不惜三度坐牢的爱国志士,怎么可能对迫害者歌功颂德?他对现实的负面评价有他的负面生存境况的事实作依据,如何便是“造谣、诽谤、诬蔑”?一个长年被软禁在书房里的书生论政有什么“现实社会危害性”?难道只有像高铭暄们那样成天为权贵拍马溜须才有“现实社会建设性”?高铭暄为何不读读二十五史?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像刘晓波那样不惧权势,不计利害,不顾安危,疾言厉色痛陈时弊的人们,从来都被誉为国家真正的栋梁,是国家的建设性力量!反之,那些紧跟在权势后面亦步亦趋,嘴里成天高唱“太平盛世”,暗地里为自己捞足名利之徒,没有一个不被谴责为奸臣。如果按照把直言敢谏视为最大美德的中国传统,而不是按照来自于前苏联的将服从视为美德的洋奴传统,那么,刘晓波的言行恰恰不仅不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而正是现实社会建设性的代表!把刘晓波关进牢房,却让高铭暄高据学坛,这是这个国家的悲剧!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指的正是这种现象。
高铭暄喜欢引经据典。也许他自以为通过引经据典就能证明自己这个共产党的御用刑法学“泰斗”不是浪得虚名,就能把迫害人权包装成司法正义。实际上,高铭暄的人格和“学识”也就仅限于能搞点“引经据典”。由迷信“法律是统治者意志和利益”、照搬照抄不敢更改前苏联法学权威一字的奴性十足的学术体制培养“成奴”的高铭暄,学到的核心原则就是“坚决与党保持一致”,终身赖以吃饭的工具则是“揣摩领导意图”。他的脑袋早已被权力强制灌输的这种一致性格式化,被权势安装了奴颜婢膝的小程序后,其毕生就被对权势的畏惧与媚颜讨好的小程序所占据,一辈子都在这个小程序里循环。高铭暄思维的内核就是讨领导欢心,对领导服从,其毕生的学术事业就是用法学术语解释、宣传和维护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这种阉割了批判与创造精神的方法是奴才的方法——所谓奴才,特点就是在强权面前止步,行为与思想全面止步,以主子之是非为是非。
高铭暄虽然靠卖弄刑法学“知道”捧了一辈子法学教授的金饭碗,却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刑法学。在以高铭暄领衔主编的《中国刑法学核心教程》里,前一页吹嘘书中的刑法学是科学,后一页又说刑法学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高铭暄们眼里,原来科学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就是科学!前一页大谈董必武、彭真、邓小平等等中共高官如何主导操纵立法,没有片言只字涉及到人民参与过立法,后一页却又断定共产党这种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和意志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书中逻辑矛盾百出。用这种学问教授出来的法学门生,怎能不是奴才加蠢材?岂能不以“服从领导”迫害人权为职志?整本书从未追问大陆现行刑法条款的正当性源头,这并不表明这些条款没有正当性源头,而只是书里的正当性论证是以隐蔽的方式完成的。它暗中贩卖给学生的预设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统治者制定的就是正当的。这本书从不打源头上追问更高级的法,制定法与公民权利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可看出,这本书的作者们大脑里缺根弦,或者说,他们那根原本属于理性范畴的弦,被贱卖给了权势。因此,在他们的学问中,强权就是更高级的法,强权需要的就是正当的——用书中引用过的列宁的信条表达就是:法律是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以高铭暄领衔编写的这本教材是一本相当恶劣的教材,对刑法学学理的阐述基本依靠东拼西凑,毫无批判意识,对现政权所立法律不给予半句质疑。其刑法“各论”部分以每一条款都是只能执行不能质疑的天然正当为前提,可说就是对现行法律条款的解释和宣传。这样的学者,认真说来,不是学者,而只是“喉舌”,是宣传员与解说员。
丧失了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所谓学者,不配被称为学者。像高铭暄这样的落井下石之辈被誉为“学界泰斗”,不过是当前道德沦丧在刑法学界的例证,是对学术的亵渎和侮辱!对像高铭暄这样的视侵犯我们言论自由权利为合法的“专家”,如果不早点从刑法学界驱逐出去,如果迫害人权被“正读”成维护国家安全,我们每个中国公民就除非像高铭暄那样随权力起舞,否则,就可能像刘晓波那样,随时面临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