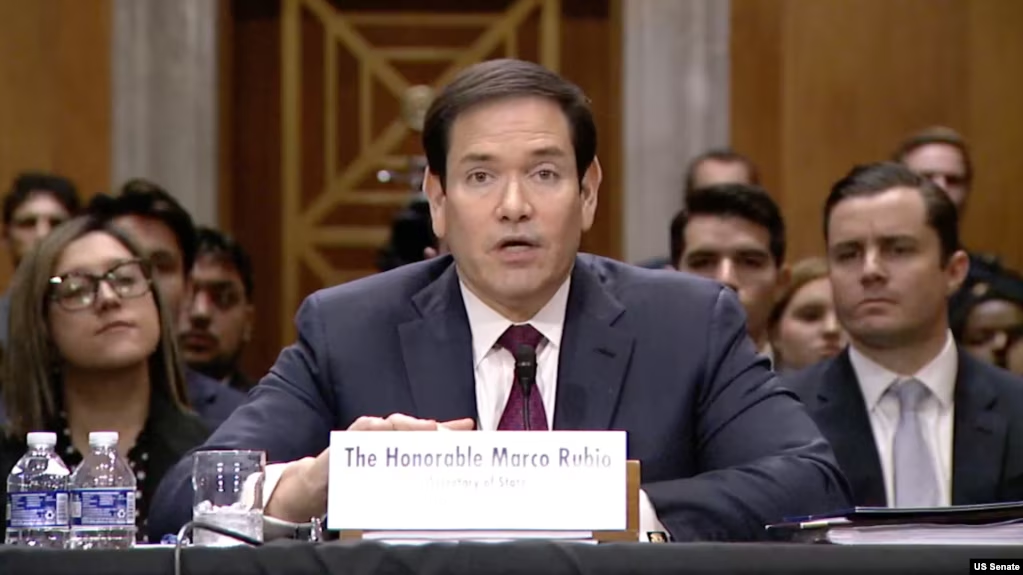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暨国立新竹教育大学教育学系兼任副教授
周静妮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法官
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在职硕士专班研究生
一、国际人权法关于冤狱或错案赔偿之规定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之《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3条宣示:「人人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之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复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于第9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同条第5款规定:「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赔偿的权利。」第14条第6项则尚明定:「经终局判决定罪之人,其后因有新事实或发现新证据,确实证明有误判而经撤销原定罪或赦免者,除经证明该相关之新事实之未及时揭露,全部或部分原因系可归责于该人者外,对因而误判而受罚之人,依法应赔偿其损害」,明定国家对因误判而造成冤狱之被害人,应负赔偿责任。由上可知,凡人身自由受国家机关不限于依据刑事程序也包括基于行政目的所为之非法逮捕与监禁,或因法院误判而曾受侵害者,均有权获得国家之赔偿。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6款规定之刑事赔偿,系以「误判」为要件,而必须系经判决确定后,提出新证据或发现新证据因而使原判决确实因误判而遭撤销或赦免者。如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观之,则仅有再审程序有规定可于确定判决后提出新事实与新证据。法院在既有之证据基础上做成之判决,因新证据之出现而遭推翻是否可称之为「误判」,显有价值之判断,但被告人身自由之一度丧失却是事实。我国对此类之行事赔偿称为冤狱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有学者称之为错案赔偿。此外,经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与经无罪判决确定但曾有下级审法院判决有罪者,以及虽经有罪判决确定但确定前曾有法院判决无罪者,乃不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得请求冤狱赔偿之范围内。该公约亦将赦免之情形纳入,赦免之原因,则未必基于误判,而可能系基于人道因素,这也是适用该公约所必须留意者。
中华民国于1967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直到2009年方由立法院批准,并另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关于要求各缔约国必须以立法来加以实践之规定,而由立法院订定〈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使之具有国内法上之效力,而得为各国家机关直接适用。
〈冤狱赔偿法〉系制定于1959年,其关于补偿之要件,系采损害赔偿之概念,司法院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70号解释〉认为〈冤狱赔偿法〉所定之国家责任,系国家因实现刑罚权或为实施教化、矫治之公共利益,对特定人民为羁押、收容、留置、刑或保安处分之执行,致其〈宪法〉保障之自由权利,受有超过一般应容忍程度之限制,而构成其个人特别牺牲时,依法律之规定,以金钱予以填补之刑事补偿,因此,该法所定之国家责任,并不以行使公权力执行职务之公务员有故意或过失之不法侵害行为为要件;另则认为〈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不得请求赔偿之规定,不符〈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意旨,与〈宪法〉第23条之比例原则有违,而要求该法有关限制赔偿请求权之规定,配合〈冤狱赔偿法〉相关法制为通盘检讨。于是而有〈冤狱赔偿法〉修正之启动,并于最后决定修正该法名称为〈刑事补偿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人身自由受国家司法侵害之损害填补情形,大略可分为两类,一为刑事赔偿,一为刑事补偿。受国家非法逮捕拘禁者,国家应负刑事赔偿责任,受国家依法之行为而生损害者,则可请求损失补偿。惟其用字并未清楚区别赔偿和补偿,而以赔偿一词涵盖全部情形。台湾的〈冤狱赔偿法〉同样情形,在其第1条规定人民得依该法请求国家赔偿。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6款规定之国家冤狱赔偿具体核心准则有三,即:国家冤狱赔偿责任原则、构成冤狱赔偿之积极事由,与国家免责之消极事由。国家冤狱赔偿责任原则系明定冤狱赔偿责任之主体为国家,由国家对冤狱被害人负法定赔偿责任,因而并非是国家代位法院承担清偿责任,而是国家自己责任的承担;构成冤狱之积极事由至少有三:受终局定罪而别无其他司法审查或上诉;被定罪而宣告其刑者;以有新事实或发现新事实,确实显示有误判,而撤销原定之罪或赦免者。故非因新事实之提出或发现而被撤销,或系经总统行使元首特权,依〈赦免法〉规定赦免被告者,即非属「误判」;而关于国家免责事由,系指可推翻原定罪之新事实,其未被实时揭露,系可归责于被告本人者,国家则得免赔偿之事由。
二、司法院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70号解释〉促成修法
司法院大法官于2010年1月做成之〈释字第670号解释〉,是促成〈冤狱赔偿法〉修正为〈刑事补偿法〉的直接原因。该号解释之争点乃有关国家免责事由,就〈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受押而不赔偿的规定是否违宪而为解释,大法官于解释文中认为:「受无罪判决确定之受害人,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或军事审判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受羁押者,依冤狱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不得请求赔偿,并未斟酌受害人致受羁押之行为,系涉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或系妨碍、误导侦查审判,亦无论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可归责程度之轻重及因羁押所受损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补偿请求,并非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所必要,不符冤狱赔偿法对个别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实现国家刑罚权之公共利益,受有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时,给予所规范之补偿,以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立法意旨,而与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有违,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至迟于届满二年时失其效力。」
该号解释之理由书谓:「人民受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之财产权,因公益需要而受特别牺牲者,应由国家依法律予以补偿,已迭经本院解释在案(本院释字第四○○号、第四二五号、第五一六号、第六五二号解释参照)。人民受宪法第八条保障身体之自由,乃行使其宪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权利之前提,为重要基本人权,尤其应受特别保护,亦迭经本院解释在案(本院释字第三八四号、第五八八号解释参照)。是特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公共利益受公权力之合法限制,诸如羁押、收容或留置等,而有特别情形致超越人民一般情况下所应容忍之程度,构成其个人之特别牺牲者,自应有依法向国家请求合理补偿之权利,以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意旨。冤狱赔偿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依刑事诉讼法、军事审判法、少年事件处理法或检肃流氓条例受理之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得依本法请求国家赔偿:一、不起诉处分或无罪、不受理之判决确定前,曾受羁押或收容。二、依再审或非常上诉程序判决无罪、不受理或撤销强制工作处分确定前,曾受羁押、收容、刑之执行或强制工作。三、不付审理或不付保护处分之裁定确定前,曾受收容。四、依重新审理程序裁定不付保护处分确定前,曾受收容或感化教育之执行。五、不付感训处分之裁定确定前,曾受留置。六、依重新审理程序裁定不付感训处分确定前,曾受留置或感训处分之执行。』本条项规定之国家赔偿,并非以行使公权力执行职务之公务员有故意或过失之不法侵害行为为要件。是冤狱赔偿法于形式上为国家赔偿法之特别法,然本条项所规定之国家赔偿,实系国家因实现刑罚权或为实施教化、矫治之公共利益,对特定人民为羁押、收容、留置、刑或保安处分之执行,致其宪法保障之自由权利,受有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限制,构成其个人之特别牺牲时,依法律之规定,以金钱予以填补之刑事补偿(以下称本条项之赔偿为补偿)。人民之自由权利因公共利益受有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法律规定给予补偿时,为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受害人对损失之发生或扩大,如有可归责之事由,固得审酌不同情状而排除或减少其补偿请求权,惟仍须为达成该目的所必要,始无违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冤狱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受羁押者,不得请求补偿部分(以下称系争规定),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及军事审判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所规定之羁押而言,并未斟酌受害人致受羁押之行为,系涉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或系妨碍、误导侦查审判(例如逃亡、串供、湮灭证据或虚伪自白等),亦无论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可归责程度之轻重及其因羁押所受损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补偿请求,并非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所必要,不符冤狱赔偿法对特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实现刑罚权之公共利益受有干涉,构成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时,给予所规范之补偿,以实现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立法意旨,而与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有违。系争规定应由相关机关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二年内,依本解释之意旨,衡酌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之情状、可归责程度及所受损失等事由,就是否限制其补偿请求权,予以限制时系全面排除或部分减少等,配合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通盘检讨,妥为规范,届期未完成修法者,系争规定失其效力。」
大法官于本号解释中,明确宣示〈冤狱赔偿法〉之法理,实为对于人民人身自由遭受侵害的损失补偿,而该一损失补偿则系基于对特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实现刑罚权之公共利益受有干涉,构成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时,给予之特别补偿,故而国家之责任系基于无过失责任主义,〈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2项规定:「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亦同。」第3条第2项规定:「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损害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可知〈国家赔偿法〉之赔偿原理系采过失主义,与〈冤狱赔偿法〉乃迥然不同,两者立法目的不同,所规范之行为合法性不同,损害填补方式亦有异,故而实亦不必将〈冤狱赔偿法〉安置于〈国家赔偿法〉之特别法地位。
其次,大法官指出,关于国家之免责范围,〈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规定,乃将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受羁押者完全排除于补偿之外,亦有违反〈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之处。〈宪法〉第23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之「必要」,实乃比例原则(der Grundsatz der Verhaeltnisma-essigkeit in Weiteren Sinne, The concept of proportionality)之规定,即要求国家行政、立法及司法行为对于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仅得于「必要」之范围内为之,即其手段与所欲实现之目的间,应有合理比例关系,不得不成比例。而所谓「必要」程度之衡量,〈行政程序法〉第7条之规定,则提供了一个可兹立法参照的基准:「一、采取之方法应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二、有多种同样能达成目的之方法时,应选择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者;三、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演绎大法官之意,刑事手段上基于发现真实和实现公平正义之目的而对于人民人身自由之限制,乃有其不得不然之理,而既要求人民为特别之牺牲,自然应尽可能给予等价之补偿。纵人民于自身人身自由之受限,可能有出于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之情形,但不能排除国家与有过失的存在,又对于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可归责程度之轻重及其因羁押所受损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补偿请求,乃并非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所必要,所以大法官认为〈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规定违反〈宪法〉第23条规定,而以两年为期,为届期无效之警告性裁判,并要求立法者衡酌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之情状、可归责程度及所受损失等事由,就是否限制其补偿请求权,予以限制时系全面排除或部分减少等,配合〈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通盘检讨。
三、〈刑事补偿法〉述评
〈刑事补偿法〉已于2011年6月修正通过施行,该法之立法,自然代表台湾人民之人身自由和司法人权,又再获得进一步的完善与保障。
〈刑事补偿法〉首先将人民关于其人身自由于公正审判中之特别牺牲,由国家承担之刑事补偿,由冤狱赔偿加以正名,自是值得肯定。但将原〈冤狱赔偿法〉第1条第2项「非依法律受羁押、收容、留置或执行」之情形,改写为「非依法律受羁押、鉴定留置、收容、刑罚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之执行」亦纳入刑事补偿范畴,而规定于〈刑事补偿法〉第1条第7款则有待商榷。此因「非依法律」限制人身自由之行为即已违宪违法,本就属于国家不法,合并于〈冤狱赔偿法〉中规范,本合乎其赔偿请求之性质,但将之改为补偿请求,则形成对于国家不法之损失补偿,法律逻辑上乃存在矛盾,至为不妥。如果立法政策上认为将国家之刑事不法纳入规范行政不法之〈国家赔偿法〉并不妥适,则宜另订「刑事赔偿法」或使之准用于刑事补偿。
〈刑事补偿法〉承认刑事保安处分有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质,则又为超越〈冤狱赔偿法〉之处。原〈冤狱赔偿法〉第1条第1项第2款仅列举强制工作处分,于拘束人身自由之其他保安处分,如〈刑法〉之监护、禁戒、强制工作或强制治疗等;〈窃盗犯赃物犯保安处分条例〉之强制工作;〈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观察、勒戒或强制戒治等处分,如其有实质违法情事,原皆未列入对于人民人身自由之保护范围,且于第2条第2款后段明文加以排除,〈刑事补偿法〉则将所有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处分纳入规范,于第1条第2款、第6款、第7款、第2条第3款、第5款予以增订,于人民人身自由之保护更臻周全。
关于国家免责事由,〈刑事补偿法〉实际上已将其范围大幅限缩。〈刑事补偿法〉第3条规定国家绝对免责之情形有二:「一、因刑法第十八条第一项或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之事由而受不起诉处分或无罪判决时,如有证据足认为无该事由即应起诉或为科刑、免刑判决;二、因判决并合处罚之一部受无罪之宣告,而其他部分受有罪之宣告时,其羁押、鉴定留置或收容期间未逾有罪确定裁判所定之刑、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期间。」前者实指因〈刑法〉第18条第1项「未满十四岁人」及第19条第1项「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两类以行为人不具责任能力而免除对其刑事诉究之情形,此与联合国排除政治性赦免不在冤狱或错案赔偿之道理相通,只要国家经由周详缜密之侦办,认定犯罪之行为与事实存在,仅因刑事立法政策豁免其刑责,乃不同意行为人请求刑事补偿。
原〈冤狱赔偿法〉违宪之第2条第3款规定已为〈刑事补偿法〉加以删除,该法同时亦删除了〈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2款前段「行为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而情节重大」而受羁押或留置、收容等处分,而却未受任何刑事有罪裁判者不得请求补偿之规定。〈社会秩序维护法〉第47条、第53条、第93条赋与警察机关对于违反该法案件嫌疑人24小时留置之权力,因涉及对于人身自由之限制,应由法院以判决为之,内政部已决定向行政院提案废除有关警察留置权之所有三个条文,〈刑事补偿法〉则先将留置纳入补偿范围,未来一旦〈社会秩序维护法〉中之警察留置权遭到废止,倘有警察使用此一权力,便构成不法,届时则将属于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故而宜再修正为准用〈刑事赔偿法〉。而警察于〈检肃流氓条例〉中之留置权和感训处分权,则因〈检肃流氓条例〉已经为司法院大法官于〈释字第384号解释〉、〈释字第523号解释〉、〈释字第636号解释〉三度宣告违宪而于2009年1月为立法院废止,已无从附丽而早经废止,原〈冤狱赔偿法〉当中有关〈检肃流氓条例〉之规定则皆已于〈刑事补偿法〉中删除。至若羁押、现行之留置或收容期间未逾因判决并合处罚之一部受无罪之宣告,而其他部分受有罪之宣告时有罪确定裁判所定之刑、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期间者,则皆不得请求补偿,因其已折抵刑与保安处分期间。
〈刑事补偿法〉第4条亦有关于国家免责事由之另一规定,倘「补偿请求之事由系因受害人意图招致犯罪嫌疑,而为误导侦查或审判之行为所致者,受理补偿事件之机关得不为补偿」,而「前项受害人之行为,应经有证据能力且经合法调查之证据证明之。」此一规定看似悖理,岂有人意图招致犯罪嫌疑而自限囹围之理。由于刑事补偿金每日以新台币三千至五千元计算,而目前台湾法定最低工资为月薪一万七千八百八十元,也就是说,人民遭国家不当限制人身自由达四日以上,其所获之补偿金额即已超过法定最低工资,对于无资力之人而言,乃不得不提防有人滥用刑事补偿制度以实际接济个人生计。
在以上国家免责事由之外,刑事补偿应平等适用于所有个案之受害人,而为使刑事补偿符合比例原则,〈刑事补偿法〉于第7条有关于补偿金额决定标准之规定,第8条则要求受理补偿事件之机关决定补偿金额时,「应审酌一切情状,尤应注意下列事项:一、公务员行为违法或不当之情节;二、受害人所受损失及可归责事由之程度。」而关于刑事偿补之覆审,则依新法将司法院冤狱赔偿法庭改制为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掌理之。而倘若刑事补偿事件之发生,系出于公务员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者,〈刑事补偿法〉第34条第2项则规定「补偿机关于补偿后,应依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该公务员求偿」。此一情形则不致发生于公正审判因再审而形成误判或错案之情形,但若存在枉法裁判之情事,则当有本条规定之适用。
四、台湾〈刑事补偿法〉对中国大陆刑事补偿制度的借鉴意义
〈刑事补偿法〉第34条第1项规定:「补偿经费由国库负担」。补偿义务机关虽需承担补偿审理决定之业务,但本身并不需要负担补偿经费,此一设计存在一制度诱因,使补偿义务机关乐于为受害人从事补偿之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法院与检察院之经费供给来自同级政府财政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共同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下级审法院和检察院列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亦将审判、起诉和侦查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被裁判无罪、撤销案件或强制措施之刑事赔偿责任加诸于本单位元或刑事程序的前一个单位,亦加重了下级审检机关之赔偿责任,而若将刑事公正审判下之错案赔偿责任与具体办案人员之考评连结一处,则更将导致承办人员为求免责而对于被告定罪之心理倾向,反不利于真实之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并未区分刑事赔偿与刑事补偿,将「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之情形与违法侵犯人身权之情形同列,一方面使公正侦审之审检机关常年暴露于刑事赔偿责任诉究之风险,另一方面因以过失责任主义决定国家赔偿之责任,在官官相护的科层文化中,人民殊难对于司法官之过失责任负举证责任,反而容易导致求偿不易之结果。从制度之设计上而言,关于人身自由之保护,反为不利。
至于在台湾以违反比例原则而被判定违宪之〈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亦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3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此实乃应当审慎审酌公民之可归责程度与是否存在国家之与有过失等情形,而不宜一概而论,全面排除国家之补偿乃至赔偿责任。
五、小结
两岸民间交往与日热络,台湾人民在中国大陆境内不慎违法之情形日多亦可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亦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签署国,如何就人身自由之保护,在刑事补偿与赔偿及其他相关领域达到国际人权法之水平,以作为世界文明之表率,招徕远人安心前来投资移民与就学,乃深值吾人之期待。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暨国立新竹教育大学教育学系兼任副教授
周静妮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法官
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在职硕士专班研究生
一、国际人权法关于冤狱或错案赔偿之规定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之《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3条宣示:「人人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之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复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于第9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同条第5款规定:「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赔偿的权利。」第14条第6项则尚明定:「经终局判决定罪之人,其后因有新事实或发现新证据,确实证明有误判而经撤销原定罪或赦免者,除经证明该相关之新事实之未及时揭露,全部或部分原因系可归责于该人者外,对因而误判而受罚之人,依法应赔偿其损害」,明定国家对因误判而造成冤狱之被害人,应负赔偿责任。由上可知,凡人身自由受国家机关不限于依据刑事程序也包括基于行政目的所为之非法逮捕与监禁,或因法院误判而曾受侵害者,均有权获得国家之赔偿。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6款规定之刑事赔偿,系以「误判」为要件,而必须系经判决确定后,提出新证据或发现新证据因而使原判决确实因误判而遭撤销或赦免者。如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观之,则仅有再审程序有规定可于确定判决后提出新事实与新证据。法院在既有之证据基础上做成之判决,因新证据之出现而遭推翻是否可称之为「误判」,显有价值之判断,但被告人身自由之一度丧失却是事实。我国对此类之行事赔偿称为冤狱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有学者称之为错案赔偿。此外,经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与经无罪判决确定但曾有下级审法院判决有罪者,以及虽经有罪判决确定但确定前曾有法院判决无罪者,乃不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得请求冤狱赔偿之范围内。该公约亦将赦免之情形纳入,赦免之原因,则未必基于误判,而可能系基于人道因素,这也是适用该公约所必须留意者。
中华民国于1967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直到2009年方由立法院批准,并另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关于要求各缔约国必须以立法来加以实践之规定,而由立法院订定〈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使之具有国内法上之效力,而得为各国家机关直接适用。
〈冤狱赔偿法〉系制定于1959年,其关于补偿之要件,系采损害赔偿之概念,司法院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70号解释〉认为〈冤狱赔偿法〉所定之国家责任,系国家因实现刑罚权或为实施教化、矫治之公共利益,对特定人民为羁押、收容、留置、刑或保安处分之执行,致其〈宪法〉保障之自由权利,受有超过一般应容忍程度之限制,而构成其个人特别牺牲时,依法律之规定,以金钱予以填补之刑事补偿,因此,该法所定之国家责任,并不以行使公权力执行职务之公务员有故意或过失之不法侵害行为为要件;另则认为〈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不得请求赔偿之规定,不符〈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意旨,与〈宪法〉第23条之比例原则有违,而要求该法有关限制赔偿请求权之规定,配合〈冤狱赔偿法〉相关法制为通盘检讨。于是而有〈冤狱赔偿法〉修正之启动,并于最后决定修正该法名称为〈刑事补偿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人身自由受国家司法侵害之损害填补情形,大略可分为两类,一为刑事赔偿,一为刑事补偿。受国家非法逮捕拘禁者,国家应负刑事赔偿责任,受国家依法之行为而生损害者,则可请求损失补偿。惟其用字并未清楚区别赔偿和补偿,而以赔偿一词涵盖全部情形。台湾的〈冤狱赔偿法〉同样情形,在其第1条规定人民得依该法请求国家赔偿。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6款规定之国家冤狱赔偿具体核心准则有三,即:国家冤狱赔偿责任原则、构成冤狱赔偿之积极事由,与国家免责之消极事由。国家冤狱赔偿责任原则系明定冤狱赔偿责任之主体为国家,由国家对冤狱被害人负法定赔偿责任,因而并非是国家代位法院承担清偿责任,而是国家自己责任的承担;构成冤狱之积极事由至少有三:受终局定罪而别无其他司法审查或上诉;被定罪而宣告其刑者;以有新事实或发现新事实,确实显示有误判,而撤销原定之罪或赦免者。故非因新事实之提出或发现而被撤销,或系经总统行使元首特权,依〈赦免法〉规定赦免被告者,即非属「误判」;而关于国家免责事由,系指可推翻原定罪之新事实,其未被实时揭露,系可归责于被告本人者,国家则得免赔偿之事由。
二、司法院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70号解释〉促成修法
司法院大法官于2010年1月做成之〈释字第670号解释〉,是促成〈冤狱赔偿法〉修正为〈刑事补偿法〉的直接原因。该号解释之争点乃有关国家免责事由,就〈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受押而不赔偿的规定是否违宪而为解释,大法官于解释文中认为:「受无罪判决确定之受害人,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或军事审判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受羁押者,依冤狱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不得请求赔偿,并未斟酌受害人致受羁押之行为,系涉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或系妨碍、误导侦查审判,亦无论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可归责程度之轻重及因羁押所受损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补偿请求,并非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所必要,不符冤狱赔偿法对个别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实现国家刑罚权之公共利益,受有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时,给予所规范之补偿,以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立法意旨,而与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有违,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至迟于届满二年时失其效力。」
该号解释之理由书谓:「人民受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之财产权,因公益需要而受特别牺牲者,应由国家依法律予以补偿,已迭经本院解释在案(本院释字第四○○号、第四二五号、第五一六号、第六五二号解释参照)。人民受宪法第八条保障身体之自由,乃行使其宪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权利之前提,为重要基本人权,尤其应受特别保护,亦迭经本院解释在案(本院释字第三八四号、第五八八号解释参照)。是特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公共利益受公权力之合法限制,诸如羁押、收容或留置等,而有特别情形致超越人民一般情况下所应容忍之程度,构成其个人之特别牺牲者,自应有依法向国家请求合理补偿之权利,以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意旨。冤狱赔偿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依刑事诉讼法、军事审判法、少年事件处理法或检肃流氓条例受理之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害人得依本法请求国家赔偿:一、不起诉处分或无罪、不受理之判决确定前,曾受羁押或收容。二、依再审或非常上诉程序判决无罪、不受理或撤销强制工作处分确定前,曾受羁押、收容、刑之执行或强制工作。三、不付审理或不付保护处分之裁定确定前,曾受收容。四、依重新审理程序裁定不付保护处分确定前,曾受收容或感化教育之执行。五、不付感训处分之裁定确定前,曾受留置。六、依重新审理程序裁定不付感训处分确定前,曾受留置或感训处分之执行。』本条项规定之国家赔偿,并非以行使公权力执行职务之公务员有故意或过失之不法侵害行为为要件。是冤狱赔偿法于形式上为国家赔偿法之特别法,然本条项所规定之国家赔偿,实系国家因实现刑罚权或为实施教化、矫治之公共利益,对特定人民为羁押、收容、留置、刑或保安处分之执行,致其宪法保障之自由权利,受有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限制,构成其个人之特别牺牲时,依法律之规定,以金钱予以填补之刑事补偿(以下称本条项之赔偿为补偿)。人民之自由权利因公共利益受有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法律规定给予补偿时,为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受害人对损失之发生或扩大,如有可归责之事由,固得审酌不同情状而排除或减少其补偿请求权,惟仍须为达成该目的所必要,始无违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冤狱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受羁押者,不得请求补偿部分(以下称系争规定),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及军事审判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所规定之羁押而言,并未斟酌受害人致受羁押之行为,系涉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或系妨碍、误导侦查审判(例如逃亡、串供、湮灭证据或虚伪自白等),亦无论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可归责程度之轻重及其因羁押所受损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补偿请求,并非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所必要,不符冤狱赔偿法对特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实现刑罚权之公共利益受有干涉,构成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时,给予所规范之补偿,以实现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立法意旨,而与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有违。系争规定应由相关机关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二年内,依本解释之意旨,衡酌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之情状、可归责程度及所受损失等事由,就是否限制其补偿请求权,予以限制时系全面排除或部分减少等,配合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通盘检讨,妥为规范,届期未完成修法者,系争规定失其效力。」
大法官于本号解释中,明确宣示〈冤狱赔偿法〉之法理,实为对于人民人身自由遭受侵害的损失补偿,而该一损失补偿则系基于对特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实现刑罚权之公共利益受有干涉,构成超越一般应容忍程度之特别牺牲时,给予之特别补偿,故而国家之责任系基于无过失责任主义,〈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2项规定:「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亦同。」第3条第2项规定:「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损害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可知〈国家赔偿法〉之赔偿原理系采过失主义,与〈冤狱赔偿法〉乃迥然不同,两者立法目的不同,所规范之行为合法性不同,损害填补方式亦有异,故而实亦不必将〈冤狱赔偿法〉安置于〈国家赔偿法〉之特别法地位。
其次,大法官指出,关于国家之免责范围,〈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规定,乃将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致受羁押者完全排除于补偿之外,亦有违反〈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之处。〈宪法〉第23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之「必要」,实乃比例原则(der Grundsatz der Verhaeltnisma-essigkeit in Weiteren Sinne, The concept of proportionality)之规定,即要求国家行政、立法及司法行为对于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仅得于「必要」之范围内为之,即其手段与所欲实现之目的间,应有合理比例关系,不得不成比例。而所谓「必要」程度之衡量,〈行政程序法〉第7条之规定,则提供了一个可兹立法参照的基准:「一、采取之方法应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二、有多种同样能达成目的之方法时,应选择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者;三、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演绎大法官之意,刑事手段上基于发现真实和实现公平正义之目的而对于人民人身自由之限制,乃有其不得不然之理,而既要求人民为特别之牺牲,自然应尽可能给予等价之补偿。纵人民于自身人身自由之受限,可能有出于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之情形,但不能排除国家与有过失的存在,又对于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可归责程度之轻重及其因羁押所受损失之大小皆一律排除全部之补偿请求,乃并非避免补偿失当或浮滥等情事所必要,所以大法官认为〈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规定违反〈宪法〉第23条规定,而以两年为期,为届期无效之警告性裁判,并要求立法者衡酌受害人致受羁押行为之情状、可归责程度及所受损失等事由,就是否限制其补偿请求权,予以限制时系全面排除或部分减少等,配合〈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通盘检讨。
三、〈刑事补偿法〉述评
〈刑事补偿法〉已于2011年6月修正通过施行,该法之立法,自然代表台湾人民之人身自由和司法人权,又再获得进一步的完善与保障。
〈刑事补偿法〉首先将人民关于其人身自由于公正审判中之特别牺牲,由国家承担之刑事补偿,由冤狱赔偿加以正名,自是值得肯定。但将原〈冤狱赔偿法〉第1条第2项「非依法律受羁押、收容、留置或执行」之情形,改写为「非依法律受羁押、鉴定留置、收容、刑罚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之执行」亦纳入刑事补偿范畴,而规定于〈刑事补偿法〉第1条第7款则有待商榷。此因「非依法律」限制人身自由之行为即已违宪违法,本就属于国家不法,合并于〈冤狱赔偿法〉中规范,本合乎其赔偿请求之性质,但将之改为补偿请求,则形成对于国家不法之损失补偿,法律逻辑上乃存在矛盾,至为不妥。如果立法政策上认为将国家之刑事不法纳入规范行政不法之〈国家赔偿法〉并不妥适,则宜另订「刑事赔偿法」或使之准用于刑事补偿。
〈刑事补偿法〉承认刑事保安处分有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质,则又为超越〈冤狱赔偿法〉之处。原〈冤狱赔偿法〉第1条第1项第2款仅列举强制工作处分,于拘束人身自由之其他保安处分,如〈刑法〉之监护、禁戒、强制工作或强制治疗等;〈窃盗犯赃物犯保安处分条例〉之强制工作;〈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之观察、勒戒或强制戒治等处分,如其有实质违法情事,原皆未列入对于人民人身自由之保护范围,且于第2条第2款后段明文加以排除,〈刑事补偿法〉则将所有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处分纳入规范,于第1条第2款、第6款、第7款、第2条第3款、第5款予以增订,于人民人身自由之保护更臻周全。
关于国家免责事由,〈刑事补偿法〉实际上已将其范围大幅限缩。〈刑事补偿法〉第3条规定国家绝对免责之情形有二:「一、因刑法第十八条第一项或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之事由而受不起诉处分或无罪判决时,如有证据足认为无该事由即应起诉或为科刑、免刑判决;二、因判决并合处罚之一部受无罪之宣告,而其他部分受有罪之宣告时,其羁押、鉴定留置或收容期间未逾有罪确定裁判所定之刑、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期间。」前者实指因〈刑法〉第18条第1项「未满十四岁人」及第19条第1项「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两类以行为人不具责任能力而免除对其刑事诉究之情形,此与联合国排除政治性赦免不在冤狱或错案赔偿之道理相通,只要国家经由周详缜密之侦办,认定犯罪之行为与事实存在,仅因刑事立法政策豁免其刑责,乃不同意行为人请求刑事补偿。
原〈冤狱赔偿法〉违宪之第2条第3款规定已为〈刑事补偿法〉加以删除,该法同时亦删除了〈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2款前段「行为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而情节重大」而受羁押或留置、收容等处分,而却未受任何刑事有罪裁判者不得请求补偿之规定。〈社会秩序维护法〉第47条、第53条、第93条赋与警察机关对于违反该法案件嫌疑人24小时留置之权力,因涉及对于人身自由之限制,应由法院以判决为之,内政部已决定向行政院提案废除有关警察留置权之所有三个条文,〈刑事补偿法〉则先将留置纳入补偿范围,未来一旦〈社会秩序维护法〉中之警察留置权遭到废止,倘有警察使用此一权力,便构成不法,届时则将属于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故而宜再修正为准用〈刑事赔偿法〉。而警察于〈检肃流氓条例〉中之留置权和感训处分权,则因〈检肃流氓条例〉已经为司法院大法官于〈释字第384号解释〉、〈释字第523号解释〉、〈释字第636号解释〉三度宣告违宪而于2009年1月为立法院废止,已无从附丽而早经废止,原〈冤狱赔偿法〉当中有关〈检肃流氓条例〉之规定则皆已于〈刑事补偿法〉中删除。至若羁押、现行之留置或收容期间未逾因判决并合处罚之一部受无罪之宣告,而其他部分受有罪之宣告时有罪确定裁判所定之刑、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期间者,则皆不得请求补偿,因其已折抵刑与保安处分期间。
〈刑事补偿法〉第4条亦有关于国家免责事由之另一规定,倘「补偿请求之事由系因受害人意图招致犯罪嫌疑,而为误导侦查或审判之行为所致者,受理补偿事件之机关得不为补偿」,而「前项受害人之行为,应经有证据能力且经合法调查之证据证明之。」此一规定看似悖理,岂有人意图招致犯罪嫌疑而自限囹围之理。由于刑事补偿金每日以新台币三千至五千元计算,而目前台湾法定最低工资为月薪一万七千八百八十元,也就是说,人民遭国家不当限制人身自由达四日以上,其所获之补偿金额即已超过法定最低工资,对于无资力之人而言,乃不得不提防有人滥用刑事补偿制度以实际接济个人生计。
在以上国家免责事由之外,刑事补偿应平等适用于所有个案之受害人,而为使刑事补偿符合比例原则,〈刑事补偿法〉于第7条有关于补偿金额决定标准之规定,第8条则要求受理补偿事件之机关决定补偿金额时,「应审酌一切情状,尤应注意下列事项:一、公务员行为违法或不当之情节;二、受害人所受损失及可归责事由之程度。」而关于刑事偿补之覆审,则依新法将司法院冤狱赔偿法庭改制为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掌理之。而倘若刑事补偿事件之发生,系出于公务员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者,〈刑事补偿法〉第34条第2项则规定「补偿机关于补偿后,应依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该公务员求偿」。此一情形则不致发生于公正审判因再审而形成误判或错案之情形,但若存在枉法裁判之情事,则当有本条规定之适用。
四、台湾〈刑事补偿法〉对中国大陆刑事补偿制度的借鉴意义
〈刑事补偿法〉第34条第1项规定:「补偿经费由国库负担」。补偿义务机关虽需承担补偿审理决定之业务,但本身并不需要负担补偿经费,此一设计存在一制度诱因,使补偿义务机关乐于为受害人从事补偿之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法院与检察院之经费供给来自同级政府财政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共同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下级审法院和检察院列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亦将审判、起诉和侦查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被裁判无罪、撤销案件或强制措施之刑事赔偿责任加诸于本单位元或刑事程序的前一个单位,亦加重了下级审检机关之赔偿责任,而若将刑事公正审判下之错案赔偿责任与具体办案人员之考评连结一处,则更将导致承办人员为求免责而对于被告定罪之心理倾向,反不利于真实之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并未区分刑事赔偿与刑事补偿,将「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之情形与违法侵犯人身权之情形同列,一方面使公正侦审之审检机关常年暴露于刑事赔偿责任诉究之风险,另一方面因以过失责任主义决定国家赔偿之责任,在官官相护的科层文化中,人民殊难对于司法官之过失责任负举证责任,反而容易导致求偿不易之结果。从制度之设计上而言,关于人身自由之保护,反为不利。
至于在台湾以违反比例原则而被判定违宪之〈冤狱赔偿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亦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3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此实乃应当审慎审酌公民之可归责程度与是否存在国家之与有过失等情形,而不宜一概而论,全面排除国家之补偿乃至赔偿责任。
五、小结
两岸民间交往与日热络,台湾人民在中国大陆境内不慎违法之情形日多亦可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亦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签署国,如何就人身自由之保护,在刑事补偿与赔偿及其他相关领域达到国际人权法之水平,以作为世界文明之表率,招徕远人安心前来投资移民与就学,乃深值吾人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