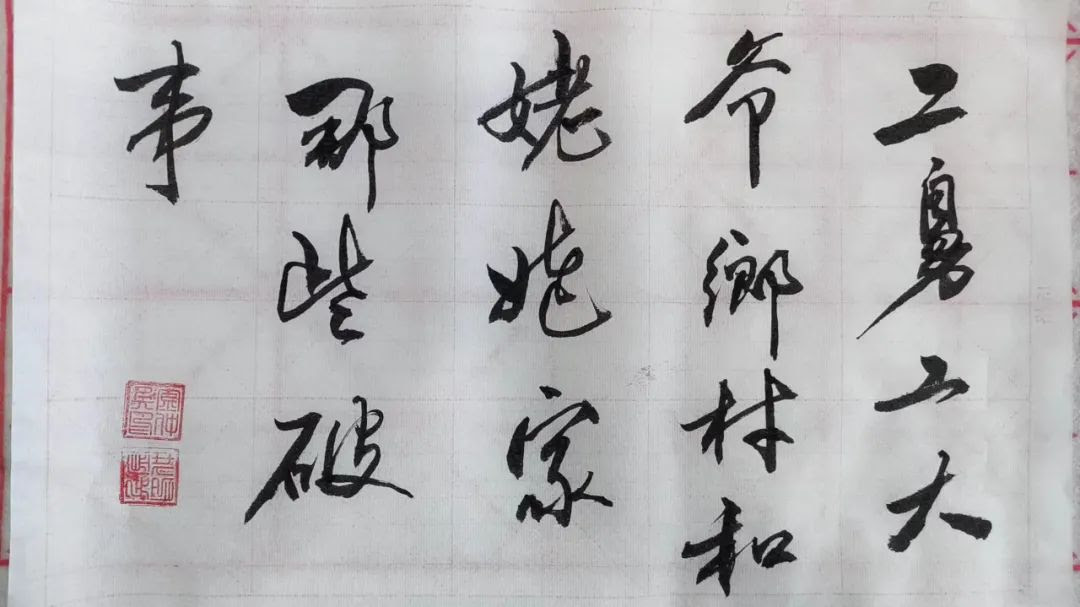2003年的一个下午,我经过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的一家建筑书屋,看到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有些土气的装帧设计,字体是那种看上去别扭的仿宋,完全不能和今天出版的畅销书媲美。但就是这么一本看上去灰头土脸的书,一本完全学术性的小众著作,我买到的版本却是第11次印刷,之前已经卖出去60000本了。
一直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是中国100年来少数几本具有国际水准,能够在历史里长久流传的伟大著作。
梁思成几乎在青年时代就抵达了这样的学术高峰。1924年,梁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他发现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还是空白,于是决心投身其中。1927年,他从宾大毕业后,申请在哈佛的科学和艺术研究生院研读一年,专门进行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文献考据。1928年回国后,他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对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开始实地调查。而在1944年,虽然国内战火频仍,虽然梁思成贫病交加,但他还是在四川李庄的农舍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1947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为表彰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为梁思成颁发了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赞词这样写道:“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如果说梁思成的学术贡献让我心驰神往,那么他的温文尔雅和内心宽阔的爱情品质更是令人感叹。梁思成曾经对林洙讲述过他与林徽因的爱情细节,说的是1932年的某一天,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见到他,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林徽因说起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像妻子对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梁思成听到这事,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梁思成也感谢林徽因对他的信任和坦白。第二天早上起来,梁思成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金岳霖一起幸福?梁甚至把自己、金岳霖、林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他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自己缺少金岳霖哲学家一般的头脑,认为自己不如金。梁思成把这样的结论告诉林徽因,并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金岳霖,祝愿他们永远幸福。两个人都哭了。过了几天,林徽因说,她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这些都是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美好往事。一个读书人,写出了有价值的好书,找到了最纯正、最透明的爱情。他的人生幸福抵达了最高点。1949年注定是梁思成的转折之年。这一年的年初,北京清华园,一名解放军干部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的带领下走进梁思成的家。他简单道明来由:由于即将攻打北平,共产党特意请梁思成绘制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不得已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四十七岁的梁思成竟然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梁思成的激动其来有自。此前二十年间,他在国内经历了战火、通货膨胀、近乎原始的贫穷生活,在国民党政权下受尽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之苦。尽管并不了解共产党,但他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然而共产党对文物的珍视远超出他的预想,做了他原来一直担心而不敢奢求的大事。多年过去之后,他想起这一刻,仍然饱含深情:“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如此心态,其实源于梁思成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家国意识。汉学家费慰梅女士曾回忆1934年与梁思成夫妇探寻山西广胜寺的艰难经过。由于阎锡山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在公路路基上铺铁轨,阻断汽车通行,他们只得步行前往。辛苦跋涉中,好心的外国传教士为他们提供食宿,梁思成却因“在自己的国家里靠外国人获得清洁和整齐而感到丧气。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准则的行为的伤害。”
按照梁思成的理解,1949年之后,怀揣一颗民族之心的梁思成应该能更好发挥他的大好才华。可是局面似乎并不如此。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梁思成和苏联市政专家一起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苏联专家指着对面的东交民巷操场,说应当在那里建设政府办公大楼,而梁思成早在七个月前就已经提出这块空地应辟为公园绿地。梁思成热爱的建筑美学问题上,他和这个崭新国家的分歧开始显现。
同年12月,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主持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建筑专家与苏联市政专家到会参加,关于行政中心区是建在北京旧城还是新市区的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梁、陈希望保护旧城,建议将中心区建在新市区,苏联专家则认为围绕天安门广场建立中心区,才是维护北京市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并且改造旧城将节省大量造价,更加经济。争执过程中,苏联专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毛泽东认为政府机关应该建在旧城。
由于苏联专家已经拿出书面方案,会后梁思成和陈占祥决定尽快拿出自己的方案来。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著名的“梁陈方案”出台了。
这份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建议》,包括“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三个部分。《建议》认为苏联专家提出的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不但不经济,而且“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两位学者进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建设政府行政中心的设想,认为这样“能同时顾全为人民节省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为建立进步的都市,为保持有历史价值的北京文物秩序的三方面。”他们还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的设想:“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
很快,这个方案被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企图否定”天安门的政治中心地位。与此同时,决策者毛泽东已经对行政中心区的位置有了明确意见。曾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句回忆:“苏联专家提出第一份北京建设意见,聂荣臻见到后,非常高兴,送毛主席。毛主席说:照此方针。所以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后来写到:“‘梁陈方案’被否定,主要不是没有钱,而是主席反对。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曾传出这么一句话来:毛主席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可见,毛主席对‘梁陈方案’很恼火: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央人民政府搬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最主要是毛主席不欣赏,如果毛主席欣赏的话,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不在话下的。”
“梁陈方案”被否决不久,高层传来了要拆除北京城墙的消息。1950年5月7日,病中的梁思成发表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该文秉承梁思成一向温和优雅的文风,却也态度坚决地表明了保护城墙的立场。他说:“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反而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地为我们可贵的环境。这样由它的物质的特殊和珍贵,形体的朴实雄壮,反映到我们感觉上来,它会丰富我们对北京的喜爱,增强我们民族精神的饱满。”
然而,梁思成的文章没能动摇决策者的决心。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为保住旧城梁思成四处奔走。一次,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与梁思成争执过程中竟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在场的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当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嗓音失声,但“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城墙、城门、牌楼还是陆续被拆除了。梁思成痛心疾首,多次落泪。后来,毛泽东给拆保之争定下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不久以后,东交民巷操场就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占用,盖起了政府机关大楼,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办公楼也在东长安街盖了起来。“梁陈方案”被实质的否定了。面对新式建筑即将大量涌入旧城的现实,梁思成退而求其次,试图保住北京城的天际线。于是,他在1951年11月召开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旧城大部分房屋应是两三层的。很快他发现,在建筑高度问题上,他又失败了——五六层的办公楼迅速地盖了起来。
1953年3月,梁思成奉命按照政府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原则,组织甲、乙两个规划方案。节节败退的梁思成转而希望可以保持和发展旧城中轴线,保住更多城墙和古建筑。基于现实考虑,他再次让步:不再坚持大部分房屋应是两三层的,提出有的房屋也可以盖到四五层、六七层,个别地区也可以有计划有限度的盖到十几到二十几层。
同时,他发现有很多行政机关随意圈地、各自为政、粗制滥造,导致大量“庞大而惹人注目的不正确、不调和的设计样式”产生,在苏联“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的启发下,他进一步强调,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地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梁思成对于高度问题的妥协,也没有得到认可,全部方案均未通过。1953年11月北京市委规划小组作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要点》指出:“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将天安门广场扩大,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据彭真的秘书马句的回忆录记载,《要点》是在毛泽东表态后才确定下来的。
眼看着高楼在旧城一座座建起,梁思成被迫一退再退,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旧城。他建议各部办公楼加盖“大屋顶”,而这原本是他最为厌恶的不伦不类形式。他曾在文章中批评“盖了一座洋楼,上面戴上琉璃瓦帽子”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头戴红缨帽”。在这样的审美问题上,这是梁思成与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相同。毛曾经说过:“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
事实上,心思缜密的梁思成到生命的终点,都不认同政府关于北京市城市建设的美学蓝图。在病床上,他对林洙说到,“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梁思成的这些话让他几乎成为一个先知。看看今天的北京城,人车汹涌,所有的道路,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中南海。这个巨大的城市一方面正在日复一日的拥挤,一方面却又摊大饼似的向外扩张,而这种气势磅礴的扩张却不能缓解城市的紧张。空气越来越糟糕,道路越来越拥挤,人口越来越稠密。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好办法来治理,所有人都以为这样的北京才是发展的北京,才是现代化的北京。看看那些指点江山、拆墙毁城的人们,他们有谁能偶尔想起梁思成,想起这个温文尔雅的建筑学家,这个充满古典主义精神的美学家,曾经在60年前就提出过美好的北京计划。如果这样的计划得以实施,今天的北京,应该处处与历史同在,应该不会如此拥挤不堪。
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意识形态中去。我们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个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失败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本文参考资料
《梁思成全集》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77年
《城记》王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刘军宁/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
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梁思成/文
1957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学习苏联城市建设和建筑的经验》梁思成/文
本文参考资料圣彼得马尔蒂雷教堂的礼拜堂梁思成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