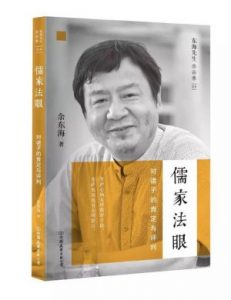狱中韩磊印象
我认识韩磊,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当时,那是一所集中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其中的刑事犯基本上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或死缓的。此外,也关押了一些政治犯和外籍犯。韩磊因盗窃了一辆轿车被判无期徒刑。这辆轿车原价大约三四十万元。当时正值1996年江泽民时期的严打,在满是重刑犯的二监,与韩磊同样被判无期徒刑的,不乏贪污了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贪污犯、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
我认识韩磊时,他刚刚因为打狱警被加刑一年。
起因大致如下:一天晚上,韩磊想给家人打电话——在狱中这叫“亲情电话”。但是狱警不允,在与狱警争抢电话中,韩磊打了狱警一耳光。在二监,与家人通电话不是犯人的基本人权,而是一种对待犯人的奖惩手段。狱方对“表现”不好的犯人,会以剥夺亲情电话作为惩罚。像我这种不认罪的政治犯,从来没有与家人通过电话。
我相信,如果韩磊能够与家人通电话,他的家人是不可能鼓励他与政府对抗的,我所见到的犯人家属,都是要自己的亲人在狱中好好服刑改造,争取早日出狱。而在被隔绝了亲情的情况下,犯人心理上孤独脆弱,很容易就会失去自我控制,做出过激行为。
因为打了狱警一耳光,韩磊付出的代价是被加刑一年,而且被关了“小号”,遭到暴打。“小号”是监狱惩罚犯人的禁闭室,大小仅可容身。韩磊还给我看过他背上遭到警察和其他犯人暴打留下的伤痕。
这次事件后,韩磊开始积极地争取减刑。他参加劳动,参加成人自学考试,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监狱规定,犯人参加成人自考,每通过一门课程,就会得到加分奖励,获得减刑。韩磊每次考试都要报七八门课程,而基本上都能通过。韩磊是很聪明的,智力、毅力均远过常人。
桀骜不驯的韩磊似乎服从“改造”了。但在私下里,他却说这纯粹是为了减刑,他从没有真正认同所加给他的刑罚。在一次被犯人欺负时,他发出尖厉的嘶喊,长期被压抑的愤怒在那一瞬间释放。但在漫长的服刑生活中,他的愤怒都不得不经常性地被压抑。
在狱中,犯人都被剃了光头。韩磊的头型上尖下圆,两耳高耸,我每次瞥见他低头走过的背影,都会心中一紧,仿佛看到地狱中的怨鬼,行迈迟迟,踽踽独行。
“无限自由”的自由裁量权
我还认识一些犯人,他们的罪刑失衡,比韩磊更严重。有一个犯人王平,因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他的盗窃行为有多么严重呢?他去偷牛蛙吃,不慎弄开了闸门,放跑了许多牛蛙。倒霉的是,这些牛蛙不是“一般”的牛蛙,而是公安部某疗养院养的、特供官僚们享用的牛蛙。结果王平就因偷吃牛蛙被判了无期徒刑。至于判决书,当然不会赤裸裸地说明原委,而是把那些放跑的牛蛙换算成价值上万元,这叫作“打成价值”。于是王平就因盗窃价值上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按照当局现行法律,盗窃价值数万元,就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农民王平,就因为嘴馋,而且偷错了地方,偷到公安部的后院,就被夺去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岁月,青春时光被葬送在了监狱里。他的事情,在犯人中是被当作笑料的,但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多么荒诞的“笑料”!
在二监的重刑犯中,诸如此类的犯人不胜枚举。犯人李建国,因盗窃价值数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犯人孙凯,因盗窃价值几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其实他偷的不过是几件衣服——这衣服当然要按市场价格换算,不可能按清仓大甩卖的价格“打成价值”。在二监的重刑犯中,盗窃几万元的和贪污几千万元的、偷一辆车和偷几十辆车的、盗窃的和杀人的,被判同样刑期的情况极为常见。有的甚至颠倒过来,盗窃的比抢劫的、强奸的、杀人的,判得还重;盗窃数额少的比贪污数额多的,判得还重;情节轻微的比情节恶劣的,判得还重。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局司法体制中,有一种“自由裁量权”!比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罪是这样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是新刑法的规定,而在以前的刑法中,犯盗窃罪是可以被判死刑的。
什么叫“数额特别巨大”?三万元以上就算。而从十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这个巨大的量刑空间,就由法官来裁量,这就是所谓“自由裁量权”。不仅盗窃罪是这样,其他罪名也是如此。犯某某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诸如此类。
从三年到十年,从十年有期徒刑到死刑,这其中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就掌握在司法官僚手中。换言之,同一种情况,既可以判三年刑,也可以判十年刑。三年和十年的差距有多大?它意味着你会多坐或少坐七年牢。对短暂的人生来说,七年牢狱对生活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更极端的是,同样的罪行,既可以判十年有期徒刑,也可以判无期徒刑,还可以判死刑。从十年刑到死刑,这个量刑空间多么广大,它甚至跨越了生死两重天!这是谈量刑空间,还没有涉及到对情节的定性问题。如果你向司法官僚行贿,那么你的情节就可能变轻,会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你被冤枉了,坚决不肯认罪,那么你就可能被定为顽抗,态度恶劣,要从严从重处罚。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在不同时期,同样的罪行会得到极为悬殊的结果。在平常不算严重的罪行,倘若正值当局的“严打”期间,就可能被判得极重,甚至被处死。真是“无限自由”的自由裁量权!
“罪对刑的攀比”
在量刑上如此广大的自由裁量权空间,为司法的黑暗、腐败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和肥沃的土壤。
在实行判例制度的英美法系中,量刑不是由法官随意决定的,而是要比照以往的判例,罪行大致相当,刑罚也大致相当。而在当局的司法中,量刑完全取决于司法官僚的意志,这就为其腐败提供了机会。司法官僚就可以利用这种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寻租,你如果满足了其要求,就可以少坐几年牢,甚至由死变活;如果你不能满足其要求,就可能多坐几年牢,甚至失去生命。司法黑暗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即使是这样一种法律,也还是一种“进步”。很多人未必知道,中国现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后才制定颁布的。而在1979年之前的三十年里,根本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可想而知,那时的司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司法官僚完全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而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王朝尚且有律法,明朝有《大明律》,清朝有《大清律》。
犯人们待在一起,自然就会相互比较各人的罪行和刑罚。面对这种明显失衡的量刑,很多犯人的心理当然会随之极度失衡。但在监狱的高压环境下,刑事罪犯为了减刑,仍然会按照狱方的要求写出“认罪悔罪书”。认罪悔罪书有统一的格式和要求,刑事罪犯之间经常相互抄袭。
在认罪悔罪书里,刑事罪犯会忏悔自己的罪行,并且表示,法院的定性是准确的,量刑是合理的,他们会坚决服从法院的判决。私底下,他们却认为,自己受到刑罚,并不是因为法律有多么公正严明,而是因为自己“没玩好”。因为他们看到,许多比他们罪行严重百倍的人,却判了与他们一样的刑罚,甚至更轻;更多与他们同样违法犯罪的人,由于有权有势或有钱,能够“摆平”官府,即使犯了罪,也可逍遥法外!
当局这套法制,在刑罚的目标和尺度上,都失去了合理性。它在执法中滥用权力,有权有势者即使犯了罪也能够逃脱法律制裁,或者大罪小罚,而无权无势者却小罪重判或无罪被判,这种滥权执法怎么可能起到惩戒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呢?刑事罪犯看到特权者逍遥法外,“玩得好”的人能够大事化小,觉得自己受刑是因为没有权势和金钱,是因为“没玩好”,在心理上就会失衡,就会用更大的犯罪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这叫作“罪对刑的攀比”。而中共监狱就是在执行这种刑罚的背景下,对犯人进行所谓“改造”。至于这种“改造”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有一个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北京市绝大部分刚被判刑的犯人,在下监之前,都要到这里集中,经过两三个月的“实习”,再分送到不同的监狱。我曾经在那里对周围的犯人做了一个粗略的调查统计,其中约有一半的犯人是“二进宫” 以上的,即两次以上犯罪的累犯。他们被称为“二哥”、“三哥”,乃至“七哥”、“八哥”。经过中共监狱的“改造”,刑事罪犯的再犯罪率是如此之高!
社会为制度买单
韩磊是1996年被判的无期徒刑,当时年仅22岁。他在狱中无论怎样减刑,也总要待上十六七年,出来时年近40,一无所有。他为一辆车付出青春的代价。算起来,他今年再次犯事,应该是在刚出来不久。
与路人偶然发生争执,彼此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会做出那种暴戾的行为?只能说,韩磊心中长期压抑积累的戾气和怨气找不到出口,终于在一个偶然情景下被引爆,发泄到一个无辜的儿童身上。不公正的制度在个人心中积聚的怨气,找不到出口,而转移发泄到其他无辜者身上,导致我们整个社会,都要为制度买单。
如果我们的视听、心智如果还没有彻底麻木的话,应该还能够想起近年来,多地频发的幼儿园杀童案,推延至今天的韩磊摔童案,这股戾气不可谓不深长凌厉!儿童是带血的祭品,凶手何尝不是负罪的牺牲。高潮迭起的悲剧的共同点是,都指向了一个社会最纯洁、最弱小、最无辜的群体,这已经是悲剧的顶点,是人类对生命本身的反噬。
而真正的导演者,那罪孽更重的作恶者,仍然隐身在堂而皇之的国徽之后,轧轧作响地运转着,也必然推陈出新,继续导演新的悲剧给我们看,给社会看,也给终将做出评判的历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