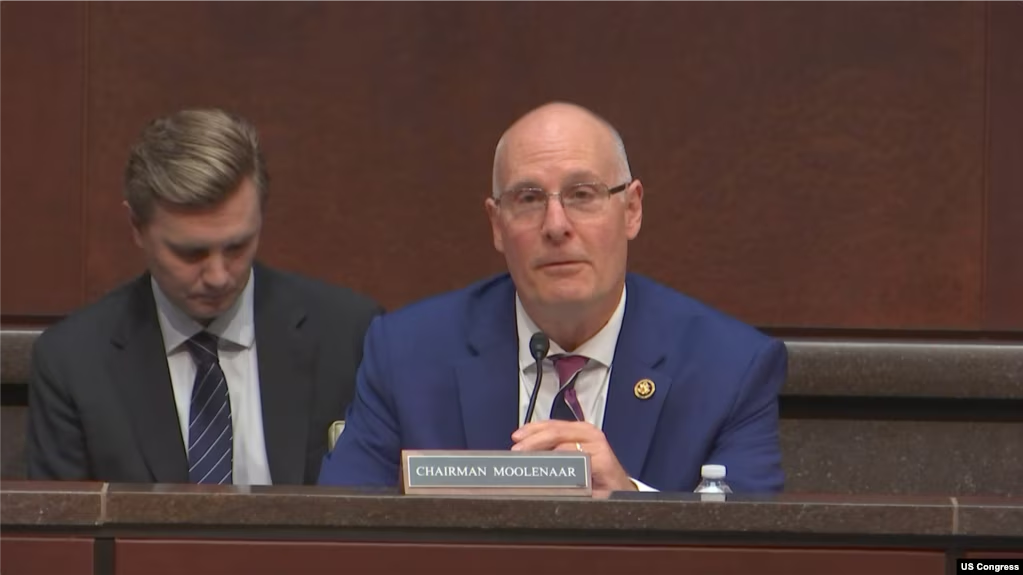被国民党供上神坛的孙文
1929年6月1日,清末立宪派领袖之一,当时充当退位皇帝溥仪顾问的郑孝胥在其日记中如是写道:诣行在。是日为阳历六月一日,南京乱党葬孙文于紫金山,风沙蔽天,金陵必有变异。
虽然郑孝胥希望孙文的葬礼进行不下去,但当天在南京却出现了一场规模超过皇帝葬礼的盛大仪式。孙文陵园占地二千多亩,不仅规模超过附近的明孝陵,气势上也超过以往的皇陵。孙文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口口声声反对帝制,反对复辟,但其死后的做派,无一不是按照中国历史上皇帝死后的做法。他的政治对手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其追随者不敢以皇帝之礼安葬他,其墓园被徐世昌命名为袁林,以示与皇陵的区别,而且袁林占地只有一百四十亩,规模远逊中山陵。据说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对取名袁林而不叫袁陵有所不满,徐世昌告诫道: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果,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用“袁陵”不妥。而孙文死后,其追随者竟然称其墓地为中山陵,公然把孙文看作中国的皇帝,对号称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而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据沈云龙在其《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一书中的记载:六月一日,为中山先生奉安之期。是日上午二时,奉安委员会特备之奉移汽车,即停于中央党部二门前院内,中央党部礼堂门首树立照坊及党旗,堂内铺以绿色地毯,花香满地,上悬匾额“精神不死”四字。奉安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及各组主任均先到场指挥,时中山路左右民众参观,道路拥塞……灵车自中央党部启行后,至陵墓二十里间,沿途两旁民众均脱帽肃立,瞻礼人数在五十万以上。
其实孙文早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但孙文临死之前,曾对他的追随者说了几个遗愿,一是希望死后“愿照其友列宁之办法,以防腐品保存其骸,纳诸棺内”以便于让他的追随者瞻仰。一是希望遣体“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132页)孙文死时,苏俄助其成立的军政府仍偏居广东一隅,孙文所谓党国大业并没有完成,因此他想葬于南京紫金山与朱元璋并列的遗愿一时无法达成,其追随者只好先将其遗体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孙楚部进入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告灭亡,代之以在孙文“党国、党军、暴力革命”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孙文的葬礼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就对外宣称: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此明示吾人今后之组织,虽为民主的集体制,然除全体党员正式投票选举代表而投票选举之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吾党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盖中华民国之独立自由,惟有完全继承中华民国创造者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意志,为能实现耳。1925年至1987年,国民党把孙文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些所谓遗教当作治国的圣经,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孙文的遗嘱说自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多少有些夸张。但自1893年兴中会成立孙文即参与其中,到1925年孙文离世还念念不忘要拯救中国,其革命的时间也长达32年。他生前是国民党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死后又成为了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为了把孙文神化,把国民党的党国事业合法化,1928年8月8日,在推翻民国政府2个月后,国民党即决定1929年1月1日为孙文安葬日,由于准备不及,后又几次变更时间,最后把安葬日定为1929年6月1日。
孙文死后,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即开始把孙文供上神坛。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通过决议,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月1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布《纪念周条例》,规定每周星期一上午8时为纪念周活动时间,其目的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而1929年5月开始的奉安大典,国民党的目的即在于向民众宣传孙文遗教,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之本。国民党试图通过奉安大典在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化洗脑教育。
国民党为此还规定了统一的宣传方式,如编发各种宣传品,讲演孙文革命之伟大精神及史略,演放有关孙文革命之各种影片,张贴各种迎榇图片等等。国民党反复强调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领导国民建设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党,要求民众拥护国民党、赞助国民党。1929年6月1日,在孙文的公祭仪式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如是说道:天生总理,辅相裁成。范围百世,覆育群生……国民革命,扶危定倾。后无来者,前无古人。建设国家,三民主义。独先创行,聪明睿知。岂即君子,博爱和平。神武不杀,此其至仁,脾睨群雄,锄除非种。夷险芟荒,是为大勇。呜呼总理,乃圣乃神。巍巍荡荡,民莫能名……(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00页)在这里,蒋介石把孙文吹捧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神圣。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孙文之于民国而言实乃罪人而非功臣。孙文通过所谓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秩序毁灭的干干净净。孙文革命几十年,所争的也并非民众的利益实乃自己的一己私利。孙文临死时,要追随者谨遵自己的遗教,要求保存自己的遗体,这些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丝毫谈不上为国为民。二十世纪的人类有几个人把自己的尸体制成木乃伊想不朽,他们是列宁、孙文、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然而在世人的眼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而非他们自认的救世主。
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训令尊孙文为“国父”: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源,宜表尊崇。兹经本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三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在案……此令,这样,孙文就被国民党捧上了国家的神坛。
天丧斯文,后无来者的梁启超
相比于孙文死后所得到的名实不符的巨大虚荣,孙文的同乡,清末民初的时代巨人梁启超死后却要凄凉许多,甚至可以说,到了1929年梁启超去世之时,中国人好像把他这个满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华民国的肈造者忘记的干干净净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而1925年孙文住过的医院恰好也是协和医院。不仅如此,为他们看病的医生都一样,先是德国人克里,后是外科专家刘瑞恒。所不同的是,1925年2月18日,孙文在协和医院确认其已无药可救后出院再接受中医治疗,而梁启超却一直在协和医院直至逝世。
1929年2月17日,梁启超葬礼在北京举行,当时,北京、上海两地梁之故旧为其举行了公祭仪式。天津《益世报》的《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二月十七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梁任公先生,业志二月十八日本报。兹将当日情状,简括追志如下:事前由广东旅平同乡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地素牌楼一座,并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等字样。门内为奏哀乐处,高悬阎锡山一联。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缀以“天丧斯文”四字。
……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梁启超年谱长编》776页)而上海公祭梁启超的也不过一百来人。
最主要的在于,梁启超的葬礼纯属自己的亲朋故旧所举办,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似乎没有一点关系,国民政府甚至于北平地方政府也没有派一人参加,这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刚刚攻占北京之时,国民政府就明令优恤前总统黎元洪,并着内政部详拟丧葬典礼。6月28日,又颁令国葬黎元洪,拨款一万元治丧,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
梁启超曾两度出任民国内阁总长,而且在袁世凯称帝后联络各方力量武装反袁,有再造民国之不世功勋,何况,自1896年加入时务报起就倡导维新,成为清末民初言论界第一人,满清灭亡和民国宪政秩序的建立,梁启超都居功至伟,这样一个民国伟人离世,国民政府居然视而不见,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其实梁启超非常在乎这些礼仪。1912年10月,梁启超从海外回到北京,他就把自己在北京受到的欢迎场面和孙文到北京受到的欢迎场面作了一番比较,并且津津乐道地告诉了自己的大女儿思顺。他在信中说::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
然而事易时移,1929年中国已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显然没有忘记几十年来孙文及其党徒与梁启超的恩怨纠葛。我们从国民党对待梁启超的态度中也可看出,国民党仅仅只是一个从自身利益和自身立场出发的视野狭隘的旧式政党,根本不具现代政党的气度。
而反观梁启超,却与国民党的做派完全不同。沈云龙在其《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一书中曾记载孙文死后梁启超前往吊唁的趣事:是日,梁启超曾至行馆吊唁。自清末以来,梁主立宪,孙主革命,政治见解互歧,入民国后,亦各行其是,甚少合作机会。故上海申报18日记其事云:“三月十四日,梁启超至中山行馆吊奠,致奠后,由汪精卫招待,其谈话有可记之价值。兹拉杂书之于后。梁问孙先生病逝时情形,汪即略述梗概,并谓先生自十一日夜半以后,已不能为有连贯的发言,惟断断续续以英语或粤语及普通语呼‘和平’‘奋斗’ ‘救中国’等语。梁极感叹谓:‘此足抵一部著作,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 时有党员问:‘昨日晨报所载足下论先生为目的不择手段等语,作何解释?’梁谓: ‘此仅慨叹中山先生之目的未能达到。’党员尚欲继续质问,汪谓:‘梁君吊丧而来,我们如有辩论,可到梁君府上,或在报上发表。’党员始无言而退。(《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188页)
据梁启超家人记述,梁启超并没有留下遗嘱,只是吩咐家人等其死后,将其尸体解剖,找出病因所在。梁启超曾自认自己对晚清思想界破坏甚巨但建设甚微,他还把自己与其师康有为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在旁皇求索中。
自1901年6月《立宪法议》发表,梁启超就不断为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秩序而奔走呼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梁启超也以自己言论方面的成就而获得了时人的肯定。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启超离世后,再也没有人象他一样在言论界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仅仅凭借手中的一枝笔,就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他是一个书生,但更是一个革命家,他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独一无二的书生革命家。
孙郎使天下三分:章太炎挽联成谶语
孙文死后,据其治丧处统计曾收到挽联59000余副、横幅500余条。在这众多挽联中,当时公推徐树铮的“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联为最佳。徐树铮是段祺瑞幕下的中坚人物,号称段系的灵魂,但在北洋集团中,他对孙文却颇为礼敬与友善。孙文死后,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了上面这副挽联。据黄埔军人出身的报人周游所记: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其实徐树铮此联真如周游所说道出了孙文的心事了吗?我看未必。民国建立后,时代的主流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秩序,恰恰是孙文的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才悍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则支那无一日安”才是孙文内心的写照,真正想称王者唯孙文耳。孙文死之前来北京的目的是联合段琪瑞、张作霖对抗曹锟、吴佩孚,没想到事没办成自己竟一身先死。对于孙的所作所为,一向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很有些看不下去,所以孙死后,他写有一副挽联讽刺孙文: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故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挽联借用三国与屈原故事,借古讽今,对孙文应段祺瑞等之邀北上,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对孙文建立军政府兴兵北伐,也提出严厉的批评。正因如此,这副挽联没有被孙的追随者允许挂在孙的追悼大会上。
孙文与段琪瑞、张作霖的三方合作因孙亡而作罢,但孙文联俄、容共的政治路线和一直借助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铲除国内异己的做派终于使中国饱尝恶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国在江西瑞金建立,毛泽东出任临时主席。1932年3月,日本人扶持早已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溥仪为执政,文章开头提到的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中国果然一分为三!这样的结果恰恰是孙文联俄捧日政策所致。“孙郎使天下三分”, 章太炎不是一语成谶么?
1924年11月孙文北上前先行赴日,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关于此次访日,孙文本人曾说是因为由上海到天津的船位已经定满了,再过十五日之后的船位,也是定满了。所以在上海等船,还不如绕道日本。其实这些不过是借口而已,孙文访日并非临时突然之举,而是在广州时就有了准备。11月17日到上海后,从日本返国的李烈钧极力劝说,坚定了孙文赴日的决心。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谋求建立以中、日、俄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洋同盟,以对抗西方。二是谋求日本的支持,以增强与段、张谈判的地位。
1924年11月28日下午,孙文在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演讲, 孙文说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日本自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便成了亚洲的头一个独立国家。其实早在1897年孙文初到日本之时,就赞成“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的说法。1913年孙文为日本军国主义头子头山满题联:西彦(谚)曰血浓于水,东古训唇齿相依。直至1923年,孙仍提议建立中日同盟,以日本为盟主。1924年访问日本时更表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
1929年6月1日,孙文所谓奉安大典,日人头山满、犬养毅、宫崎震作、梅屋庄吉、宫崎龙介等人作为孙之故旧被国民政府隆重邀请,而两年之后的“九一八”事变,头山满即是幕后主要的策划者。1925年3月12日孙文去世,头山满在题为《求亚洲民族之解放》的悼文中说:孙先生之功绩,非特欲求中国之富强,其求亚洲民族解放之决心亦未尝稍变。我与先生相知二十余年,先生每来日本,必来顾我。今闻此噩耗,能无怆然欲涕耶?孙文与头山满相交长达二十年之久,难道会不知道其对中国及中国人民所做的极为无耻的罪恶勾当?那些极力为孙文辩护的人,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白痴就是用心险恶的小人。
自五四运动过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升温,要求废除满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声音越来越响。孙文感到不改变自己以往一味依赖外部势力的做法将失去最基本的民众支持,所以他也跟着高喊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以争取国内激进力量的支持。1924年11月到日本之后,孙文试图与头山满等人讨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土地的问题,但遭到头山满当场拒绝,之后,孙文在各种场合不再提东北问题。1924年11月30日,与日本《告知报》记者代表的谈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代表先问:日人方面近传中山愿对于日本占领东三省土地之问题暂不置论,确否?中山答:良确。但此并非含有许日本处于其他列强不同的地位之意味。关于彼恢复中国独立之运动,现时以两点为限,一为废除治外法权,一为收回海关。至于日本在东三省之地位,彼认为与香港、澳门相同,目下并不要求归还。(《孙中山全集》11卷 420页)仅仅过了几年,日本人就发动“九一八”事变,将整个东北据为己有,头山满及与孙文关系深厚的黑龙会在此事件中充当了侵略中国急先锋的角色。
孙文死后,社会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副挽联: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这副挽联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及国民党奉孙文为国父、孙文学说为遗教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自1923年1月孙文与俄人越飞签订所谓《孙越宣言》开始联俄、容共后,在苏俄的极力扶持下,孙文势力急剧臌胀,并拥有了国民党的私人武装。新成立的苏共儿子党也开始飞速发展,中国已逐渐成为苏俄赤色势力范围。
孙文这些极端的政治主张,在当时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欲与孙文结成联盟的张作霖在与孙文见面时,就曾明确表示了自己反对孙文联俄、容共的做法。1924年12月4日,孙文从日本回到天津,不久即前往 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据叶恭绰年谱记载:总理抵津之日,访张于其寓邸,时在座者有张学良、杨宇庭、吴光新及先生(指叶恭绰)等五人,寒暄方毕,张即起言:“孙先生,我系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云云。其言甚显豁,可知其固出于诚意者也。(《遐庵汇编》俞诚之编)
孙文24年北上经过上海时,少年中国学会的创立者曾琦也曾与孙文见面,曾琦意在说服孙文放弃联俄容共的主张。据曾琦自订年谱记述:是年冬,孙中山先生北上过沪,予曾谒之于莫利爱路,劝其中止联俄容共,中山固执己见,予亦当仁不让,辩论久之,不欢而散……予预料国共之终必破裂,惟虑共产党非藉国民党之庇护而养成势力不可;复深知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故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藉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
对于孙文的联俄容共,梁启超一直极力反对,在与其长女思顺的书信中,曾多次提及。如1925年9月3日:共产党横行,广东不必说了,(广东宪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产权者。)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1926年9月29日: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指孙传芳)败以后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1927年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1月25日: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廷、加伦的羁绊——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
梁启超还在一封家书中谈到自己的儿子梁思永想加入共产党的事情: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我怕我们家里有共主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那全国青年之类比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
梁启超也在家书中直白地写出自己对孙文的看法:……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琪瑞、张作霖等——依然还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苏俄人指挥而成功者! (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以上均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尽管梁启超、曾琦,甚至张作霖等各派势力都极力反对孙文的党国政策,但没有底线和原则的孙文却一意孤行,在苏俄金钱和枪炮的支持下,由他的追随者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暴政政权,并开启了中国直至今天的党天下的罪恶历史。
梁启超与孙文都生于广东,都在清末起而否定满清的统治。只不过梁主张渐进改良而孙主张激烈革命。在他们三十多年为国奔走的生涯中,彼此几乎形同陌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梁与孙都属于善变一类的政治人物。只不过,梁的善变是以国家利益为考量,每一次变化都是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方向;而孙的善变则是以自身和党派私利为考量,每一次变化都是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梁的善变体现人性善,孙的善变表现出人性恶。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看到的梁启超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而孙文却是一个经过包装漏洞百出的神。
梁启超说自己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的事弄好,他就绝不惜向别人表深厚的同情,他还说自己从不采“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而孙文却恰恰相反,在孙文的人生哲学里,恰恰奉行的是“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所以他才会有“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则支那无一日安”这样极端的政治心态。
毫无疑问,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孙文和梁启超的影响力都非常巨大。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他们又在同一年彻底走进历史。所不同的是,孙文死后,他的追随者把他奉为国父,并在他“党国、党军、暴力革命”遗教指引下,最终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国,他的名头随着国民党的造神运动的不断深入也越来越响。而与孙文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党国、党天下调门越来越高,梁启超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以至于到了中共当政的时代,天下已没有几个人还知道中国曾经有个梁启超了。
1929年6月1日,清末立宪派领袖之一,当时充当退位皇帝溥仪顾问的郑孝胥在其日记中如是写道:诣行在。是日为阳历六月一日,南京乱党葬孙文于紫金山,风沙蔽天,金陵必有变异。
虽然郑孝胥希望孙文的葬礼进行不下去,但当天在南京却出现了一场规模超过皇帝葬礼的盛大仪式。孙文陵园占地二千多亩,不仅规模超过附近的明孝陵,气势上也超过以往的皇陵。孙文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口口声声反对帝制,反对复辟,但其死后的做派,无一不是按照中国历史上皇帝死后的做法。他的政治对手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其追随者不敢以皇帝之礼安葬他,其墓园被徐世昌命名为袁林,以示与皇陵的区别,而且袁林占地只有一百四十亩,规模远逊中山陵。据说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对取名袁林而不叫袁陵有所不满,徐世昌告诫道: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果,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用“袁陵”不妥。而孙文死后,其追随者竟然称其墓地为中山陵,公然把孙文看作中国的皇帝,对号称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而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据沈云龙在其《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一书中的记载:六月一日,为中山先生奉安之期。是日上午二时,奉安委员会特备之奉移汽车,即停于中央党部二门前院内,中央党部礼堂门首树立照坊及党旗,堂内铺以绿色地毯,花香满地,上悬匾额“精神不死”四字。奉安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及各组主任均先到场指挥,时中山路左右民众参观,道路拥塞……灵车自中央党部启行后,至陵墓二十里间,沿途两旁民众均脱帽肃立,瞻礼人数在五十万以上。
其实孙文早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但孙文临死之前,曾对他的追随者说了几个遗愿,一是希望死后“愿照其友列宁之办法,以防腐品保存其骸,纳诸棺内”以便于让他的追随者瞻仰。一是希望遣体“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132页)孙文死时,苏俄助其成立的军政府仍偏居广东一隅,孙文所谓党国大业并没有完成,因此他想葬于南京紫金山与朱元璋并列的遗愿一时无法达成,其追随者只好先将其遗体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孙楚部进入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告灭亡,代之以在孙文“党国、党军、暴力革命”理论下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后,孙文的葬礼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就对外宣称: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此明示吾人今后之组织,虽为民主的集体制,然除全体党员正式投票选举代表而投票选举之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总理。吾党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盖中华民国之独立自由,惟有完全继承中华民国创造者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意志,为能实现耳。1925年至1987年,国民党把孙文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些所谓遗教当作治国的圣经,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孙文的遗嘱说自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多少有些夸张。但自1893年兴中会成立孙文即参与其中,到1925年孙文离世还念念不忘要拯救中国,其革命的时间也长达32年。他生前是国民党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死后又成为了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为了把孙文神化,把国民党的党国事业合法化,1928年8月8日,在推翻民国政府2个月后,国民党即决定1929年1月1日为孙文安葬日,由于准备不及,后又几次变更时间,最后把安葬日定为1929年6月1日。
孙文死后,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即开始把孙文供上神坛。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通过决议,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月1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布《纪念周条例》,规定每周星期一上午8时为纪念周活动时间,其目的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而1929年5月开始的奉安大典,国民党的目的即在于向民众宣传孙文遗教,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之本。国民党试图通过奉安大典在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化洗脑教育。
国民党为此还规定了统一的宣传方式,如编发各种宣传品,讲演孙文革命之伟大精神及史略,演放有关孙文革命之各种影片,张贴各种迎榇图片等等。国民党反复强调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领导国民建设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党,要求民众拥护国民党、赞助国民党。1929年6月1日,在孙文的公祭仪式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如是说道:天生总理,辅相裁成。范围百世,覆育群生……国民革命,扶危定倾。后无来者,前无古人。建设国家,三民主义。独先创行,聪明睿知。岂即君子,博爱和平。神武不杀,此其至仁,脾睨群雄,锄除非种。夷险芟荒,是为大勇。呜呼总理,乃圣乃神。巍巍荡荡,民莫能名……(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00页)在这里,蒋介石把孙文吹捧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神圣。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孙文之于民国而言实乃罪人而非功臣。孙文通过所谓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秩序毁灭的干干净净。孙文革命几十年,所争的也并非民众的利益实乃自己的一己私利。孙文临死时,要追随者谨遵自己的遗教,要求保存自己的遗体,这些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丝毫谈不上为国为民。二十世纪的人类有几个人把自己的尸体制成木乃伊想不朽,他们是列宁、孙文、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然而在世人的眼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而非他们自认的救世主。
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训令尊孙文为“国父”: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源,宜表尊崇。兹经本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三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在案……此令,这样,孙文就被国民党捧上了国家的神坛。
天丧斯文,后无来者的梁启超
相比于孙文死后所得到的名实不符的巨大虚荣,孙文的同乡,清末民初的时代巨人梁启超死后却要凄凉许多,甚至可以说,到了1929年梁启超去世之时,中国人好像把他这个满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华民国的肈造者忘记的干干净净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而1925年孙文住过的医院恰好也是协和医院。不仅如此,为他们看病的医生都一样,先是德国人克里,后是外科专家刘瑞恒。所不同的是,1925年2月18日,孙文在协和医院确认其已无药可救后出院再接受中医治疗,而梁启超却一直在协和医院直至逝世。
1929年2月17日,梁启超葬礼在北京举行,当时,北京、上海两地梁之故旧为其举行了公祭仪式。天津《益世报》的《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二月十七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梁任公先生,业志二月十八日本报。兹将当日情状,简括追志如下:事前由广东旅平同乡在广惠寺大门高扎蓝花白地素牌楼一座,并用蓝花扎成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等字样。门内为奏哀乐处,高悬阎锡山一联。祭台前用素花扎成牌楼,缀以“天丧斯文”四字。
…… 是日到者甚众,除尚志学会、时务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司法储才馆、广东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外,有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林砺儒、瞿世英、杨树达、熊佛西、余上沅、蓝志先、任鸿隽、陈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钱稻孙、袁同礼等,门人中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约五百余人。(《梁启超年谱长编》776页)而上海公祭梁启超的也不过一百来人。
最主要的在于,梁启超的葬礼纯属自己的亲朋故旧所举办,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似乎没有一点关系,国民政府甚至于北平地方政府也没有派一人参加,这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刚刚攻占北京之时,国民政府就明令优恤前总统黎元洪,并着内政部详拟丧葬典礼。6月28日,又颁令国葬黎元洪,拨款一万元治丧,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
梁启超曾两度出任民国内阁总长,而且在袁世凯称帝后联络各方力量武装反袁,有再造民国之不世功勋,何况,自1896年加入时务报起就倡导维新,成为清末民初言论界第一人,满清灭亡和民国宪政秩序的建立,梁启超都居功至伟,这样一个民国伟人离世,国民政府居然视而不见,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其实梁启超非常在乎这些礼仪。1912年10月,梁启超从海外回到北京,他就把自己在北京受到的欢迎场面和孙文到北京受到的欢迎场面作了一番比较,并且津津乐道地告诉了自己的大女儿思顺。他在信中说::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
然而事易时移,1929年中国已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显然没有忘记几十年来孙文及其党徒与梁启超的恩怨纠葛。我们从国民党对待梁启超的态度中也可看出,国民党仅仅只是一个从自身利益和自身立场出发的视野狭隘的旧式政党,根本不具现代政党的气度。
而反观梁启超,却与国民党的做派完全不同。沈云龙在其《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一书中曾记载孙文死后梁启超前往吊唁的趣事:是日,梁启超曾至行馆吊唁。自清末以来,梁主立宪,孙主革命,政治见解互歧,入民国后,亦各行其是,甚少合作机会。故上海申报18日记其事云:“三月十四日,梁启超至中山行馆吊奠,致奠后,由汪精卫招待,其谈话有可记之价值。兹拉杂书之于后。梁问孙先生病逝时情形,汪即略述梗概,并谓先生自十一日夜半以后,已不能为有连贯的发言,惟断断续续以英语或粤语及普通语呼‘和平’‘奋斗’ ‘救中国’等语。梁极感叹谓:‘此足抵一部著作,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 时有党员问:‘昨日晨报所载足下论先生为目的不择手段等语,作何解释?’梁谓: ‘此仅慨叹中山先生之目的未能达到。’党员尚欲继续质问,汪谓:‘梁君吊丧而来,我们如有辩论,可到梁君府上,或在报上发表。’党员始无言而退。(《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188页)
据梁启超家人记述,梁启超并没有留下遗嘱,只是吩咐家人等其死后,将其尸体解剖,找出病因所在。梁启超曾自认自己对晚清思想界破坏甚巨但建设甚微,他还把自己与其师康有为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在旁皇求索中。
自1901年6月《立宪法议》发表,梁启超就不断为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秩序而奔走呼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梁启超也以自己言论方面的成就而获得了时人的肯定。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启超离世后,再也没有人象他一样在言论界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仅仅凭借手中的一枝笔,就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他是一个书生,但更是一个革命家,他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独一无二的书生革命家。
孙郎使天下三分:章太炎挽联成谶语
孙文死后,据其治丧处统计曾收到挽联59000余副、横幅500余条。在这众多挽联中,当时公推徐树铮的“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联为最佳。徐树铮是段祺瑞幕下的中坚人物,号称段系的灵魂,但在北洋集团中,他对孙文却颇为礼敬与友善。孙文死后,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了上面这副挽联。据黄埔军人出身的报人周游所记: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其实徐树铮此联真如周游所说道出了孙文的心事了吗?我看未必。民国建立后,时代的主流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秩序,恰恰是孙文的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才悍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则支那无一日安”才是孙文内心的写照,真正想称王者唯孙文耳。孙文死之前来北京的目的是联合段琪瑞、张作霖对抗曹锟、吴佩孚,没想到事没办成自己竟一身先死。对于孙的所作所为,一向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很有些看不下去,所以孙死后,他写有一副挽联讽刺孙文: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故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挽联借用三国与屈原故事,借古讽今,对孙文应段祺瑞等之邀北上,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对孙文建立军政府兴兵北伐,也提出严厉的批评。正因如此,这副挽联没有被孙的追随者允许挂在孙的追悼大会上。
孙文与段琪瑞、张作霖的三方合作因孙亡而作罢,但孙文联俄、容共的政治路线和一直借助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铲除国内异己的做派终于使中国饱尝恶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国在江西瑞金建立,毛泽东出任临时主席。1932年3月,日本人扶持早已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溥仪为执政,文章开头提到的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中国果然一分为三!这样的结果恰恰是孙文联俄捧日政策所致。“孙郎使天下三分”, 章太炎不是一语成谶么?
1924年11月孙文北上前先行赴日,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关于此次访日,孙文本人曾说是因为由上海到天津的船位已经定满了,再过十五日之后的船位,也是定满了。所以在上海等船,还不如绕道日本。其实这些不过是借口而已,孙文访日并非临时突然之举,而是在广州时就有了准备。11月17日到上海后,从日本返国的李烈钧极力劝说,坚定了孙文赴日的决心。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谋求建立以中、日、俄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洋同盟,以对抗西方。二是谋求日本的支持,以增强与段、张谈判的地位。
1924年11月28日下午,孙文在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演讲, 孙文说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日本自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便成了亚洲的头一个独立国家。其实早在1897年孙文初到日本之时,就赞成“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的说法。1913年孙文为日本军国主义头子头山满题联:西彦(谚)曰血浓于水,东古训唇齿相依。直至1923年,孙仍提议建立中日同盟,以日本为盟主。1924年访问日本时更表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
1929年6月1日,孙文所谓奉安大典,日人头山满、犬养毅、宫崎震作、梅屋庄吉、宫崎龙介等人作为孙之故旧被国民政府隆重邀请,而两年之后的“九一八”事变,头山满即是幕后主要的策划者。1925年3月12日孙文去世,头山满在题为《求亚洲民族之解放》的悼文中说:孙先生之功绩,非特欲求中国之富强,其求亚洲民族解放之决心亦未尝稍变。我与先生相知二十余年,先生每来日本,必来顾我。今闻此噩耗,能无怆然欲涕耶?孙文与头山满相交长达二十年之久,难道会不知道其对中国及中国人民所做的极为无耻的罪恶勾当?那些极力为孙文辩护的人,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白痴就是用心险恶的小人。
自五四运动过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升温,要求废除满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声音越来越响。孙文感到不改变自己以往一味依赖外部势力的做法将失去最基本的民众支持,所以他也跟着高喊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以争取国内激进力量的支持。1924年11月到日本之后,孙文试图与头山满等人讨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土地的问题,但遭到头山满当场拒绝,之后,孙文在各种场合不再提东北问题。1924年11月30日,与日本《告知报》记者代表的谈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代表先问:日人方面近传中山愿对于日本占领东三省土地之问题暂不置论,确否?中山答:良确。但此并非含有许日本处于其他列强不同的地位之意味。关于彼恢复中国独立之运动,现时以两点为限,一为废除治外法权,一为收回海关。至于日本在东三省之地位,彼认为与香港、澳门相同,目下并不要求归还。(《孙中山全集》11卷 420页)仅仅过了几年,日本人就发动“九一八”事变,将整个东北据为己有,头山满及与孙文关系深厚的黑龙会在此事件中充当了侵略中国急先锋的角色。
孙文死后,社会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副挽联: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这副挽联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及国民党奉孙文为国父、孙文学说为遗教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自1923年1月孙文与俄人越飞签订所谓《孙越宣言》开始联俄、容共后,在苏俄的极力扶持下,孙文势力急剧臌胀,并拥有了国民党的私人武装。新成立的苏共儿子党也开始飞速发展,中国已逐渐成为苏俄赤色势力范围。
孙文这些极端的政治主张,在当时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欲与孙文结成联盟的张作霖在与孙文见面时,就曾明确表示了自己反对孙文联俄、容共的做法。1924年12月4日,孙文从日本回到天津,不久即前往 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据叶恭绰年谱记载:总理抵津之日,访张于其寓邸,时在座者有张学良、杨宇庭、吴光新及先生(指叶恭绰)等五人,寒暄方毕,张即起言:“孙先生,我系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云云。其言甚显豁,可知其固出于诚意者也。(《遐庵汇编》俞诚之编)
孙文24年北上经过上海时,少年中国学会的创立者曾琦也曾与孙文见面,曾琦意在说服孙文放弃联俄容共的主张。据曾琦自订年谱记述:是年冬,孙中山先生北上过沪,予曾谒之于莫利爱路,劝其中止联俄容共,中山固执己见,予亦当仁不让,辩论久之,不欢而散……予预料国共之终必破裂,惟虑共产党非藉国民党之庇护而养成势力不可;复深知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故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藉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
对于孙文的联俄容共,梁启超一直极力反对,在与其长女思顺的书信中,曾多次提及。如1925年9月3日:共产党横行,广东不必说了,(广东宪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产权者。)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1926年9月29日: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指孙传芳)败以后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1927年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1月25日: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廷、加伦的羁绊——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
梁启超还在一封家书中谈到自己的儿子梁思永想加入共产党的事情: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我怕我们家里有共主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那全国青年之类比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
梁启超也在家书中直白地写出自己对孙文的看法:……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琪瑞、张作霖等——依然还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苏俄人指挥而成功者! (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以上均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尽管梁启超、曾琦,甚至张作霖等各派势力都极力反对孙文的党国政策,但没有底线和原则的孙文却一意孤行,在苏俄金钱和枪炮的支持下,由他的追随者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暴政政权,并开启了中国直至今天的党天下的罪恶历史。
梁启超与孙文都生于广东,都在清末起而否定满清的统治。只不过梁主张渐进改良而孙主张激烈革命。在他们三十多年为国奔走的生涯中,彼此几乎形同陌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梁与孙都属于善变一类的政治人物。只不过,梁的善变是以国家利益为考量,每一次变化都是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方向;而孙的善变则是以自身和党派私利为考量,每一次变化都是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梁的善变体现人性善,孙的善变表现出人性恶。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看到的梁启超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而孙文却是一个经过包装漏洞百出的神。
梁启超说自己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的事弄好,他就绝不惜向别人表深厚的同情,他还说自己从不采“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而孙文却恰恰相反,在孙文的人生哲学里,恰恰奉行的是“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所以他才会有“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则支那无一日安”这样极端的政治心态。
毫无疑问,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孙文和梁启超的影响力都非常巨大。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他们又在同一年彻底走进历史。所不同的是,孙文死后,他的追随者把他奉为国父,并在他“党国、党军、暴力革命”遗教指引下,最终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国,他的名头随着国民党的造神运动的不断深入也越来越响。而与孙文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党国、党天下调门越来越高,梁启超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以至于到了中共当政的时代,天下已没有几个人还知道中国曾经有个梁启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