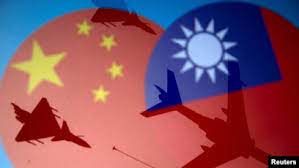《殉道者·缅怀陈子明》(明镜出版社)
法广:高伐林先生,我注意到,《殉道者·缅怀陈子明》这本书,没有给陈子明冠以“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这一类头衔,只是称他为“殉道者”。这是为什么?
高伐林:我想,这是因为陈子明所涉猎的领域太广,从事的活动太多,难以界定、也难以罗列。用他近40年的伙伴王军涛的话来说:“在20世纪推动极权主义制度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陈子明一个人做出的开拓性努力,几乎涵盖了除了武装暴动之外的所有事业:他打过选战,组织过街头抗议,主编过独立民刊,办过大学,出版过丛书,建立过民间智库,进行过填补国家空白的理论研究;他坐过牢,在狱中进行过维权抗争;他甚至办过高科技开发公司、基金会和音像图书印制发行企业……”而且,这些活动,还都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最后就发现,只有“殉道者”这个名称,对他来说最恰如其分,他也最当之无愧。
法广:陈子明是怎样成长起来、又是怎样从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呢?
高伐林:他是中国现当代反对专制的先知先觉与先行者。上海出生,北京念书,“文革”中,他到内蒙插队,当过羊倌、赤脚医生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他的一封批评时政的信件遗失,被拾到者上交化工学院保卫处,又转交北京市公安局,于是他以“反革命小集团”嫌疑被关进了看守所。
陈子明崭露头角,是在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被推举为与当局谈判的群众代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出现短暂而猛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是民刊《北京之春》编委;随后又投入北京高校竞选热潮,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身份,当选海淀区第七届人大代表。这次竞选,在大学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启蒙,意义深远,一大批有胆有识的新型人才涌现出来。
法广:陈子明抓住了时机,集结了队伍?
高伐林:是的,就有了一系列“第一”:1987年他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民间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8年接办《经济学周报》,这是借腹怀胎的中国第一家民营报刊。可惜他的事业被“六四”打断。他从一开始就审慎看待广场请愿,但最后还是因其民间政治家的履历和政治反对派的色彩,被当局视为“幕后黑手”,判处13年徒刑。他在秦城监狱中写的“我的辩护书”,不仅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轨迹与理念,并超越个人荣辱,对学运做出辩护与评说,该文可与中外历史上政治犯们的最优秀辩护书媲美。
法广:他是什么时候走出监狱的呢?出狱之后面临新的时代,陈子明有了哪些变化?
高伐林:他是2002年刑满释放的。13年牢狱生涯,陈子明成了饱学之士、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他出狱后创办了“改造与建设”网站,更用各种笔名,在海内外发表闪烁真知灼见的论文,有人评价,他是中国思想界最能打通理论与现实的智者。2010年出版的12卷《陈子明文集》,给中国未来的变革和发展,留下了厚重博大的精神遗产。
当然,陈子明并不甘心只当一个思想家。他对朋友说:我目前做些思想和学术工作,日后当然要搞政治,不然对不起国家的栽培、大家的栽培。
法广:他渴望怎样投入政治活动呢?
高伐林:他的朋友说,子明除了“不会作秀”这项欠缺,在很多方面是天生的政治家。他几乎永远乐观,对任何最悲观的问题,都信心满满地给你解答,他是真的相信事情总是可为的、还有希望和转机。
他也是理性、现实的,坦然地说:愿意和中共一同推进民主。别人这样说,很有可能“里外不是人”;但陈子明这样说,人们相信他出自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代政治及民主路径的深刻理解。
陈子明以政治家自期,以推动中国自由民主为己任。无奈,铁窗、病魔与监控,将他的生命最后的十余年,定格在思想家的身分。他最终没有等来中国和自己的政治机会,壮志未酬。
法广:《殉道者》这本书,集中了他的朋友们缅怀他的文章?
高伐林:这本25万字文集,收录了他海内外朋友们深情缅怀他的文章,回忆了在国人争取自由与权利的各个阶段,他所扮演的核心或重要角色;也有一些是与他并不很熟识的人所写的,他们写出自己对他和他的思想的感悟。这本书中包括了中国研究院2014年10月28日,也就是陈子明去世“头七”那天,在纽约召开的追思研讨会的全部发言。这些文章都有血有肉,感人至深,不仅刻画了这位殉道者的一生,而且也以陈子明为脉络,勾勒了这40年来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变迁的缩影,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今人和后人深思的课题。
这本书的主编、中国大陆的著名作家徐晓,也值得一提,她是陈子明多年好友,陈子明生前嘱托她来主编自己的纪念文集。陈子明葬礼之后第三天,她摔断了右腿腓骨,随后她因另外一件莫须有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押了一个月,被取保候审后才继续编辑这本书。徐晓很感慨:我与子明,“与所有阴阳两隔的朋友们,这40年的经历,总是这样奇特、荒诞,甚至惊悚。难道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