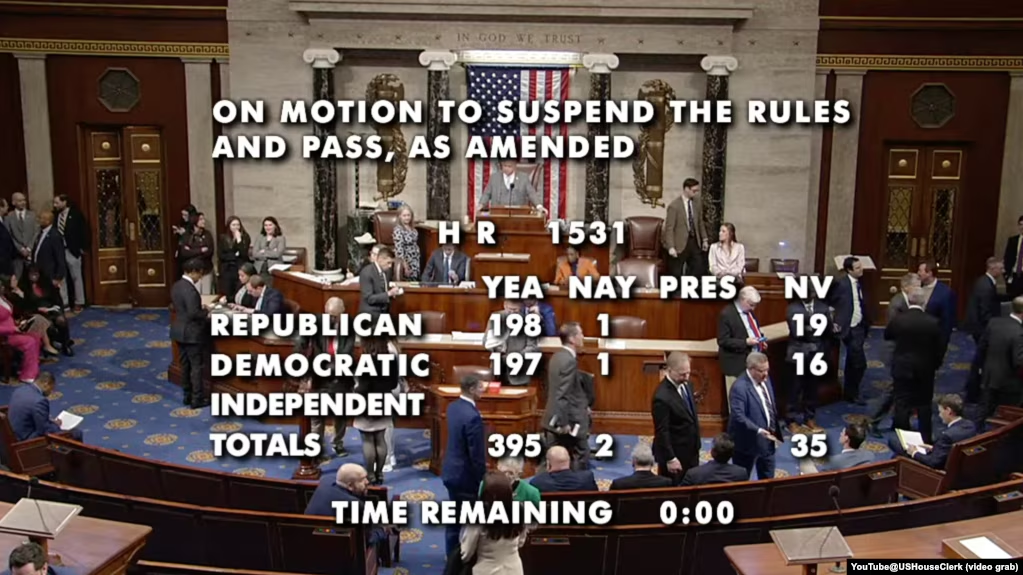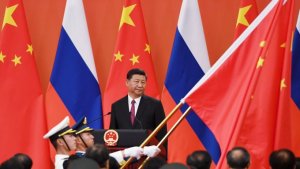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上个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内部自发地发起了一场名为“基督教本色化”的运动,希望中国基督教在组织机构上能够摆脱外国差会而自治自养,在传播形式上能够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的基督教。这一运动并没有当时政府的参与、也没有把某个党派的思想作为本色化的特征之一,它与目前被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所谓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运动有根本的区别,因它本质上还是一个非政治的宗教界运动。但是不幸的是,正如上个世纪初教会内部发起的三自运动最终被中共政权抢夺了领导权一样,目前方兴未艾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也被当局说成是当年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的关系,从而看清出这次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完全是为党国服务的政治运动、跟基督教本色化并无实质关系。
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旗手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就指出上个世纪初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为现今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铺垫了基础。他在《“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中写道:“赵紫宸、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韦卓民、丁光训、陈泽民等中国基督教领袖曾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有过许多构想和论说,这为我们今天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注:见2014年8月5日《中国民族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晓峰在其《基督教中国化如何开展?》 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为了教会的本土化、本色化做出了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尝试,其中涌现了赵紫宸、刘廷芳、诚静怡、张亦镜、吴雷川、王治心、倪柝声等一大批基督徒思想家。作为后来人,我们能够从唐代景教的所谓“中国化”、元代也里可温的非“中国化”,明清耶稣会士步履维艰的“中国化”,以及民国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本色化”努力中总结哪些经验呢?”(注:见2014年8月26日《中国民族宗教报》)由此可看出这些学者有意将其推动的当下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民国初期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联系甚至混同起来。
其实当初的本色化运动中并没有出现诸如大规模拆十字架、“五进五化”、“文化礼堂”等怪现象,而纯粹是从基督教内部神学、学术、文化上的一次本土化尝试。我们可以从赵紫宸、吴雷川、王治心等人的论述及实践上得到证明。
赵紫宸是民国时期著名基督教神学家,曾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長,他也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赵紫宸认为:“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国文化之内而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传可以将表显宗教的方式贡献于基督教”(见石衡潭《赵紫宸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及其融通实践》一文,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赵紫宸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基督教在中国自然不免要与中国文化作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创造宗教的术语,而借重中国的言词;第二要向中国的哲理伦理作一个去取对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评中国一阴一阳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挥写一个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在文字上要取雅达的成词,拨开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而吸取其精英。在哲理上要在天人一贯宇宙自然的道统上加上超世入世、超自然超历史的理论。在伦理上,要执着天下为公四海兄弟,定名分,行孝道的三纲五常,而加入人神的关系,上帝的命令,耶稣的新诫,以建立一个有宗教基础的伦理学。在历史上要指出自然主义不能保存价值,成全意义,而陈述一个以超历史成全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 (见赵紫宸:《从中国文化到基督教》,见《赵紫宸文集》第二卷第4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赵紫宸还亲自实践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他早期所写的《基督教哲学》是一部体现中国文化融神学、小说于一体的著作。他出版过赞美诗集《民众圣歌集》,采用中国民歌来创作赞美诗歌。赵紫宸编译的《《团契圣歌集》被世界公认为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一个里程碑。赵紫宸采用四种语体来翻译其:一是用古诗体如骚体来翻译,二是用绝句来翻译,三是文白夹杂的方式或说浅近文言来翻译,四是纯粹用白话来翻译。
可见,赵紫宸是在用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语言、音乐形式等与基督教交流互通,目的在于让基督教更好地在中国传播。与赵紫宸类似,当时的基督教学者王治心、吴雷川也从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出发来,来与基督教互通互补。不过王偏重于佛学、吴偏重于儒家思想。
王治心是民国时期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先锋,也是教会史学家。曾在沪江大学和金陵神学院任教职。著有《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宗教学者何建明、赖品超在《佛教對基督宗教在華的本色化的啟迪》一文中指出:“王治心先生是近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当中较早意识到佛教对基督教的挑战,井自觉地从佛教的中国化历史中寻找可以成为基督教中国本上化之借鉴的先驱者之一”(见台湾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一期2001年12月《佛教对基督宗教在华的本色化的启迪》 282页)
王治心在《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佛教在中国的趋势,庙宇式的迷信,果然渐渐地消沉,而居士派的研究,却一天澎涨一天,试观今日的知识阶级,十九都表示对于佛学的欢迎。因此,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的话:‘不研究佛学,
不足以传道’”(见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学研究》,1-2页)。王治心在该书中提出基督教虽然也讲忍耐,而佛教却在“忍辱”之后,继以“精进”;佛教对社会责任强调不够,但基督教“纯从社会服务上表现出来;所以基督教是社会的宗教,对
于社会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要促进社会的进步”。(见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学研究》,53页)。可见王治心强调基督教与佛教某些理念的互补。
同时,对于一些教堂建筑采取佛教寺院建筑的形式、礼拜仪制采取佛教仪式,一些基督教徒的婚丧礼节采用雇僧道念经的形式,如在上海的一些基督教教堂里,堂的正中是圣坛,旁边是讲台,圣坛用锅炉燃点沉香,焚香点烛,因为植香足以息人之杂念,定人之精神。礼拜之前每人必须在圣坛前跪待,讲道者着玄邑圣衣,圆领对襟长及踝骨等等现象,王治心特别指出:“这种形式上的改造,还不过是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接近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根本上的下种方法。因为基督教的生命里,没有中国文化的血液在内,则基督教与中国社会虽日趋于密切,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形式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为血液,庶几无所谓基督教中国,和中国基督教,这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了”(见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旅: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页238-239)。
另一位基督教本色化运动领袖人物吴雷川,清末翰林,曾浙江大学校长,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著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墨翟与耶稣》等著作。他强调基督教欲本色化必须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他主张基督信仰的精髓已存在于中华文化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信徒只要将其发掘出来即可。早在1923年,吴雷川推出了信仰与文化整合的观点,指出“道”与“教”的区别在于,道为真理,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而教则是宗教,儒教、基督教均为其中之一。道为本,教为末,后者彰显前者,故人们需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1924年,吴雷川又将孔子与耶稣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进行了比较,首先将孔子的宇宙观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曰天有意志;二曰以天道为自然,运行进化不息;三曰天道不能目睹,但无所不在;四曰天德是真诚无妄。而耶稣的宇宙观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与孔子的学说相吻合(见邸永君《翰林基督徒吴雷川》一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网站 http://www.cuaes.org )。
吴雷川也提出“尊崇基督教”并不会“贬损儒家”的看法。吴雷川觉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对中西两大传统的误读,一方面,对于宣传基督教的人士而言,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教方式影响,“误以基督教为唯一独尊,可以推倒一切中国固有的文化” ;另一方面,这一排斥本土信仰传统的偏识反过来又成为中国知识界攻击基督教的理由,被认为是“用夷变夏”、“非圣无法”。这些都形成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绝对不相融洽”的错误观念,吴雷川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彼此都没有深通对方的精义,却采取了“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主观做法。吴雷川也认为如果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国社会(尤其是他后来倡导的耶稣“人格救国”),那么也就是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具体而言,基督教的“人格救国”、“以爱为总纲”、“公义与诚实”等启发性的原理,可以参照和印证儒家的“普济群民,占溉后世”、“仁”-“爱”- “兼爱”和“诚”等改造社会的实践性理论,因而,“如果深体中国的国情,必要知道完成儒教,即是发展基督教。”(见梁 慧、柴燃恒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吴雷川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一文 维真网 http://www.regentcsp.org)
从以上对民国初年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的赵紫宸、王治心、吴雷川三人观点的简要论述中,我们看到当时运动的大多数领军人物是从学术、文化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也都从基督教如何更好地在中国传播此一善意立场,来讨论中国文化(佛教、儒家、墨家等)对基督教传播形式和神学理念的互补,他们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学术语言而非政治语言。
但是,自习近平上台前后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却完全是一场政治运动。正如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旗手、御用宗教学者卓新平在其《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一文中所说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非常简单,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其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问题……基督教中国化是对在华基督教的一种政治定位,即要根本解决基督教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同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化意义上的政治定位还没有彻底解决。比如说,我们今天谈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渗透时,其中很大一部分之所指,就是西方的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我们社会政治体制的抗衡,所要推行的是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我们坚持三自爱国运动,就在于其对基督教来说首先是一个政治运动,并不完全是一个教会自身的、内在的宗教运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和表态……基督徒在政治中的不同参与及其不同态度,正好说明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上乃任重而道远……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要强调中国化,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见《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七版《基督教中国化的三要素》一文、2015年3月17日、同见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
也正如天亚社中文网评论者吴莫言在其文《卓新平论基督教‘中国化’》一文中写道:卓新平指出:“‘中国化’的缘起,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宣教热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另一方面,基督教翻译和解释西方神学、《圣经》过程中,在不断推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型态;第三方面,在社会实践上,还和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教会团体甚至西方政府接触时,偏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三自爱国’运动奠定的政治立场、出现的严重‘开倒车’的现象有关,比如:基督教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不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配合的明显举动,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暗中引导下走‘西化’的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根本的矛盾”。(见天亚社网站 http://china.ucanews.com 刊登日期: 2015年7月8日)
由上可见,当前的这场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是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改造、修正基督教的运动,是执政党发起、操作,由国家机器护航,为执政党政治利益服务的运动。它虽然穿着学术、文化的外衣,并自诩为民国初期本色化运动的继承者,而实际上它与基督教内部的文化、学术、宣教运动风马牛不相及。可惜国内不少的牧者、学者、基督徒都被它所迷惑,有意无意地配合其继续在神州大地上肆虐。这正如马太福音7:15~16:“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发生的这次共产党及其政府主导、彻底政治化、旨在遏制和阉割基督教的所谓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根本不能与民国初年的本色化运动相比。如同民国初年教会内部的自治、自养、自传在1949年后成为了共产党党的教会、国家教会的代名词一样,我们要提防的是当局冒用本色化运动的名称,却行基督教共产党化、社会主义化和非基督教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