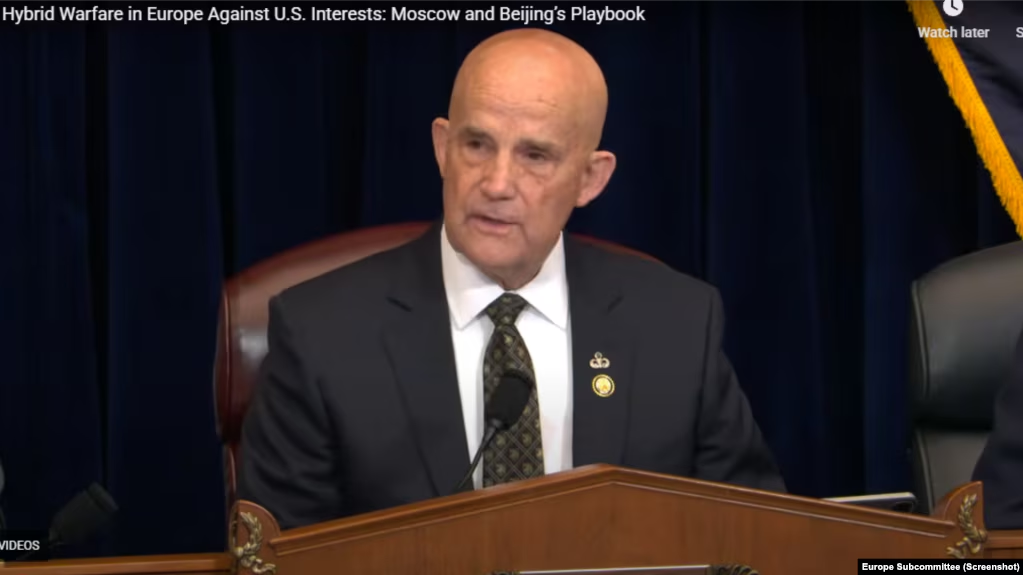2006年春节前,我再次见到难友方后高时,他已是七十有四的古稀老人了,半头的白发,满面沟壑,颀长的身躯也佝偻了。四十八年前我们同一生产队时的那位英俊少年,已经难觅踪影了。但当我们共同回忆起门口塘农场的艰难岁月时,我发现他依然是思路清晰,语言明快,还是少年时的愤世嫉俗和古道热肠。一别近半个世纪,我俩都老了,老人本该多说些欢乐的话题,免得再徒生许多伤悲。但是,我们毕竟是在那样非常时期结识的,他所在的无为县又是反右和饿死人时的重灾区,别看我们相聚时,正是春节将近,市场人欢马叫,处处是喜庆气象。但这表面的繁荣,依然掩盖不了当年运动连年,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有些人至今还在痛苦中煎熬。回避不是办法,一个强盛的民族,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应该敢于面对历史,认真处理好历史上留下来的问题, 还受难者一个公道。
这次我是衔命而来,我要为我那本已出版的小书《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做一些补充,要为一些基层小右派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做几分社会档案,给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供后人研究。后高兄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又古道热肠,对无为城乡情况都十分熟悉,是我这次无为行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他也乐以为之,我们的合作算正式开始了。(以下笔者简称“茆”,受访者方后高简称“方”)
茆:无为县虽说号称安徽第一大县,人口在百万以上,但偏居一角,交通闭塞。只靠几条等级不高的公路与外界联系,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突然声名大噪,为的是两件事:一是大跃进期间,无为县大批饿死人, 副省长张恺帆为解民于倒悬,毅然解散公社食堂放粮于民,被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点名;一是文革期间,无为民众为报无为恶吏县委书记姚奎甲,害死无为数十万百姓的深仇大恨,将姚奎甲装入铁笼中游街示众。结果装姚的铁笼在十字街心,被十余万愤怒民众用石块砸扁,差-点将姚砸成肉泥。此事当时名闻遐迩,大快人心,你家世居无为,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方:虽说那时我已戴上右派帽子,和你一起在门口塘农场劳动了。但家乡饿死数十万人,是家乡人最刻骨铭心的心痛。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当然说到饿死人,不能不感谢张省长,要不是他冒着丢官和坐牢的风险,毅然解散食堂,把口粮放还百姓,无为饿死人还会更多。张恺帆省长是我们无为人,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元老。他上世纪三十年代领导的无为六州暴动,是安徽省内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革命行动之一。但那次暴动中,很多老同志和无辜百姓牺牲了。张省长为此终身不安,常回故乡缅怀悼念老战友。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中,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芜湖地委书记杨明再到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推行一系列的极左措施:高指标,高征购,挖地三尺搜刮余粮,仅有的每日几两口粮,还集中在公共食堂里。再被大小干部和炊事员贪污侵吞,早已食不裹腹。随着劳动强度的加大,口粮日益减少,致使农民一批批饿死。张省长正是这时回到无为农村的。他的亲朋故旧,领着他一家家去看,不是有人饿死了,就是形容枯槁奄奄待毙,百姓们过了今天,还不知有没有明天,是一片的恐慌和绝望。死亡与挨饿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原来是鱼米之乡的无为大地。张省长面对如此的人间悲剧,悲从心来,深感愧对乡亲。他当时虽说是省级高官,但只是个副职,无权改变这一切,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解散食堂,把社员自己的口粮,发还给社员,让社员自己按计划食用。起码可以少一层剥削和浪费,从此无为饿死人的事大为减少。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张恺帆无为放粮和解散食堂事件。所谓放粮也就是把百姓的仅能度命的口粮,发还百姓而已,有什么错?但和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鼓吹什么“雷打不散的食堂”,什么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等宣传大相径庭。一时舆论哗然,直到惊动最高,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划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被捕入狱,还株连了一大片。可是在无为百姓眼中,张恺帆永远是为民造福的青天形象。现在历史的真面目,正在逐渐被揭开,无为放粮这件事应该尘埃落定了。
茆:这些情况我们都是熟悉的。(随着《张恺帆回忆录》正式出版,此事已有官方结论。笔者曾著文“大跃进安徽官场与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 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上)今天我们先讨论那场大饥荒,再说说游斗姚奎甲的事。
方: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那里政治运动极左,那里饿死人也最多。姚奎甲1955年才调到无为来,与无为人并没有什么恩怨过节。但此人骨子里就是个迫害狂,整人为乐,自诩为政治坚定,是全体无为人眼中的恶魔。虽说无为饿死几十万人,不能只追究他个人的责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条左倾路线带来的恶果。但姚奎甲心忒毒手忒狠蛇蝎心肠,所以无为灾难最重。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无为在姚手上打的右派最多,大部分送到我们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去了。在那里我们也受到了很多苦,饿死了一些人。但是比起全无为人受的苦,还是幸运一些,死的人也少-些。足见这场大灾难,受苦的不仅是我们右派,而是全体中国人!否则在笼游姚奎甲这个恶魔时,也不会那么万众一心,群情激愤!
茆:你说的很对,这笔帐总归要清算的,欠的债总要还的。今天我来无为,是想核实一下,你的老师李信鹏先生被饿死的真实情况。你们俩在无为中学是师生,反右后又同时被发配到农场,又同分在-个生产队,应该是最知实情的,他确实是饿死在挑粪的途中吗?
方:是的。我们那个农场所在地是广德县。宣(城)郎(溪)广(德)三县毗邻,都是重灾区,尤其是宣城,在册的饿死人数就达17万人。相比之下,那时的广德县,因为邻近江苏和浙江两省。同样在三面红旗照耀下,江浙两省领导,没安徽那么左,死的人要少一点。比如邻近我们门口塘农场的浙江省牛头山煤矿,因为是能源基地,物质供应一直较好,很多广德难民在那儿讨得了一口残羹度命,也包括我们农场的难友,当然,也就是积点肥料和买一点议价粮而已。
茆:我也到牛头山煤矿捡过粪,买过高价粮。不过你们作业区离牛头山更远,有四十多里地吧,一天能走个来回,还有时间捡到粪吗?
方:是这样的。受益的主要是你们赵家岗作业区的难友。那儿离赵家岗才三十多里地,你们去的又较早,开始矿上管得较松,你们积肥买高价粮都方便些。等到我们赶去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里到那儿有近五十里山路,走到时因为连日挨饿,四肢无力已是累得半死,积肥又是下了死任务的,最低八十斤,别说积不到这么多,积到了也挑不动。我的中学老师李信鹏就是饿死在积肥回家的路上。
茆:这件事我在农场时就听说了。他应该是你们罗家冲作业区第一个被饿死的人,您能说说他的情况吗?
方:他是我们无为一中的化学老师。浙江大学毕业。无为县城很大,有十多万人口,一中规模也大,有好几千学生。教师队伍反右之前是很棒的,有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大学生个个是宝,可惜反右一场灾难之后,很多老师被打倒,从此一蹶不振了。
茆:都说你们师生关系很好,最困难的时候都是相互帮助的。特别是您,在那样人人自危的时刻,还不忘尊师的古训,真是难得。
方:别说了,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我那里有您说的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其实我在无为一中读书时,可能未和李老师单独说过话。我当然认识他,他不一定记得我。李老师主要教高中部,我初中毕业考上芜湖农校就走了。毕业后回无为农业局工作,也没有和李老师打交道的机会。只是反右时共同罹难,又一起发配到这荒山沟来,又在一个生产队,当然就亲近起来。
茆:李老师我在总场卫生所时见过,瘦高个儿,斯斯文文的,虽说在干苦力活,但总是穿得乾乾净净的,一介书生模样。见到他时似乎总是在思索什么,像是话不多。看来批斗会的阴影,还在罩着他。他这么放不开,是很难熬过去的。
方:你见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在我们很熟悉的人群里,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人是群居动物,不能没有交流的,交流就要说话,否则人会被憋死。他虽然话不多,但看问题很深刻也很尖锐,依他看,在完成物质领域的所谓改造之后,事实上就是国家或曰执政党,已把全国财富收入自己囊中。接着必然要搞思想整肃,使其行为合法化,不允许别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叽叽喳喳。执政者大权在握,想怎么做都可以,只是搞什么阳谋引蛇出洞,手段有些—怎么说呢,不高明吧!不该是大国元首所为。再说整肃应该是针对那些大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与我们这些教书的,有什么关系呢?整到你们这样的孩子们头上,更是荒唐!要遭报应的!当然他说得没这么直接,有些话也听不懂,懂了一点也不敢乱猜乱传,那是犯大忌的。我知道他这么说,是他经过久久思索,才在较亲近的人之间,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一种宣泄,或一种自慰。但经李老师这么一说我的思想就要平静多了。他对我这么信任,我也很高兴。那时虽说他也才三十多岁,但体质瘦弱,从未干过农活。我才二十郎当岁,又是学农的,帮帮他责无旁贷。
茆: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有思想善思考的人,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啥也不懂,稀里糊涂过一天算一天,日子好混些。
方:也不尽然,还要看小环境。李老师和我们一样,也是被斗倒斗臭之后,才放到农场来的。早已有了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虽说体力弱一点,一般性的劳动还是能坚持的。情绪也还稳定,要不是劳动强度愈来愈大,口粮日益减少,应该说他是能熬过这一关的。当然,有些农活他是做不下来了!
茆:举个例子。
方:比如有一次施肥,本来从猪场挑来的半稀不干的粪肥里,有猪粪尿,还有未沤烂的死猪,活蛆乱爬,恶臭难闻。舀这样的粪已是受大罪了。可是那个红眼睛黑牙齿黄胡子的梁队长,硬说用粪瓢是修正主义,偏要我们用双手捧!那是人干的活吗?臭气近距离直冲脑门不说了,徒手伸进满是死猪烂肠子的粪桶里,大大小小的蛆虫,顺着手臂带着粪水,直往身上爬,能把人恶心死。我看到李老师直搓手,就是不敢往粪桶里伸,就轻声对他说,你蹲地上,就说肚子疼,你的任务我来完成。李老师总算逃过了这一劫。
茆:李老师最后还是死在挑粪的途中,终于没有逃过粪难!
方:那天的事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得是1959年深秋了,秋收结束了,按农业规律应该要进入冬闲季节。可是在继续更大跃进的口号摧逼下,劳动强度更大了。不问天晴天阴,每天每人要交100斤粪肥。而且要到牛头山矿区去挑优质的人粪肥。来回近一百里,还是去偷粪的,那里能说偷就偷的到!深秋夜长日短,那天刚亮,李老师他们十来人就出发了,天黑以后,才见到难友们陆续归队,积的都不多,多的也不过六七十斤。李老师和我一个宿舍,出发的人眼见一个个回来,依然不见李老师的踪影,我心中十分不安,一个个问同去的人,都说李老师还在路上,积的肥很少,一路上都是担惊受怕的样子,步履满跚,有气无力在一步步往前捱。我听了十分着急,眼看小半夜了,还没有人影,我预感大事不好,急忙向作业区领导汇报,领导要我邀几个人一路查找。果然在张家大庙附近的路上,见到了已倒地而毙的李老师。陪伴他的只有一条扁担两只粪筐和筐里还在散发出的粪臭。
茆: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没有任何过错,就这样死于非命!究竟是谁之过?听说一付薄皮棺材短短的,连腿也伸不直。
方:棺材是我找难友木工焦山长连夜钉的。我先找到农场领导,拿着批条找到焦山长。焦是位热心真诚待人的人,急忙四处找木料。场里确实存有几方大园木,焦说那是准备盖马厩用的,谁也不敢动。就四下找木板,长长短短厚薄不一的板料找了一堆,勉勉强强拼凑成一付薄皮棺材。可惜短了,不到一米六长,而李老师身高在一米七以上,入殓时真费了很多事。头是低着的,两腿是蜷着的,还是一付低头认罪,两膝下跪的姿式。真的对不起老师了,这也算入土为安了,总比曝尸荒野,任狗啃狼拖好吧!
茆:也亏得这个特殊的姿式,二十多年后,你才和师母一起,从一片荒芜的乱坟岗上,找到了老师的遗骸。当时也未通知家属吧!
方:还不是和你们赵家岗作业区一样。死个把右派,和死个小猫小狗,没什么区别。当时的说法是避免扩大影响。给老师装殓时,我还是把他最珍爱的一件皮背心给穿上了,使他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胸前多一点暖气。
茆:真难为你了。听说你还为老师立了个碑,为这事还开了你的斗争会。
方:家属未来,中国历来有师徒如父子一说。那时形势十分严峻,农场四周每天都有农民饿死,农场的口粮正日渐减少,今天李信鹏饿死了,下一个还不知是谁?我们那时还是单身,那一天走了,除了父母哥姐,没人为我们牵挂。而李老师是有家室的,他的老婆孩子总有一天,要来寻找亲人。我要活着,还能帮帮忙,如果我也饿死了,谁还能记得这块墓地呢?说立碑是夸大了,我只是在山上找到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没工具,就用一根大铁钉,凿成几行字,因为不知道李老师生年,只凿了:殁于一九五九年十月 李信鹏老师之墓 学生方后高立。
记得刚把石碑埋好,当天晚上就开了全作业区的批斗大会。说我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阴谋反攻倒算,是一本变天账,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但要把我批倒批臭,还要对我加重处理,以杀一儆百!那万炮齐轰的火力,一下就把我打懵了,什么加重处分,不就是送劳教劳改吗?这个作业区已经送走了好几个了,听说很快就饿死了。我要是也被送去,还有我的活命吗?我才二十几岁呀—-想到这里,我全身冒冷汗了,腿肚直打颤。那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要是想到了,借个胆子给我,我也不敢!不能老师饿死了,再搭上我这个学生—-
茆:是右派“君子”徐毅给你解的危吧?
方:是的!在大批判中发言的,都是在落井下石,有管理人员,也有所谓的难友。能明哲保身不说话的,已是很难得的了。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恨他们。都是运动作的孽,谁都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就得随着大流走,轮到我算我倒楣,恨谁也没用!那里想到在这种气氛下,居然还有难友为我说话!徐毅当时只说了几句话,语调平和,声音也不高,但全场马上肃静下来了。徐毅说这是件平常的事,方后高又没有说他永垂不朽,又没有说他有什么丰功伟绩,称李信鹏为老师,自己是学生,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说错。石头上凿几个字只是个记号,免得以后家属来找不到地方。依我看没什么错!徐毅这么一说,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同主持批斗会的人,在这样常识性的浅显道理前,都无话可说了,匆匆收了场,我当然松了口气,心中对徐毅的感激与崇敬,一时不知怎说才好。
茆:你和徐毅平日不怎么熟吧!
方: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平日很少打交道。但我们知道他是13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的红小鬼。知道他是反赫鲁晓夫划的右派,知道他正直正派敢说敢当, 常为受难的右派难友仗义执言。有时连管理干部也有点怵他。平日我们就尊敬他,这件事之后,我们就视他为“君子”了。他一直身体不好,患过肺结核,听说曾因大咯血,住在你们科里,现在还好吧?
茆:我也有几年未见到他了。他是在宣城县副县长位子上离休的。还住在宣城,身体还好。他是个豁达的人,曾开玩笑说,他反右之前就是副县,离休时还是副县。从做官角度看,他不算是成功人士,但从做人的角度看,他应该是极大的成功。在那种是非颠倒人妖混杂的乱世,作为难友仍能受到他人君子一般的崇敬,不是几句话几件事就能使人信服的。所以文革初起,我们这批难友之间,有人挑起事端,妄图借陷害徐毅陈炳南等人保全自己,你毅然过江而来,找到始作俑的小张,你也不怕惹火烧身?
方:怎么不怕?不过小张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文革前他有一天到无为来,我俩逛街,在新华书店他看到了郭沫若新出的诗集《百花齐放》。他越看越气,拿起笔在书上写了一通,又放回去了。我当时未留意,不知道写些什么。小张第二天走后,我想想不放心,又回到书店找到那本书,一看吓坏了!原来小张在书中写了几句话:狗屁不通!吹大牛,无耻!这样的书,要是落到别人手里,还不是铁证如山的罪证?我当时不动声色地把这本书买下了,藏在家人不易发现的地方,未和任何人说起过。因为这只是小张一时义愤,信手写来,其实和我们观点没什么区别,当然我永远也不会告发他。忽然听说小张居然挑衅,要整徐毅和你们这些好友,我疑虑重重,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过江来找到小张,问他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而致难友相残。我特别提到徐毅,说徐对他一贯是很爱护的,为何翻脸不认人?你猜小张怎么说,他说徐毅真的有问题,说徐多次赞扬于谦,于谦是明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那不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吗?我一听气坏了,看不出小张进步可真大,成了真革命派了。我说我不和你辩论,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我从包里拿出了郭沫若那本诗集,翻到他写评语的那一页。小张一看顿时傻眼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把书往包中一放,对他说你脑子清醒点,这可是白纸黑字,比道听途说管用多了!说罢我转身就走了。这件事你们芜湖的人,没一个知道,我不说小张肯定不敢说。当然,以后运动转移了方向,改斗工作组走资派了。不然真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
茆:不说了不说了!说来叫人丧气,我那本书为小张专写了一章,写他我心情是很沉痛的,为什么相濡以沫的难友,会反目成仇,究竟是谁之过?你还是继续说说李老师的故事吧。农场解散你们回到无为,还能经常见到你的师母吗?还谈起过李老师吗?师母提过去寻找墓穴的事吗?
方:回到无为我们日子都不好过。我是摘帽右派,她是右派家属,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偶尔在街上遇见了,也只点点头而已,能说什么呢?更别提寻墓的事了,那叫右派翻天!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极为亢奋地站在街边,一改多年来灰头土脑低眉顺眼的形象。
茆:那是1979年右派改正之后吧!
方:不!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斗走资派时期。你知道的,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在无为干尽了坏事!饿死了二、三十万人,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为老百姓恨死他了!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了,但还是安排他当了芜湖造船厂的头头。老百姓再恨也拿他没办法。文革开始,本来又是一次整人运动,抓牛鬼蛇神呗!那里想到还会有群众斗领导的事。就一个县来说,居然敢把最高的官,抓出来游街示众,真是造反了!无为百姓最想斗的是谁?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几个造反派头头,过江到芜湖来,揪姚回无为批斗游街。这件事在当时也很平常,到处都在游斗工作组和当权派,都在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办事。很多地方也就是走过场,大家心里清楚,共产党的天下没有改变,运动来了,大轰大嗡一阵子,过后谁干啥还得干啥,官还是官,民还是民,乱不得的。可是游斗姚奎甲就不一样了,无为人对他有血海深仇,二、三十万人不能白死,他们的亲属子女还在,他们会忘了这笔血债?几个造反派头头犯难了,他们清楚,如果只开几次现场批斗会,多组织些力量,还能控制局面。游街就不一样了,单县城就有十几万人,四乡八邻一定还会有百姓赶来。大家都是报仇雪恨心里,群情激奋起来,那场面是无法控制的,出了意外咋办?按说无为饿死二十多万人,换他一条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饿死的人和直接被杀死的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再说一项全国性的决策失误,仅追究地方官员,也不是公正的。当时全国到处如此,姚奎甲只是更左一些而已。可是百姓们不会想的那么多,他们只知道是姚当书记,饿死了这么多人,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什么事干不出来!几个头头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用个铁笼子把姚奎甲装进去再游街,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事后证明,果然是好办法,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茆:要不然十个姚奎甲也要被石头砸死了!这件事当时传的沸沸扬扬,我们在江南都听说了。它反映了民心的向背,和载舟之水也覆舟的常识。你也一定在现场,能给我说得详细一点吗?是不是就是那天,你看到李师母他们也神情亢奋地站在街边的?
方:是的,就是那天!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对李师母一家来说,李老师死了,就像家中顶梁柱倒了,从此寡妇孤儿只能苟活了。对我来说二十来岁,突遭横祸,从此沦为异类,受尽屈辱与磨难。而给我们带来厄运的,正是这个姓姚的在无为当政期间。面对这个恶人,怎能不怒火满腔,恨不得上前煽他几个耳光。但是,我和李师母都是历经磨难的人,也清楚自己的身分,不想给自己以后找麻烦,只能当旁观者。不过即使是旁观者,那天也吐了一口郁闷在心中多年的恶气。那场面你是未见到,见到了终身也忘不了。我们经历过的运动可谓多矣,哪一次运动不是领导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山呼海啸,群情激愤。可是谁都知道,所谓群众运动,实乃运动群众也。什么激情什么义愤,都是为了运动的需要,而调动起来的。除了少数别有所图的人,绝大部分群众都是盲目的,只是运动中的一粒棋子,任人摆动而已。
而游斗姚奎甲就不是这回事了。那是百姓自发地向这位一贯推行极左路线,从而给无为百姓造成极大伤害的统治者讨回公道的日子。所以游街的日期一公布,那天全街道早早地站满了人,有县城的,也有从很远的乡下赶来的。大都表情严肃,有的眼里还饱含泪花,一定是想起亲人惨死,而情不自禁。当然也有看热闹的,但为数不多。就算是百万人口的大县,一下子饿死了二十多万,有几家能幸免于难!所以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在街道中出现时,全街道顿时沸腾了,一片打倒之声,向姚奎甲讨还血债之声响彻云霄。这些都是事前估计到的。
但是,很快,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人群中有人用准备好的石块,向姚的铁笼车砸去,一人开了头,只见街两旁的人,一拥而上,纷纷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边砸边喊,声震云霄。也有捶胸顿足的,也有掩面而泣的,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终于掀起狂风巨浪了。多亏笼车是铁的,而且很坚固,就这样也被砸得不成形了。车内的姚是吓得尿裤子了还是昏死过去了,只有近前的人才能看到。可以想见,那天要是不装进很牢固的铁笼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酱!就是那天我看到了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亢奋地站在街边观看,他们也一定看到我了。因为人群都拥向了笼车,我们是少数没有行动的观望者。其实我们和大家心都是通的。
茆:这件事应该写进历史!单写进地方志还不够,应该写入正史,最好在无为街头,立一个百姓砸姚笼车的记念碑。使世世代代万古千秋的执政者,都应该知道百姓不可侮,民心不可违的浅显常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百姓才是头上天!谁胆敢违背民意,下场可能比姚奎甲更惨!听说保了姚一条命的造反头头,清队时还是挨了批斗。
方:那是必然的。不过明知要被秋后算账,而且姚罪恶再大,群众组织也不能把他定罪,到头来还得自己吃亏。尽管如此,能有一次向姚这样的人,施行报复,还是会不顾一切去干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是二十多万饿死者的冤魂啊!斗完姚奎甲之后,一切还是老样子,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好说的。要是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为我们改正了,那到今天我们还不得像贱民一样苟活着。无为饿死二十多万人的事,也将永远被尘封着!
茆:笼游姚奎甲,算不算民间文革的一种形式呢?有研究文革的学者称,文革有高层与低层两种形式。高层是毛泽东为报七千人大会一箭之仇,不惜绑架全国,发动的权力斗争。但底层确也有部分百姓在大动乱中,乘机向统治者发起反抗。
方:我们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只盼望当权者多给百姓办些实事,别总想着法子整人。狗急了也要跳墙哩,老百姓也不总是好欺侮的。载舟之水也覆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茆:我们都是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大饥荒时代的经历者和幸存者。我们忘不了,正是有一批批人牺牲,包括被饿死的人,才有后来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所以我特别敬重, 右派改正后你陪同李信鹏老师的遗孀,数百里寻墓一事。事隔二十多年了,你们怎么能在那一片乱坟岗之中,找到了李老师的墓穴呢?
方:说来真是话长。李老师改正之后,李师母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把李老师的遗骸迁回自己的故乡,与亲属子女长相守。而且她已经知道了,老师入土是我装殓掩埋的,还刻了块碑,要求我陪同前往。我也欣然同意,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总不能使自己敬爱的老师,长年埋骨荒野,成孤坟野鬼吧。
茆:无为到广德并不远,过了江芜湖汽车站有开广德班车的,要是赶上上午的班车,到广德转车,当天就可以到门口塘农场所在地:邱村。可是咫尺天涯,你们特别是李师母,二十年了,却不能到此来凭吊她日夜思念的夫君,向他倾诉作为未亡人的艰苦辛酸和怀念。你重新踏上这块埋葬了你四年青春的荒山野岭,也一定有许多感慨吧!
方:是的!我们赶到邱村时,已是傍晚,我把李师母安顿在小旅社之后,一个人在通向昔日农场的小路上徜徉。还是这个深秋,还是这个十月,还是晚风萧瑟,还是寒气逼人。那年是1979年,距李老师罹难正好二十整年!二十年啊!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却又是漫长的。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如果是一个清明时代,这二十年对李老师对我们都是生命力最旺盛时期,都是为国家为百姓效力的最佳年龄段。可是李老师却躺在一座孤坟里,逐渐化为一堆枯骨。我们活着的人,则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不清哪一天又是什么运动来了,被拉出去斗个七死八活,谁都可以羞辱你作践你。真的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恢复自由之身,还能陪伴师母来寻找李老师的遗骸。明知这是一件希望渺茫之事,我也得付出我的最大努力。
茆:确是一件极悲伤又极艰苦的工作,很难想象你们终于在几乎绝望时,发现了真墓穴!
方:确实是这样。所谓的墓碑,当然早已荡然无存。没了碑就和所有的无主孤坟一样,没有任何识别标志了。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地形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既是乱坟岗,就基本是无主坟,也就没人来祭奠凭吊和修葺。一眼望去,只见地形杂乱,荒草萋萋,坑坑洼洼。有些乱坟堆坍塌了,还能见到几根白骨夹杂在荒草与泥泞之中。是一片毫无生气的死亡之地。不是衔命而来,谁也不愿在此停留。
茆:李师母看到这么凄凉的死亡之地,想起和自己多年相濡以沫的丈夫,竟然归宿在这里,一定是无限悲伤吧!
方:那还用说吗?师母虽然刚五十出头,但抚孤成长,艰苦备尝,生活的重担精神的压力,早已把她压垮了。已半头白发,行动迟缓了。当天面临那一片肃杀的死亡之景,连走路都困难。就这样她也陪着我连连挖掘了两天。
茆:你们是一个一个坟堆挖吗?
方: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其实哪里称得上坟堆,因无人管理修葺,只是略高于地面的土包而已。你只能一个不丢地一排排挖过去,用所谓地毯式挖掘,事后你才不会后悔。其实干这种事心里挺虚的。中国人最忌被别人挖祖坟了,那是对一个人也是对一个家族最大的侮辱。这里虽说是乱坟岗,都是无主坟。但都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们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力惊动他们呢?所以干这种事时,我一直有犯罪感,每一次都小心翼翼,只要挖开茔地,见到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都是祈祷式的念念有辞:请不要怪罪,我们要找亲人,不得已惊动了你,我一定原样修复好,再多培上几锹土,让你安息!百姓都认为这么做是犯了阴气,于人是十分不利的。收工时我目测了那块乱坟岗,不过动了不到五分之一,按这个速度,那还要五、六天。我虽不迷信,也自认为是在做善事,起码我这么辛苦,决不是为自己谋一点私利,想到这里我才少了些犹豫与恐惧,也坦然多了。但对能否找到墓穴,还是毫无把握。
茆:第三天你们还是原样一排排挖过去吗?
方:按说也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不过第三天一上工,我在乱坟岗上转了一圈,目测了一下哪里离我们作业区最近。虽说准确位置找不到了,但大方向是不会错的。所以在那认为离作业区最近的地方,转来转去。果然,隐约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官吧!所以第三天我们换了一个起点开始挖。
茆:果然是第六感官帮了你的忙?
方:哪有那么神奇的事。第三天和前两天一样,从太阳刚出山,一直干到夕阳西下,还是一无所获。不过没有第一天失望,似乎可能下一个就是。这时人的体力实在支持不下来了,那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李师母也过意不去了,连声说回吧,明天再说。不知为什么,我脑海里突然萌生这样的念头,成败就在今天,今天再失败了,明天就可能累得起不了床了。就对师母说,太阳还未落山,再掘几个试试。果然,掀掉第二个坟堆的土层,就可见到长短宽窄不一的白茬棺木,正是我和焦山长一起钉的那一付!木材是腐朽,一碰就烂了,但形状不会变。我连声对师母说,找到了!找到了!我马上开棺了,你最好站远点,免得受不起这个刺激。师母哪里听我的,恨不得上前用手扒开棺木。她想象不出,那么鲜活的一个人,学问好,品德高尚,一直受人尊敬,没有任何过错,开过几次批斗会,人就被送走了。走时是四肢健全,思维敏捷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大活人,现在要见到的却只一堆白骨。究竟是谁给人间带来如此的悲剧?这一切岂能就“改正”二字便打发了?
茆:撬开棺木时,还是原先装殓时的体形?
方:那还能变得了?只是一切有机物都消蚀干净,归还给茫茫大地了,连同那件轮廓还依稀可辨的皮背心。留下的只是依然低着头蜷着膝的一付白骨架。李师母一见到她日夜思念的亲人,竟然是这么模样时,立即昏过去了。剩下来的拣骨和装袋工作,都由我一个人完成了。翌日我们便匆匆赶回无为。遗骸是被拣回来了,但生命青春连同屈辱恐惧疲惫和挨饿都永远丢在这荒凉的土地上了,一同丢失的还有夫妻恩爱,阖家团圆的渴望,和重返课堂重执教鞭的本不是奢求的梦想—-
茆:一同丢失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处,和对宣传与口号的激动,乃至对当时执政者的信赖—-
2006/4/4于广州 2007/7/13改定 2016/3/10定稿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