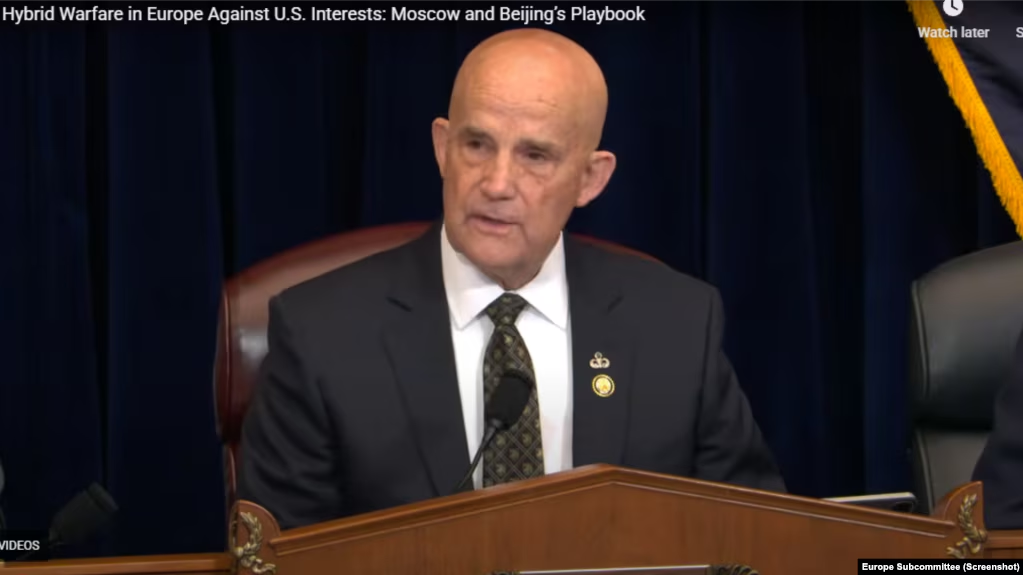北京消息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公开发表“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4月4日《信息时报》)
信访制度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它的主要功能是充当“社会安全阀”,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巩固并使现行政权或体制合理化和合法化。虽然主流话语一直宣称,信访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体现群众疾苦的重要途径”。然而,不论哪一级政府都不太欢迎上访者,因为他们的到来就好像在华丽的官袍上泼了一瓢令人掩鼻的粪水,同时又像呈现到一位因某种原因不愿或不敢照镜子——甚至对镜子过敏——的人手中的镜子,其令人不快也是非常自然的。
上访的人大部分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或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到上级行政部门“告御状”无非就是为了维权或申冤,向政府要求——甚至乞求——本应该属于自己的社会公正,因为司法渠道的不畅通或高成本,使他们的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合理的和及时的解决。当然,也并不排除少数人是无理取闹,或者像孙东东所说的“精神有问题”,属于应该被“强制医疗”的“偏执型精神障碍”。另外,政府部门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往往过度宣传或渲染了信访的“神奇功效”,也会误导了一部分民众,使他们以为信访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或正确的途径,从而更愿意通过信访——而不是司法——的途径,来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人际冲突。还有一些上访者则纯粹是“为上访而上访”,甚至将之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因为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掩盖某种真相,或为了息事宁人,会对他们的每一次上访都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总之,上访者是现行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无法处理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废弃物——一方面不得不以信访作为现行体制之缺陷的补充,以维持体制本身的稳定;另一方面却将上访者定义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千方百计阻止上访事件的发生。在接访部门,上访者意味着无穷无尽且令人难以忍受的工作量,而在被上访者投诉的部门或个人,则意味着政绩上的污点、即将曝露的丑闻、不确定的个人前途或政治风险等等。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甚至不惜花费高昂的成本(当然是纳税人的钱),采用截访的手段,把上访民众拦截在中央或上级有关部门信访登记之外,并强制带回原籍。
不过,这下好了,作为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和北京大学教授的孙东东通过将99%以上的令地方官员感到头痛的“老上访专业户”定义为“偏执型精神障碍”方式,为他们的截访提供了另一种合理合法,且不容易引起民众非议——甚至可以美其名曰“为了上访者自身的利益”——的完美的处置方式,即“强制医疗”。而且,按照孙专家的解释,就算思维很清晰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被命名或被定义为“精神病人”——“因为大家对精神病有误解”。如此这般,以后只要有“专家”和“精神病院”两种“硬件设施”,我们国家的很多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真的是“不亦快哉”呀!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的序言里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孙东东教授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表面上是指“老上访专业户”,其实却暗示所有的上访者都是潜在的“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这一事件真可以算得上是福柯理论的完美注脚。
上访者与上访行为的大量存在,其实是由于缺乏制约的权力的恶性膨胀和疯狂扩张而引发的种种社会不公所生产和制造出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混乱、无序的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产物——同时,也被冷酷的专家们定义为诸如“偏执型精神障碍”之类的 “废弃物”。
上访是遭受社会不公的民众要求与政府、与权力进行对话的一种诉求,“老上访专业户”的存在表明这种对话被无限期地忽视或延宕了,而将上访者定义为“精神有问题”,则表明这种对话关系的彻底破裂——从此,上访者成了不折不扣的“废弃物”,不得不将自己置于专家和精神病医生的理性审视下,并以自己的“疯癫”来确认其他人的“神志健全”。
帕斯卡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至少99%以上的“老上访专业户”变成了“精神有问题”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