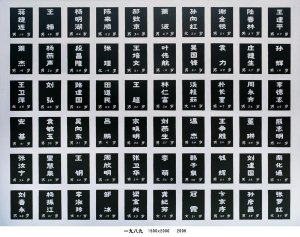《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終極版問世,這是2021年7月。100年前的7月,一幫匪徒成立了他們的黨,從此,人類的災難像雪球越滾越大,逐漸鋪天蓋地,看似不可收拾。終於,他們用烈性病毒挾持了全人類。
往事如雲湧上心頭。我想起2005年深秋,藝術家高氏兄弟向我引薦了第一個六四暴徒武文建,他的面部扭曲,憤怒、淚水和獰笑持續了幾個小時,他一口一個“你們他媽的”——“我們他媽的怎麽你了?”我反問——他答不上來。高氏兄弟代答:“他們他媽的憋壞了。”

我想起2003年丁子霖委託我探望被刺刀捅死在街頭的吳國鋒的父母。臨近告別,割掉了一個腎的吳國鋒的爸爸說:“千萬不要把我們家的情況告訴丁老師!我們倒下沒關係,她不能倒下。她倒下就沒人知道我們了。”
我想起出獄十幾年,每晚長跑五公里,王怡追問為什麼,我答怕死。於是王怡寫了《廖亦武的肉體意義》。
我想起跟武文建在茫茫都市尋訪暴徒,一次次被拒絕,猶如在深海中摸魚,只能眼睜睜盯著一個個無名的坦克人消逝。我想起出逃那年專程去北京看武文建,他那麽窮困潦倒,卻突然間賣掉一幅畫,他居然要取一萬塊給我,嚇死我了。

我想起在西方一夜成名,在英語世界接連發表《吆屍人》《上帝是紅色的》和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佳评如潮,如日中天——而《子彈鴉片》英文版卻歷經周折,2019年才艱難面世——雖然美國《國家評論》以“你選擇鈔票,我選擇革命”爲題,2015年11月就全文發表了長達兩萬多字的《子彈鴉片》引言, 猛烈抨擊了全球資本和獨裁中國的可恥交媾及災難性後果: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all-you-want-is-money-all-i-want-is-revolution/?fbclid=IwAR00tI82nJ_2yRtlvVyuPq4dikrm642plvy4_AAeWa8Gws_8uBh3bUchspw

‘All You Want Is Money! All I Want Is Revolution!’
Before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everyone loved China; now everyone loves the renminbi.
www.thenation.com
我還想起自己對台灣讀者的偏見和傲慢,如何不重視母語版。想起2012年首次到臺灣,廖志峰陪了我那麼多次,我還沒心沒肺地編排旅館門外有鷄,床上有陰毛的“底層故事”打擊他的自尊心。
我想起最後這次,修訂了好幾年。余志堅客死於病重,劉曉波困死於謀殺,與我通信數年的蔣培坤突發心臟病,他和丁子霖曾寫下《送別兒子》,多年後,不得不由丁子霖寫下《送別丈夫》。
還有劉賢斌又出獄了, 他那篇10前年的記錄《出獄100天》,恍若幾分鐘前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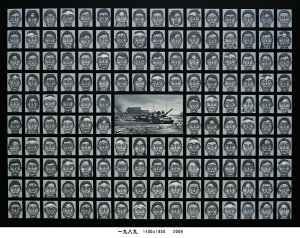
這是一場記憶戰爭,唯有在記憶戰爭中,我們的記憶才能與全世界的記憶交匯。唯有在記憶戰爭中,中國人、四川人、北京人、台灣人、猶太人、朝鮮人、新疆、西藏和香港人的記憶才能連接成一面阻擊政治謊言的哭墻,最後奪回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未來。
我相信他們完蛋之後,《子彈鴉片》將回到六四那夜反抗鎮壓的人們當中,它會像被猶太人傳遞的埃利 威塞爾的《夜》一樣,成為見證天安門大屠殺的受害者必讀書。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但你我死就死罷。
人終歸塵土,書終將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