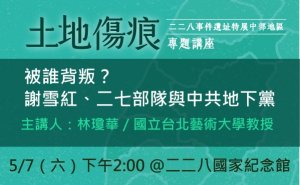
臺灣二二八與中共地下黨:
關於臺灣左翼史的省思
林瓊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二二八學」是不唯臺灣各學界都應探究的,也是身為臺灣人必須建立的認識臺灣的基礎知識。其中,最易被今日臺灣人誤解的,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投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地下黨」或「省工委會」)的臺灣左翼人士。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歷史脈絡是密切相連的。許多在白色恐怖時期有意識地投入地下黨的反抗者,正因經歷二二八而對原來「白色祖國」的國民黨政府從滿懷希望到失望,乃至完全絕望後,因而投入有組織的反抗行動,希望能推翻這個屠殺同胞的「統治集團」 ──這個動機及決定採取的行動,無疑將使他們的生命進入死亡的陰影中──而究竟當時臺灣面臨甚麼樣的社會境況,會使這些人抱持認定的價值而願冒險赴死呢? 這是反思當時的中共地下黨問題首先必須探究的重要課題。
即使已進入廿一世紀,國民黨自2016年第一次在戰後成為立法院的少數政黨,民進黨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以來已連續完全執政兩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結束了2018-2022為期四年的工作,但由於加害體制乃至其處置方式仍無法進入公民社會意識及相關討論中,當今大眾對戰後臺灣社會究竟在二二八過程中經歷如何天翻地覆的創傷與劇變的過程,事實上仍不甚清楚,或說關心的社群比例依然有限。 在這樣客觀的困境上,溯因自1949年開始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及同時進行的黨國反共教育,加之現實上中國對臺長期文攻武嚇,尤其近年海空聯合軍事演習的威脅,確實使不少人一聽到「中共」便難以冷靜,情緒上的反感,更使人無法產生理知動機,進入當時島嶼歷史脈絡和社會情境省思箇中緣由。1950年韓戰爆發,原已對國民黨收手復又納於反共陣線中的美國所帶來的影響,對臺灣被盟軍規劃由「中華民國」軍事佔領而身不由己的狀態,都是理解臺灣有志尋求自主之路的反抗者投入行動的背景脈絡。這群希望推翻國民黨惡政的臺灣反抗者中,確實有不少人受到社會主義裡公平公義思想價值的吸引,與已和國民黨有豐富交戰經驗的中共具有共同的、推翻國民黨的政治目標,也因此現實上的合作並非偶然。雖然前者在現實情境上有挽救淪喪中家園的急迫需求,後者則志在一統江山,欲透過這些臺灣在地黨人完整其紅色國土。而姑不論臺灣行動者們對左翼思想與理論是否嫻熟或認同,能使國民黨在臺灣的治權儘快停止、消失,正是雙方第一個有力的合作動機。
如今看來,在現實中已長期被中共恫嚇的臺灣,歷史政治的正義也尚未從被迫必須在島上共存的中國國民黨得到真正具體的償還,但這兩個紅白中國政黨對臺灣思想視野的侷限和綁架,無疑地使臺灣處於雙輸狀態──不僅現實中扮演「山寨版中國」的臺灣在主體性上備受傷害,左翼價值的缺席,更使人們對一個更符公平分配價值的民主家園缺乏想像。社會主義思潮曾是三十年代世界性影響各國知識分子的國際思潮,臺灣在當時也並未缺席,即使1931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社運之後,經歷十多年的寂靜,但這股火種並未完全熄滅,在戰後歷經二二八之後死灰復燃,且從二二八初始只有七十多名成員的單薄規模,繼而迅速發展,在白色恐怖期間增加到全島各地多達兩千人的組織勢力。
更令人驚奇的是,其中成員廣含社會各階層,從知識分子到工農大眾皆有之。包括醫師、教師、藝文人士、青年學生、原住民村長、佃農與勞工等,這些投入地下黨的臺灣革命者,因二二八的衝擊而對白色祖國絕望,在整個社會已被國民黨武力屠殺、鎮壓後,他們成為這個社會的秘密反抗者,透過組織行動希望推翻這個佔據家園、屠殺人民的暴力政權。而吸引他們的進步價值,可以「新民主主義」所揭舉的人民民主精神和社會平等目標為代表。此時在中國土地上的國共戰爭仍持續中,中共也正處於推翻國民黨的作戰狀態,它可以提供給臺灣的除了實質組織策略、財力、軍備等,是非常實際的客觀資源和條件。如果沒有從國民黨政府自1945年之後的一年四個月對臺灣社會造成的衝擊與震撼作為背景歷史的認識,繼而看見二二八爆發後這個「統治集團」如何派遣軍隊來臺進行殘暴的血腥鎮壓、沒有認識當年社會陷入的破碎與黑暗有多深,便無法體會當時為何會有士農工商各階層高達兩千多人,願意提著自己的頭顱,紛紛投入推翻這個不義政府的行動裡。
我們必須回到歷史脈絡裡認識此一哀慟的場景,才能避免跳接地從今日現實的中共侵臺行為去汙名化當年這兩千多位臺灣反抗者。
戰後歷經白色恐怖殺戮的臺灣社會,長達38年的黨國戒嚴體制中,在歷史教育中被清洗得最徹底的──即使在民主化之後的臺灣,除了二二八中的武裝反抗者,就是紅色的社會主義份子; 歷史上對獨裁統治反抗最力的,永遠也將是成王敗寇邏輯下被高度消音的對象。考察中國國民黨在二二八爆發前的社會已近乎崩潰的政經狀態,乃至陳儀政府如何玩弄兩面手法欺騙臺灣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暗地聯繫蔣介石派兵鎮壓、屠殺臺灣的殘酷,便難以理解這些嚮往紅色祖國的臺灣人當時心中的決志與悲憤。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從目睹自身親友、鄰人成為二二八冤魂的哀痛經驗中覺醒,進而遁入地下成為行動者。
即使今日諸多檔案出土,讓我們看見白色恐怖過程中灰階、複雜與軟弱的人性眾相,譬如在《鹿窟案》中牽連無數村民的的地下黨人,在「投誠自新」後保全性命,甚至位居高職、安養天年,而村民中無論是否具左翼理想者,所判之刑都比這些背叛同志的幹部更重。但即使如此,綜觀在冷戰背景臺灣白色恐怖下的左翼運動,仍無法以其中的個別叛變者與演變成壓迫者或罪犯的這些少數人, 來汙名論斷為數相對更龐大的,確實未能推翻國民黨政府獨裁統治而犧牲的這群歷史行動者。
曾群芳先生,當年正是上述歷史脈絡下的一位倖存的左翼青年。他在二二八爆發後加入地下黨,創立學生工作委員會臺大法學院支部,並從任職的臺糖公司轉任產業支部與第五街頭支部,協助《光明報》的編印與發行工作。在蔡孝乾於1950年初投降後,開始展開近兩年的逃亡,足跡遍布全島各地。雖幸得兄長與相關法政人士協助而脫險,但長期被國民黨政府監控至動員戡亂時期結束,這段經歷也如同所有臺灣戰後政治犯,在長期戒嚴時代裡未曾向子女提及。一直到長子建元也在自己的青年時期投入學運後,才第一次開口說出左翼經歷的往事。這是歷史之神給予曾家與臺灣的恩典,不僅讓建元有機會記錄了父親的歷史,並以各種方式為臺灣流傳這段左翼史。
缺少左翼史的臺灣史是不完整的歷史。無論從歷史或現實而言,臺灣社會都應從中國共產黨的恫嚇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思想箝制這兩造的精神綁架中解放出來,開啟自己對臺灣一個貧富差距最小的公義社會的想像和實踐,這也是在今天臺灣年輕人已無法在我們的島嶼孕育下一代的希望的此際,前人所留給我們的最好警惕與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