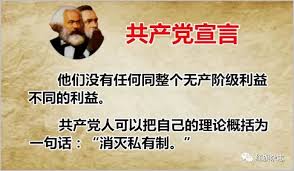第五十一章
民运人士安福兴 壮志未酬身先死
陈默和女友安然看到韩流过来,就推门进了医院。
韩流虽然与安福兴上次见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但这次见到躺在病榻的安福兴却是判若两人,北方大汉粗犷的大脸不见了,看见的只是瘦弱、苍白、颧骨突出的脸。双手的手腕都扎着输液的针头在慢慢的打着点滴。
安福兴的母亲告诉我们:安福兴是在三天前的晚上住的院。在此之前,他发了两天高烧,并且便血,直到他腹部痛疼得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才被家人强行送进医院进行抢救,但医生告诉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韩流和陈默找到主治安福兴疾病的医师张永胜,了解安的病情。医师张永胜说:安福兴患有肝炎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五年前他曾经住过一次院,但临床病症还没有消失的时候,他就出院了。出院的原因不用说,是经济问题。如果他上次要是好好的治疗的话,他的病不会恶化到这种地步。这次他来住院,当时我们就感觉到他已是肝硬化了,并且有腹水的可能性,只是当天晚上不能作检查。第二天上午,他的腹部就眼瞅着膨胀。经作穿刺抽水化验,腹水已经感染,并被腹膜吸收,导致腹膜炎。然而我们又不能把他的腹水抽尽,因为他的脾肿大并压迫门静脉。门静脉已经是曲张,腹水一抽尽,减压太快将造成门静脉血管迸裂,尽管如此,门静脉还是随时有迸裂的危险。门静脉曲张及腹水细菌蔓延再加上肠胃溃疡出血不止,这也是他便血不止的原因。
当他们问医师最后诊断时,他说:对这种多种疾病并发症,目前还没有下最后诊断。我们只能是根据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尽量的进行抢救,但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毕竟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有限的。他告诉韩流和陈默:安福兴每天用的人血白蛋白(每瓶450元)、立血止(每只50元)、血浆(每袋300多元)等昂贵的药品费用需要1000多元的支出。就是做一次胃肠消化道止血的治疗,就要花掉800多元钱,而且至少要做三次。别说他这样的家庭,就是有工作收入的家庭也是承担不起的。
几天之后韩流再次去医院,安福兴病情依然没有好转,仍然便血不止。他已经是七天没有进食了,甚至水都不允许多喝一点,仅靠打点滴来维持生命。然而这维持生命的点滴的费用,对已是债台高垒(借款10000多元,已经是所剩无几)的安福兴的父母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企求。难道在当今追求尊重、享有人权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的时代里,金钱真的成了决定他生死之间的要素吗?
望着脸色苍白、瘦弱露骨的安福兴,过去身高马大健壮的身躯好像逐渐给抽空了似的。过去那样一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不由自主浮现在韩流的脑海中。
在狱中安福兴曾经向韩流谈论走向民主之路的心路历程。
小时候在老师照本宣科的课本教育下,他热爱这个把他父母从万恶的水深火热的旧社会里拯救出来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让他出生后就沐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阳光下茁壮成长,让他生活在比蜜都甜幸福的家庭里。那时的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还有雷锋成了他心中的偶像,英雄成了他成长的指路灯,在英雄光辉形象的影响下,懂得了爱憎分明,知道了对同志们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每天都会睁大一只眼睛,时刻盯着隐藏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由于他的警惕性高,他有一天终于抓住了公开跳出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混入教师队伍中敌人,在课堂上,这个曾经隐藏的阶级敌人公然说什么:“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连人都饿死了。”老师拿着农村亲戚寄过来的信,在同学面前不断地颤抖着。对老师的胡说八道,安福兴可以说是义愤填膺,对于这样敢公然污蔑社会主义优越制度的家伙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他果断的毫不犹豫的举报给了警察叔叔,警察叔叔雷厉风行很快就把老师戴上手铐从学校里带走了,直到多年后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如今成了老态龙钟的驼背人在给人缝补鞋子。老师的悲惨境况,尤其他那驼背好像一个舞台,安福兴仿佛感觉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成为英雄的辉煌时刻,他的英雄情结在别人弯曲的驼背上耸立起来威风一时,却让人痛苦一生。那天在老师没有认出他之前,他心乱如麻身体发颤挪动千金重般般的脚步,走到老师跟前扑通一下跪在了老师的面前,泪流满面对老师说道:“对不起老师!”十多年过去了,老师没有认出他,面无表情的对他说道:“在荒诞的年代里,有几人不做荒诞事的,只要不一直荒诞下去就行。”
安福兴没有希望老师原谅他,在心里发誓不再做让人原谅的事情。自己过去对老师的所作所为,及目睹老师的遭遇,他从过去一个被严重洗过脑的人,在思想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啊,在那个时代有几个人不做荒诞事情,”韩流感慨的说道:“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你做的事情,上学时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好学生,每天早早的来到学校打扫卫生,实际上也就是到班级里擦擦桌椅,头天放学扫除后,桌椅落得都是灰,所以第二天早去学校把桌椅擦干净。有一天去的早,在开班级门的时候,有人用粉笔在门上写一个‘毛字’还打上了一个叉,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警惕性特高,别小瞧十几岁的孩子就能感觉出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派出所离学校不远,马上报告了警察叔叔。派出所有值班的警察,跟着我就过来的,那时学校还没有学生到校,我就和警察叔叔站在门口保护现场,不让陆陆续续到校的学生靠近门口。派出所上班的警察看到值班警察的留言很快骑着带兜的三轮摩托车过来了。过来有时照相,有时查地上的脚印,警察忙活了很长时间,学校让每个人在作业本上写上毛主席万岁几个字交上去。这事折腾了一段时间,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庆幸当时没有调查出结果,否则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想想真可怕,也真可笑,对一个不能有异议不能批评,想想这是多么恐怖的时代啊,所以那时造成的各种灾难层出不穷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但悲哀的是如今这种现象还是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出现,我们这代人如果在言论方面能拓展一下空间,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
“根除这种荒诞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的。”他出狱后也成了写作者,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判断的人。
“你总是那样乐观,不记得去年因写有关《诬陷是社会发展的毒瘤》的文章的结果了。”
“这能忘了吗。”老安笑笑了。
去年的一天早上,警察打来电话,让他在家等着铁城市公安局的警察来。一个小时之后,市局警察打来电话,让他到楼下大街处。当安福兴坐到警察开的车内之后,一警察对他说:“今天正式传唤你,带你到市局去。”半个小时后,安福兴被带到市公安局政保处办公室。
一个警察问他:“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安福兴说:“我不清楚,我的一切都是透明的。”警察说:“你最近挺活跃了。”他说:“你们的话,我听不懂。”“这段时间里,写了多少文章?”“不过就是一些回忆性及有感而发的文章而已。”“你知道,你的文章发表后,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混乱。?”“不过就是一些事实罢了,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你那篇有关89年的长篇文章,把共产党、政府写的多血腥!你这不是煽动,是什么?你最近写文章的面是越来越宽了,啥话都敢说了。”
随后一位负责人让一名警察给他作一个笔录,用他们的话讲,“给他积累材料”。于是,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进行讯问他的名字、个人简历、家庭关系等,并问他所写的文章的标题和内容及目的。安福兴告诉他们:“我写文章的目的,就是针砭时弊,希望能为消除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东西,尽点义务而已。”
最后,他们根据“网络监控”所下载的文章,询问安福兴,是否都是他写的。按他们所说的文章题目,安福兴一概承认是自己写的。他们倒是很“细心”,连他写的一首短诗也给下载下来了,不妨把这首诗抄录下来:
寻
——给自己
我不相信,你从梦里来会又回到梦中去
从一间黑暗房子到另一间幽暗的房子
从“母亲”怀里的黑匣子到大地上的窀穸
从悬挂在墙上的嘴到镜里照片的嘴
从浮萍追逐归宿的影子到蜘蛛遍地的足迹
从身怀绝技木偶的舞台到创造木乃伊荒凉的沙漠
从千古冰冻的河床到诞生鳄鱼的沼泽地
从芸芸众生的人群到茂密的原始森林
从这里寻找到这里,你没有在梦外出现
也许我注定从这里的黑暗走向更加的黑暗
也许我注定从重复走向重复
也许为了你头上飘起的旗帜
——我蔚蓝色的梦
我将再一次从这间带有铁条的房子
走向另一间带铁条的房子
1999年6月4日
等记完笔录,政保处的负责人对他说:“你违反了治安条例第15条第5款。这次我郑重的对你进行警告,下次再发现你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看见一篇,拘留一次,三次就教养或判刑。”最后,他们让他在一张写有“涉嫌撰写煽动性文章在网上发表”的传唤证上签字。
中午,他被允许走出公安部门。这是本月第2次对他进行“严重警告”了。自“6•4”前后,这是第5次把他带到公安部门进行询问了。
安福兴在经历过铁窗生活的折磨及无数次的警方向他发出的各种威胁都挺过来了,如今没有想到病魔无情地摧毁了他的身体,韩流不希望安福兴这样坚定的民运人士就这样离开我们。韩流向国家社会发出了呼吁,呼吁国际社会的有良知的人士及人权团体与国际红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伸出你们温暖的手,救救濒临死亡的民运人士安福兴先生。在韩流的呼吁下,很快收到了流亡在外的方励之先生、中国民主党海外党员庄彦等人的人道汇款。
几天后安福兴无力的手拉着韩流的手说道:“我可能真的是见不到黎明的曙光了,以后就靠你们努力了。”
“不会的,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你一定会在自由的天空下放声歌唱的,”韩流安慰着他,眼里的眼泪没有流出来。这时安福兴突然坐了起来,他张开大嘴一口鲜血喷到了侧面的墙上,喷在墙上的鲜血顺着墙流淌。韩流急忙起身出门喊医生,在走廊看到医生过来,韩流转身进屋时,安福兴又是张开大嘴喷出一大口鲜血在墙上,由于喷血的力量比较大,喷到墙上的血弹回来不少,他身上白色背心和病床上白色床单都是血。在安福兴喷出鲜血后,他无力的倒在了病床上。医生这时进屋来了,摸了一下脉,然后出门,不一会随他又来了两个医生还推着一辆装有医疗器械的小车,进到病房,一个医生把一根带有透视镜的止血管子从安福兴嘴里插进去,那管子挺长的,很长一部分插进他的胃里,插完管,医生看到韩流还在屋里,就让在病房门口走廊等着。
韩流在走廊等待着医生抢救的结果,抢救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医生出来说:“血不流了。”
韩流听到医生说血不流的消息,以为出血的地方止住了,当时听了还挺高兴的,但医生随后说句:“给他准备后事吧。”韩流似乎没有听懂,问道:“不是说血不流了吗?”“血不流了,是血流光了。”听了这话,韩流有些懵了,站在那里发呆。好一会才走进病房,安福兴的弟弟已经把哥哥身上的上衣脱了下来,身体白的跟白纸似的,但上身是血迹斑斑,韩流走过去,用毛巾擦拭他身上的血迹,他的身体还有热度,仿佛是在睡熟似的,好久没有流泪的韩流在擦拭他身体的时候,眼泪情不自禁的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们怀着极其悲伤的心情给安福兴穿好衣服。他们静静地在他的病床前站了好长的时间,总感觉睡醒后的他还会与他们去做所追求的事情。
这位老民运人士虽在经历了司法机关的迫害、家庭的破碎等种种打击的情况下,都没有让他倒下去,然而今天病魔却让重重的倒了下去,甚至是生命也走倒了尽头。
安福兴,1951年生于铁城市。大学文化,曾经在吉林市石化公司销售科工作。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与当地的一些教师组建“民主社会主义同盟”政治组织。为此,1990年1月被当地公安部门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逮捕。1991年2月被当地法院认定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判刑5年。在看守所期间不幸染上肝炎。1991年4月被送到千里迢迢之外的辽宁省凌原劳改营服刑,在狱中由于长年生活营养不足、有病得不到治疗及长期遭到监狱的严重的迫害的原故,致使肝炎病情加重。1995年1月被释放后,由于继续从事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导致原有住房被原单位收回,无家可归的他不得不面临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而且又不得不回到已过花甲的退休的父母(母亲没有劳保)家中,但不久所住的房屋被拆迁,于是他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尽管他为从事民主事业的工作而落得个一无所有及身患疾病的地步,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民主事业的追求,在1998年不仅为创建“人权促进会”积极的工作,而且不惜冒着再次坐牢的危险,为筹建中国民主党而奔波,成为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甚至在他身体不佳的情况下,为声援被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而毅然决然的参加百日绝食活动。
如今他在没有看到黎明的曙光时,他壮志未酬死不瞑目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