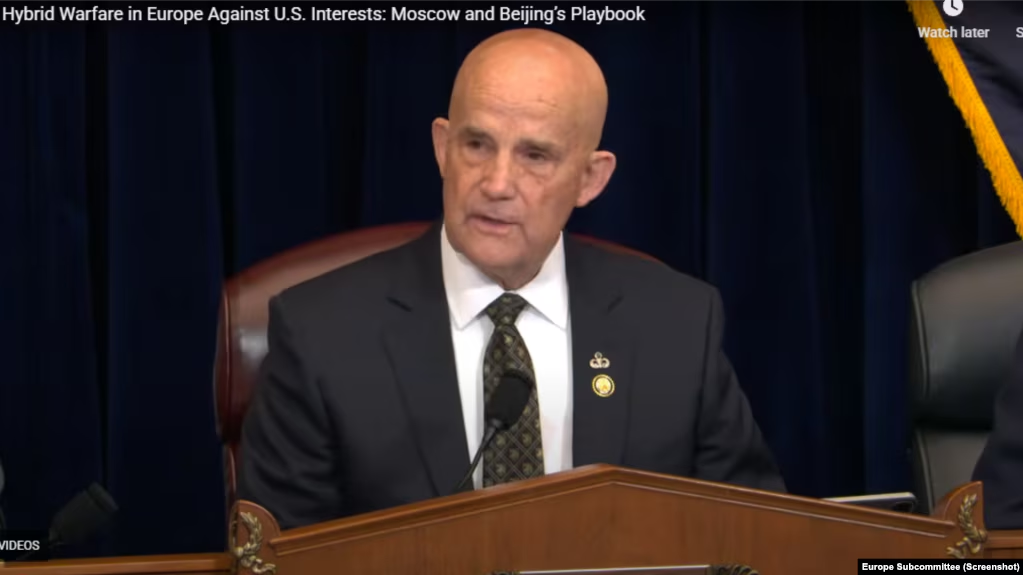(一)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天是是我手术的三周年。三年前的今天,我被切除了一叶肺,活检为谈之色变的癌。然后,又过了一年半,身患肾癌的老伴去世。我终于度过了算得上最艰难的日月。癌症预后,三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时间段。蓦然回首,三年一瞥。现在我体质状况很好,看来度过五年痊愈期是有把握的。我老伴是因为切除了一个半肾,后来癌细胞转移扩散,加上肾衰、心衰,还是熬过了将近四年,但其遭遇的痛苦,我是朝夕相伴,感同身受,莫可名状。人都希望长寿,但以度日如年的生理痛苦延长生命,并非幸福。
我的爷爷患肺病,英年早逝,大约在30岁左右,可能是癌症。父亲74岁,二弟57岁,都是肺癌,不过他们终身吸烟,我则反之,所以,一方面看家族病史,另一方面还要看其它条件,正面的,负面的,社会的,个人的,才能综合起作用。我却活过了76岁。
打右派是老毛的恩赐,得了癌症还活着是上帝的恩赐,都该感谢,否则我就写不出惹当局讨厌的文章了!
(二)健康长寿是人人追求的目标。此外,人各有志,人各有好,则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选择。回顾我这10年的经历与成就,则是10年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本来,在退休之后,只想到如何卒岁,如何了此残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还可以写出这么多的文章,应该是超过了百万字。
日前有一位47岁的研究鲁迅的教授来访,也只是匆匆一访。他是来山大有事,事情办完了,特地来看看我,说在网上,他凡见到我的文章,都要读,对他的研究启发很大。落坐不久,茶还没喝一口,手机频频响,催他吃饭,老同学要和他聚别,所以只算匆匆一访。又有一位兰州的陌生的朋友来电话。他83岁了,打过右派,是大学教授,还在上课,可见老而不朽,大概是位名师。给我打电话是告诉我,凡《往事微痕》上我的文章都读过,对我的文章表示赞赏。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说,这就算是最大的安慰与鼓励了。知音难觅,自古而然。我的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我不要写了,热心的,冷心的,深交的,浅交的,几十年的,不几年的,都谆谆相劝:你自己反正是快要翘辫子的人,还有儿子孙子,可不要连累他们啊!
(三)我是每天,除了游泳之类活动运动,还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章,所以活得很累很累,但不寂寞,更不空虚。近日,正在写的是《章伯钧,一条被毛泽东引出洞的蛇》。这是三五天前才立定主意写的,并且放下了一个正在写的长篇。这是因为看到两个材料,加上1957年的《人民日报》和章氏爱女章诒和的著作,可以综合做一篇大文章,应当是很有意义的文章。它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头号右派章伯钧的传奇,谁也杜撰不出的传奇。章伯钧的右派是怎么打出来的呢?原来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深夜两点钟打电话给他,苦苦央求他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就某个问题发言。因为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可是几天后这个发言就成了他的右派大罪状。老鼠过街,全国声讨。“章伯钧开始时,死活不承认自己有错,并且有恃无恐地顽抗。他说:政治设计院、两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泽束的!後来彭真亲自上门拜访章伯钧。两人关门密谈了半天,达成了某种协议。章伯钧全面接受批判,定为极右派。又有章伯钧说共产党借他的头,他也同意的活。中共没有亏待章氏的投降,保留了优厚的待遇,这是后话。”
23年后,据章氏爱女章诒和所云: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
“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这样的传奇,在稍稍有一点法治观念的西方社会,从古至今,都是编撰不出来的。“天方夜谭”也设想不出这类传奇故事,可是它就发生在半个世纪前具有华夏文明的敝国国度里。何谓中国特色?此一例也。
(四)写作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事,除了当年癌症时写检查交代汇报,任何人被逼是逼不出文章来的。从前靠笔写,现在靠键盘敲,但都要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孜孜矻矻。打右派时的青年作者,好大一群,例如王蒙等等,改正以后,一度文思泉涌,风光文坛,出尽风头,可是“风波”之后,忽然都江郎才尽似地了。他们,如王蒙,和我同岁,大多年龄和我相差不大。这既有环境逼迫的原因,更有主观原因。一位和曹禺交往颇多的晚辈作者毕汝谐说:“将曹禺作品质量下降,归因于1949年的政治变迁,是最便当的理由和借口;我却以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惊文坛后,曹禺作品于整个四十年代已呈现质量下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除了作者署名依旧,与公众认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远了。因此,1949的政治变迁,反倒成为曹禺写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最好的饰布;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巴金、沈从文、冰心等文坛名宿。”(《忆曹禺》)
中国的老一代作者几乎都有这个问题。曹禺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但那是不可比肩的。英国的莎翁,俄国的托翁,法国的巴氏,人家是老而弥坚,老而愈辣,大器晚成,越写越成熟,写出可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而且确实是著作等身。如王蒙们,已经功成名就,可以犬儒迎合,安度晚年了。但即使如此,想想他们,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展示了右派的苦难,但是在当时他们不可能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这个任务不是由右派作家提出的,正好是在他们沉寂之后,由另一批没有文学造诣的老右派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实际打击提出的,大体是在反右运动50周年前夕,从此出现了此起彼伏的上书,要求维权、补薪、索赔。我们被边缘化,受到监控,连走亲访友也会被当地警察或非警察关照。我们又成了“敌对势力”。
现在,王蒙成了主流社会的贵族、宠儿、供品、喉舌,但我们不羡慕,也不嫉妒。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五)但是,我们缺乏文采。我真想创作出绝世之作,但是年岁无情,学力不逮。编戏剧,谁不想做莎士比亚?写小说,谁不想做托尔斯泰?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者,文采也。也许有几位文采斐然的作家在偷偷摸摸地创作,准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可能我来不及看到了。最近,北京有人又把老舍的《四世同堂》改编成了话剧上演,成了重要新闻。与其说乱世可以出英雄,不如说乱世可以出文学巨著。这一百年是一个风云变幻、奇异诡谲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的时代,轰轰烈烈,多姿多彩,举世无可相匹,历史不可再造。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饥荒、文革大造反,等等,等等,从文学艺术的创作来看,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可以够一百个一千个莎翁托翁巧取豪夺,可以造就出多少科学、文学、艺术的巨人,栽培出多少参天的大树,为中国科学文化文学的繁荣,贡献一大批旷世之作,不幸的是60年来,科学没有大家,文学没有大师,文学艺术的原野是一片荒漠,满目苍凉。这固然可以加罪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但是我们的文学家们也太不争气了。还怕什么呢?这三十年,虽然当局者极尽打压之力,却比毛泽东时代毕竟还是有了进步。你可以偷着写,拿到网络上发表,拿到香港出版。果真是文学精品,绝对埋没不了。延安时代批判萧军、丁玲,我当然无幸看到,但是从1949年批判萧也牧开始的每一场文艺大批判,我都与闻与见。从毛泽东直到今天,中共的统治,最伟大、最成功、最不朽的功绩就是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浩气,彻底摧残了造就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繁荣的自由思想,彻底摧塌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文人立世的精神支柱,彻底践踏了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东方的人本主义。这是无论多少个GDP也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真是居功厥伟,流芳百世,万寿无疆!这六十年,使中国文化遭到万劫不复的大灾大难。
摧残者树立的丰碑就是文学艺术百花园里只有枯木朽株狼籍遍地。
积八十年的观察,我唯一可以预言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永远创作不出传世之作。
我希望《往事微痕》或《黑五类忆旧》的作者们怀抱大志愿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遗世之作。
(六)我预言:刘晓波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授予中国人,是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早在明年,晚在后年。如若不信,拭目以待。
(2010-12-5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