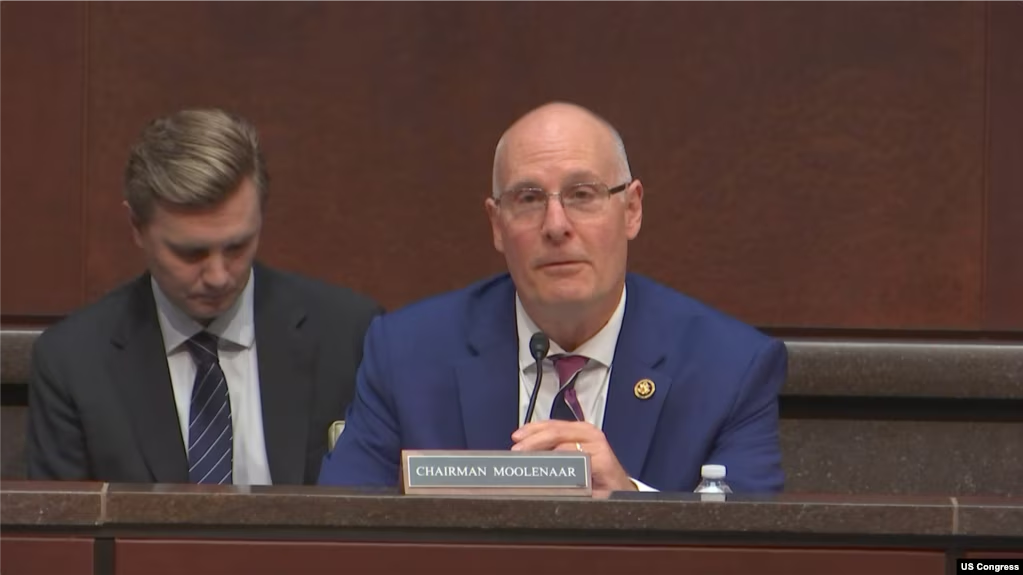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主权,通常是指国家固有的对内对外保护独立自由的权力,是对最终统治权力的高度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更重要的是指一种观念、一种理论、一种原则。主权在民,又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集中表达了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确立了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明确提出主权在民并进行系统阐说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1712~1778)。卢梭认为,主权意味着执行公意,主权者是由组成国家的个人组成的。当国家根据社会契约建立之后,所有公民的一致同意便是公意的表示。由于国家是契约的产物,那么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和认同,这才是政府及其权力存在的唯一合法依据,政府行为一旦违背人民的授权和公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从法律的含义来看,主权在民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于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从管理的角度看,主权不可能由所有公民共同行使,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大国,还是梵蒂冈这样的小国,都只能由公民中的一部分专门人才和专门机构来代行主权在民,即通过“授权”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照正当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由这些代表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人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罢免不称职的代表或其它政府官员,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民主国家,这个过程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则是一样的。既:经过人民授权,政府才有最终的合法性。
有限政府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政府的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必须经过人民的授权。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依照正当程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由这些代表行使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权力,人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罢免不称职的代表或其它政府官员,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民主国家,这个过程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则是一样的。既:经过人民授权,政府才有最终的合法性。当今世界,依照国际法具有主体地位的政府有二百多个,有民主政府,也有专制政府,这些政府只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在国际法领域就是合法政府,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但是在国际法上合法的政府,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合法政府。在国际上,一个政府是否合法,不看它是否得到了本国人民的授权,而是看它是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看它是否得到了主流大国的承认。这里所说的合法政府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那些得到本国人民授权的政府。前者讲的是“承认”,后者讲的是“授权”,就这么一点点区别。
有限政府的第二层意思在时间上体现,政府必须定期更换,定期获得人民重新授权。其他的政治人士被制度化地排除,而一部分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后人持续把持公共权力,这就不是有限政府;其他的政党被制度化地排除,而只允许一个政党组建政府,这就不是有限政府。在专制制度下,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个政党数十年把持政权,生杀予夺,这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也是司空见惯的。北朝鲜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把国家元首的位置传给儿子,儿子又要传给孙子,在这样的景象下,北朝鲜政府就不是有限政府。相比之下,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共产党就要比北朝鲜共产党好很多,但中共依然不是有限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搞自由公正的普选,而是换了一种叫做“集体接班”的传宗接代方式。毛泽东等前一辈革命家已经相继故去,但现政权中当家人的主要还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儿孙,或者是和他们有裙带关系的人。中国大陆不实行普选,但每过五年就要“选举”一次,实际上是任命和推选。在“两会”召开的时候,你观察参会名单就容易发现,投票“选举”的是那一拨人,“候选人”也是那一拨人,而平时主理政务的也是那一拨人,换来换去就那一拨人。
有限政府的第三层意思在空间上体现,政府必须有所不为,甚至有些领域永远不能进入。在文明政治中有这样一种精神,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对公民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机构设置有多少,职能范围有多广,立法要合乎什么程序,执法要合乎什么规范,违法了要受到什么惩罚,这些都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条文做出有效限制,这就是有限政府。在当今中国大陆,“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对公民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这样一种理念近年来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但是一纸《行政许可法》并不能在中国大陆建立有限政府,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有些根本没有进行,尤其是行政管理的理念、方法、制度等都存在诸多问题。在政府的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是这样,既:“对政府而言,法无限制即自由;对公民而言,法无授权即违法”,与普世价值正好相反。特别是基层政府,它们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是否授权的问题,而是政治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必然造成对普通国民的人权伤害。在一党专制之下,虽然也会有诸多法律条文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但是因为政治高于法律,所以法律的有效性就打了折扣。
当然,有限政府,不是仅仅是说法律能够有效约束它,没有这么简单。有限政府最前置的含义是说,有一些东西它不能侵犯。就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作了这样解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必须注意,这些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公民不能把这些权利转让出去,政府也不能侵犯这些权利。美国宪法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确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国会万一“一不留神”通过了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权利的法案,那就是违反了宪法,这样的立法行为和由此立出的法,就是非法的,就不能成立。这就是“非法之法不是法”的意思。很显然,这一条款的矛头不是对准政府的,而是对准国会的。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宪法正文中已经有过类似条款了。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和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第10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又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这样的法案或法律。可见,这是美国宪法一以贯之的精神,但也正是我们中国大陆所缺少的精神。
真正有效的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它的权力界限非常清晰,不该它做的,它就不必要去做,人民知道它没有相关权力,也就不会责怪它。如果一个政府的权力很大,边界也不清晰,该不该它做的事情,它都要去做,最终就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好,而民众知道它的权力很大,就会责怪它。比如各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旦政权在握,总是要领导一切,人们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它什么都想管,一旦管不好,人们就会骂它,甚至想把它轰下台去。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往往就有这样的现象,工作不顺心都会大骂共产党,当然是悄悄骂,人们大多不敢公开骂。反过来再看有限政府,有限的政府责任非常明确,不该它做的事,它可以不做,但该它做的事情大多也做得很快很好,很有效率。你看日本政府救灾快不快?你看法国政府轰炸卡扎菲快不快?你看美国政府斩首拉登快不快?都很快。所以应该有这样的结论:一个合理的政府,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有限的政府,不仅因为它政治合法,而且因为它真正有效。
主权在民的原则始终站在政治伦理的最高点,对一切政治行为进行道德审视。主权在民就要求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不能侵犯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它只能为着保护人们的权利而成立,并且人们能够通过法律有效约束它。怎么才能有效约束呢?就是从技术上把政治权力分开,使之相互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在民主国家,人民有最终的主权,他们能决定、选择和参与公共事务,政府依照公民的需要而成立,但是政府掌握了权力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身外之物,一旦遇到各种机缘,它就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合法权利,那么在选票之外,也就需要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经过千百年的政治实践,人们发现了这个窍门,要想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就是把它们的权力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然后再共同服务于全体公民。
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美国比较彻底地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比较彻底的。而美国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
当一个人,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组织权力无边的时候,它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也许就会随之而来。那怎么办呢?惟有走分权之路,并让不同的国家权力机构相互制衡,不让一方过于强大,在制度内容设计的时候,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让立法和行政机关相互制约。这样,当一个国家机关发生侵权时,另一个国家机关可能会制衡它,并纠正它,而公民可向另一国家机关寻求保护。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权力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公民才是安全的;权力自由了,人民就有祸了。分权制的实质就是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防止强人独裁专断以保障“有限政府”,并实现“人民主权”的目标。
从“主权在民”,到“有限政府”,再到“三权分立”,这是一个从自由到民主的概念序列,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序列,也是一个实践的序列。各国民主化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先争取到“人民主权”,然后才能实现“有限政府”和“三权分立”,不可能说在人民没有权利的情况下,依靠专制政府就能实现权力的自我约束。权力的自我约束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它只会在压力下被约束。压力应该来自何方?当然应该来自人民,来自每一个争取自由的人,来自每一个争取权利的人。
有不少中国大陆学者认为中国能够走上一条从法治到民主的道路,即:先实现法治,再实现民主。这种想法很有善意,但这显然是一种给专制政府让路的思维。对中国社会必须认清一点,它不是个法治社会,有法律而无法治。法治的第一原则是:平等权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普通人、总统、政府、企业和法人等,概莫例外。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人民平等权利吗?显然不能,它要领导一切;特权集团愿意与中国人民平等权利吗?显然也不能,它要掠夺一切,这两个问题是要害。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之下,根本就不存在法治社会的基础,根本不可能建立一党之下的法治,所以从法治到民主的道路是一种空想,是一厢情愿。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民在推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借助于现行法律,恰恰相反,正式因为没有法治,特权集团才肆意横行,无法无天,所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动力。中国人民要走上民主的道路,最终还是要通过借力打力,按照《零八宪章》指引,开展公民运动,实现政治革新,落实主权在民。然后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框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