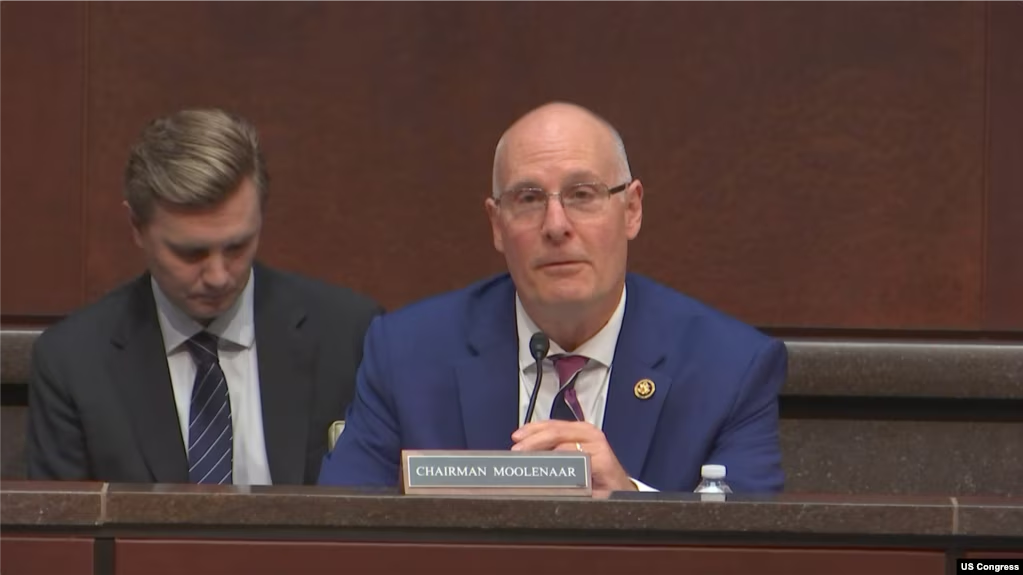核心提示: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都一一应验。我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
有一次聊天,柴静突然问我:难道你没有那么一天,如梦方醒,意识到现实生活和我们小时候通过教科书相信的美好社会不一样?我说没有啊,因为我很少通过教科书相信什么,我更相信生活。
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知道拂去时代的虚饰。从经验出发,这也是人类理性的开端。我对世界的判断并非来自课本上的说教,而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一些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验主义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开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却有年少时的照片。这当然不是因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的缘故。此时,毛主席的头像却是四处放光。
是的,这个村子贫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
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祖母和父辈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都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
谈起当年的饥饿,母亲常常和我提起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最坏。而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痛何如哉!极端的年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到本村要饭。本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的。
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都知道,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就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还在向苏联出口粮食。
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而按现在的危机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
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之所以源于一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农学家董时进先生的相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随时出现。
前文提到,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