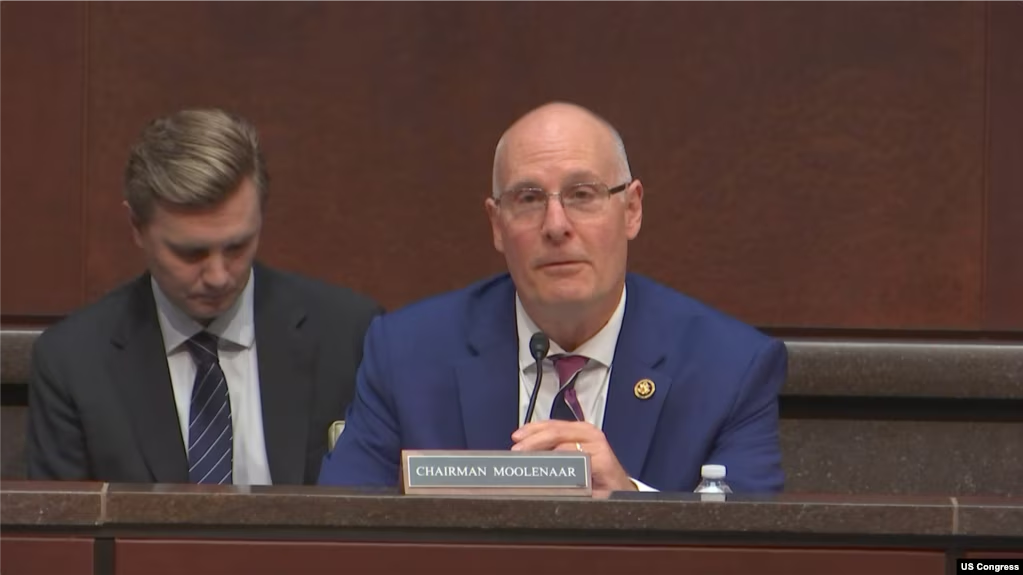我將成為這世上
曾經的過客,一個名字,
從墻上滲下來
墻上,一道傷口正向高處舔去。
————保罗·策兰
《我們都是李旺陽》是一本奇特的書,它在香港出版,封底卻沒有出版社的名字、定價和條碼,宛如在中國嚴酷的新聞出版檢查體制下,不少作者冒險自行印刷並悄悄傳播的“非法出版物”。它採用線裝書的裝幀,接近方形的開本,以及用薄薄的宣紙製作的素雅封面,最古典卻又最現代,凸顯出“體制外出版”的強烈風格。在書中,還夾著一張小小的書簽,上面寫著:“毋忘義人,七一上街,免費派發。”
而我獲得這本書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二零一三年春,我到台南訪問時去了一家咖啡館,看到牆上掛了一幅署名“智海”的李旺陽吊死在坦克上的漫畫,不禁感到好奇:發生在遙遠的湖南的這樁人權案件,何以引起台南民眾的關切?我在臉書上聯絡到這家咖啡館的老闆、同時也是草祭書店老闆的蔡漢忠。蔡先生說,這張漫畫取自詩集《我們都是李旺陽》,有一小部分書曾在草祭書店代售,現在還剩最後一本,可以送給我。
二零一四年春,我再度訪問臺灣,特意趕到草祭書店與蔡先生見面,並收到這本寶貴的書。這本書是二零一二年六月十日“我們都是李旺陽”萬人遊行、尋找真相活動的“附屬品”,所有作品的徵集都在臉書上完成。那一場活動,用組織者何比的話說,本來設想的參與者大概是數十至一百人,“我們自己很清楚為什麼要走這條路,以及如何走。我眼裏看見的只有光的輪廓”。誰也沒有料到,一位從未到過香港的內地平民李旺陽,居然激發了兩萬五千位香港市民上街抗議,抗議者包圍了中共在香港之巢穴中聯辦大樓,讓那些龜縮在陰暗的房間內的中共官員膽戰心驚。
那殺死身體不能殺死靈魂的,不要怕它
是的,無論北京欽點的地下党特首梁振英,還是富可敵國的商人李嘉誠,誰能像冤屈而死的“六四”鐵漢李旺陽,牽動無數港人的心?
李旺陽被殺人流血的“強國”囚禁、淩虐、殺害,而指使國保警察害死李旺陽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卻升任最高法院院長。外媒和很多中國知識份子矚目于周強的法學博士的眩目學歷,並一廂情願地相信習近平打造“法治國家”的謊言,他們忘記了周強手上沾滿李旺陽鮮血的鐵的事實。難道“博士治國”就是國之大幸嗎?周強和習近平都是博士,戈培爾也是博士,博士跟文明有什麼關聯呢?聖經中說,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禍了!當劊子手搖身一變為大法官,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公義和法治可言?
此時此刻,詩歌是記載真相、書寫歷史的載體,正如為本書寫序言的香港詩人廖偉棠所言:“在這樣一個完全抹殺人類文明的存在資格的世界,作為文明的捍衛者,我們只能寫好一首詩,在不可能的狀態下去令一首詩完美,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野蠻暴政的一種挑戰。”熊一豆在《悼旺陽先生》中寫道:“他們以為/燒掉/埋掉/抹掉/禁掉/還有,收買/就能把滿手血腥/修飾成胭脂//可是,他們不懂得靈魂與精神/也不知生命轉化之必然的奇妙/所以他們無知于一種新生——/李旺陽可以是,眾人”。而陳恩在《我什麼都不是》中寫道:“你可以吃掉我/但你吞不下我貞潔的骨頭//你可以把我化為灰燼/但你的雙手會因此變得烏黑//你可以將我蒸發/但我會在蒼天再凝聚/成為一場盛夏的雨//我什麼都不是/而你卻躲不開”。聖經中說,那殺死身體不能殺死靈魂的,你不要怕它。不相信人有靈魂、不相信靈魂擁有更高力量的共產黨政權,認為殺死人的肉體就萬事大吉了,統治就固若金湯了。但義人肉體的死亡並不意味著戰鬥的結束,恰恰相反,善與惡的戰鬥才剛剛開始。
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曾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法國大革命的觀察——“革命必然是從無神論開始的。”他斷言:“對上帝的憎恨是掩藏在馬克思主義背後的根本動力。”他又指出,共產黨掌權之後,善與惡的概念一直都被嘲弄著,它們被逐出了日常生活的使用範圍,它們被政治或階級的短暫價值所取代。訴諸永恆概念已經變得很讓人難為情了,因為惡在進入政治制度之前,已經在個人的心靈中紮根了。這一段描述也適用於“六四”屠殺之後的中國——人們假裝那場屠殺沒有發生過,以便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而李旺陽的殉難,讓善與惡的不相容性再度尖銳地呈現在每個人面前。張希雯在《無題》中寫道:“就算砍頭/也不回頭/因為自由的夢/沒有盡頭/不能回首//你的曼舞/從未停步/你的腳跟躍起/你要飛往/雲端以上//雲端以下/還有我們/像螞蟻一樣/纏死大象”。是的,螞蟻與大象之間的搏鬥,李旺陽與共產黨之間的搏鬥,一定會有另一種結果。這種樂觀的期待,正如姍在《看吧》中的宣告:“他們以為你倒下了/真正倒下的,是他們”。潘霍華死了,甘地死了,馬丁·路德·金死了,李旺陽死了,但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他們。
“紅旗”與“白綾”的對峙
作為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的保羅·策蘭,難以從殘酷的傷害中復原,即便詩歌也無法療傷,他縱身一躍跳進塞納河,他是一名真正的自殺者;而從二十二年的黑牢中掙扎出來的李旺陽,比保羅·策蘭更加堅韌,他要活下去,卻死於具有中國特色的“被自殺”——精心設計的謀殺。
在死亡的這邊和那邊,有兩幅怎樣不同的風景?周雪凝在《未命名》中寫道:“他/站在鐵窗前/紅旗套成環索”。這句詩歌中呈現了兩個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意象——紅旗與絞索,或者說,紅旗與白綾。兩個意象的重疊揭示出一個被遮蔽的真理:紅旗是用白綾製作的,這個政權建立在流人血的基礎之上。正如思兼在《東方紅》中所說:“探頭窗外,/聽到亡靈示威,/聞得硝煙履帶。//繩結不解,/只見盛世高樓,/不見廣場血淚。//東方紅,/血還未流夠。//人心黑,/你卻看到光。//沒有其他紅比這面國旗更紅,/底下沒有比它更黑的要掩飾。”有一天,我們必須將這面貌似紅艷其實漆黑的旗幟扯下來。
在悼念李旺陽的遊行中,有香港人第一次在中聯辦門口焚燒了這面中共欽定之五星紅旗。古有吳三桂怒髮衝冠為紅顏,今有香港人焚燒紅旗為旺陽。前者為私欲,後者為公義,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這是香港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轉捩點。邁出這一步,與沒有邁出這一步,有著根本性的差別。此舉象徵著香港民眾與中共之決裂。從此,香港市民將不再上訪、不再鳴冤、不再進諫、不再對中共暴政抱有一絲希望。
此前,香港人雖然將反共當作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卻長期受制于“愛國”的緊箍咒,束手束腳、畫地為牢,不敢捅破“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偽中國”這層薄薄的窗戶紙。大概因為香港有過英國殖民的歷史,香港人在心態上有一種自我矮化的自卑感,生怕稍有不慎,便被同胞指責為“不愛國”,那可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大罪。如今,香港人意識到:要做真正的愛國者,反共乃是必須邁出的第一步。焚燒沾滿受害者鮮血的五星紅旗,就好像焚燒那面納粹的旗幟一樣,乃是光明正大的義舉。
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謊言與暴力齊飛,天怒並人怨一色,解放軍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國保警察謀殺氣若遊絲的李旺陽,如此暴政,不得不反!正如中國先賢孟子所言,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正如歐洲宗教改革先驅加爾文所言,反抗暴君與暴政,乃是上帝賜予人類的基本權利。陳子謙在《我們都是李旺陽(或我們不是李旺陽)》中寫道:“我們不是李旺陽,真的/是二萬五千個黑影/拋出黑紗的熱浪//我們都是李旺陽/我們都是,都不是/我們,都是我,都是自由的水滴等待著/等待著聚成巨浪/重新粉碎”。焚燒紅旗,只是開端,而非結束。焚燒紅旗,就是焚燒那根勒緊我們脖子的繩索,如小西在《沒有》中所說:“沒有眼睛/才能看見微風/沒有耳朵/才能聽到森林//沒有繩索/才能自由”。
還有一個義人,值得我們尊崇與紀念
從這本詩集的誕生過程可以看出,作者們不僅坐而論道、不僅在象牙塔中寫詩,而且大都是雷厲風行的行動分子。廖偉棠說:“與這本詩集密切相關的是行動,從臉書徵集,到書寫白幡,到在六月六日大遊行中舉示蒼天與眾生,這些詩歌獲得了超越文本的更多意義,這是行動的詩學,將由未來的戰鬥來檢驗它的美。”從傳統的維園燭光晚會、七一大遊行,到聲援李旺陽、反國教以及佔領中環,香港的公民運動一步步走向成熟、多元以及更為廣泛和深刻的社會動員。
近年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日漸覺醒。同時,港人並不因為認同“本土”而對中國及世界的事務充耳不聞。恰恰相反,清晰而堅定的本土意識帶來“喪鐘為我們每個人而鳴”的更加廣闊的胸襟和視野。這就是港人深切悼念李旺陽的精神背景。對於死去的李旺陽來說,我們都是遲到者、旁觀者和苟且偷生者。“六四”屠殺之後,劉曉波一直受到作為倖存者的恥辱感的折磨——尤其是一名“有名”的倖存者。當獄中的劉曉波知道自己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不假思索地對妻子說,這個獎是給“六四”亡靈的。那時,劉曉波不會知道,一年多以後,李旺陽也成了“六四”亡靈中最新的一員。蚩尤在《重量》中寫道:“她/躲避十架/寬恕永久懸空//你/背負良知/腳跟從未離地”。這裏的“她”,雖然沒有具體的所指,但讀者猜都猜得出來,是指某些在海外趾高氣揚地指點江山的前學運領袖。與之相比,李旺陽才是以身殉道的義人,蘇麗嬋在《隨旗幟飄》中寫道:“這裏/有眼,沒有真相/有耳,沒有呼聲/有口,沒有補充/世人用一生來換取樓房把自己關起來/你以關起來的一生喚醒世人爭取自由”。無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在極權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的雙重壓搾之下,誰又不是“房奴”,誰又不是“屁民”?李旺陽之於香港、之于中國,如同幽暗大地上的一道閃電,劃破黑暗、驚醒殘夢。
因此,瞭解李旺陽,也是重新認識我們自己。沒有這個榜樣、沒有這面鏡子,在骯髒、齷齪、邪惡的勢力面前,我們就會不知不覺變得無動於衷,乃至隨波逐流。劍玲在《想知道光》中寫道:“想知道你的事/想知道你的愛情/想知道你的生活//想知道你是怎樣捱過廿二年的牢獄/想知道你如何與黑暗相處/想知道你的眼淚//你總是那麼堅持/你總是滿有盼望/你說你要修好眼睛和耳朵 要聽聽收音機//想知道你的盼望從何而來/想知道從你心底散發的光/願你的光照在黑暗裏/照著你 照著我們”。是的,我們想知道關於你的一切,以便我們勉勵自己變得更美好、更勇敢、更有同情心。
記住李旺陽,記住這位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義人,是一門必修課。或許,正因為有他的存在,中國這個大醬缸才沒有被上帝毀滅。或許,正因為有他的存在,這片土地的復興才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那些齷齪、卑鄙、邪惡的故事,我們已經聽到、看到太多,而像這樣崇高、偉大、光明的故事,我們所知的太少、太少。微輕軟在《有什麼方法可以令我們好好記著你》中寫道:“有什麼方法/可以令我們好好記著你/有什麼方法/可以令/這個大工廠大精神病院大監獄/停止運作/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裏/改建成一個/人/可以活得有尊嚴的地方/有什麼方法/可以/令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為什麼/你會站在/站在那裏/望著窗外/有什麼方法/可以/令我們/好好/記著你”。李旺陽無法親口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是給所有的生者的,我們必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