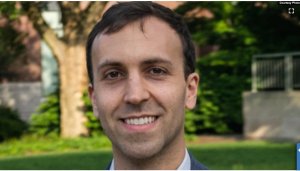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America)杂志,纽约时报中文网获得翻译授权。文章经过编辑。
太行山就像是太古时代留下的一道伤疤,从北京向南逶迤开去,穿过中国的腹地。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道山脉以女娲的发源地出名,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母神格。兵家则冷眼相看,发现了那些易于防守的关隘在军事上的价值。如今,实业家们垂涎这里丰富的矿石和煤炭资源,把它变成了世界的炼钢中心。
但是在过去的四百年里,太行山也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中心轴,是其历史和发展壮大的中心所在。在17世纪早期,北京成为了基督教(本文的基督教是指天主教、新教等宗派的总称——译注)永久的立足点,使得该教从太行山脉两侧向全国散播开去。东边是河北,有中华圣母堂等重要的天主教中心。西边是山西,朝圣地板寺山就在那里。靠近太行山稍南一点位置的,是一个名气没有多大,但或许影响力更大的天主教信仰中心:洞儿沟。
今年五月一个阳光明媚、刮着风的大清早,这个灰扑扑的村子一派十足的乡间虔诚景象。教堂传来晨祷的钟声。有人家正忙着准备大办宴席,举办传统婚礼。载着朝圣者的旅游大巴开始到来,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参观位于山顶的一个圣殿。宗教旌旗在风中噼噼啪啪,念珠发出咔嗒声,祷告直抵天庭。
这一天在42岁的刘文霞眼前徐徐展开,她个头不高,精力充沛,有着农民工消瘦结实的身材,穿着时髦的黑色紧身裤、花裙子和宽松的衬衫。跟许多当地人一样,刘文霞之前离开洞儿沟去了省会太原,这是因为当地的农场规模太小,而且气候太干旱,难以维持生计。在太原呆了20年,她给别人家做保洁、卖寝具,向医院的病人推销药物——在中国什么都需要自己去做的医疗体系下,这是常见做法。“我都做过!”她笑着说,之后变得严肃起来。“现在我有机会回到老家,为复兴天主教出力。”
两年前,她和丈夫回到了洞儿沟,把辛苦学来的创业技能与该村作为朝圣地越来越大的名气结合在一起。他们把山脚一座空的餐厅租下来,将其翻新后起名“朝圣之家”,为每年数万前往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朝圣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点。
夫妇俩还帮忙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捐赠活动,扩建七苦山的朝圣山路。建起了新的十四苦路,山顶一个仪门也进行了扩建。门的后方就是一座颇有特色的教堂,它看上去像北京的皇宫。有旅游机构在网上发布了用无人机拍摄的这壮观的一路登顶,以吸引虔诚的中国游客。
在洞儿沟,可以看到今天天主教在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种宗教仍然主要盛行于农村,但洞儿沟与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一样正在空洞化,信仰有时并未随之进入大城市。
虽然这个村庄跟中国各地的许多宗教中心一样,受益于宗教旅游的繁荣,但目前还不清楚信教的基本人数是否在增长。甚至,据一些靠谱的估计,中国的天主教人口可能正在减少,这是因为低出生率、传教不足,以及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者与梵蒂冈之间的多年嫌隙。
由于教徒数量未能出现增长——据估计,在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里,目前天主教人口的数量在1000万出头——教会的许多人因此认为,最近罗马教廷与中共之间的谈判就尤为重要。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谈判已经放缓,但当地人仍然希望关系的改善能给教会注入新的活力。他们甚至希望有一天教皇能访问华,他们相信这将唤起人们对该信仰的热情。
不过,也有不少人提醒说,北京与罗马之间关系的改善,甚至正常化,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共产主义制度下宗教信仰之不易,而是在巨变时代里获得认同的艰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既有宗教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在中国尤其明显,因为这里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
对于像刘女士这样的人来说,这些希望和困难每天都从上山去膜拜圣母玛利亚的民众身上可以看到。她说,来这里的许多国内游客都是来自天主教家庭,但在共产党对宗教的强硬打压中,他们失去了信仰。她说,朝圣可以激励这些人,帮助他们看到天主教会的美丽和力量。“他们失去了信仰,但现在主把他们带回来了,”刘女士对我说道,当天的第一批朝圣者开始向十四苦路走去。“但他们今天离开这座山,明天会回来吗?”
历经数百年的冲击而屹立不倒
基督教最早来到中国是在公元七世纪,当时是东方教会,也就是所谓的聂斯脱利派教会(即景教——译注)抵达中国。像六个世纪前的佛教一样,它也是通过丝绸之路这条穿越中亚的伟大贸易路线向东传播的。但是,到了13世纪,景教和方济会都没能继续下去。当战事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时,它们都偃旗息鼓了。
直到16世纪,基督教才在中国站稳脚跟。1552年,耶稣会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乘坐葡萄牙的一艘商船,来到广东省南部海岸的一个岛屿。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但另一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接替了他,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语言学家和外交家,他于1582年来到中国,一路慢慢北上,1598年,他达到了目的:来到了帝国的首都北京。在试图使高级官员皈依天主教的同时,他可能也对来自山西这些省份出门在外的商人进行了宣教,从而在洞儿沟这样的村子埋下了信仰的种子。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3000年,比起来基督教来到中国的400年时间似乎很短暂。但它能得以留存仍然意义非凡。自2000年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首次有一种新的宗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中站稳脚跟,历经朝代的衰落和军阀的倒台,以及国家支持的迫害浪潮,成为中国宗教景观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
这一成功部分归功于天主教会的其中一个最大优势: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和资源。直到20世纪中叶,是教会在广袤的土地上调拨资金、派遣传教士。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很快就随之建立起来。除了太行山周边的省份,天主教传教士还深入到云南南部的丘陵地带。中国作家廖义武在他的《上帝是红色》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刻画。他们还在这个国家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和小村庄建立了重要的信仰中心。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天主教会的本土化进程却非常缓慢。直到1946年,梵蒂冈才批准中国天主教实行独立圣统。三年后,当共产党上台时,大多数天主教医院、学校、孤儿院及其他机构仍然由外国人经营。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只有28个是由中国人管理(21名主教和7名高级教士)。其他109名主教和高级教士则是外国人。
因此,当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将几乎所有外国人驱逐出境,并切断了与梵蒂冈的联系后,天主教会群龙无首,在挣扎中求生。传教基本上停止了,皈依的情况极少发生,除非是因为婚姻进入天主教家庭。
这个挫折反映在天主教信徒人数增长缓慢上。1949年,中国估计有约300万天主教徒。今天最高的估计是1200万,这意味着天主教教徒的增幅仅与人口增长相当,1949年中国有4亿人口,现在是近14亿。
鉴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宗教信仰出现爆炸式增长,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人数停滞尤为令人沮丧。在共产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统治时期,宗教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自毛泽东去世,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采取了资本主义式的改革以来,宗教开始兴起,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重、追求物质主义的社会里,这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更广泛探求的一部分。
在中国各地,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数增长迅速,现在已经达到数亿人。与新教的比较更是惊人。1949年,中国有100万新教徒。现在,这个数字估计在5000万到6000万之间,而且在天主教最薄弱的地方——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专业人士中间,新教的会众规模尤其大。(伊斯兰教是中国的另一主要宗教,但局限在10个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当中,只有2300万。和天主教一样,它的增长主要是基于自然人口的增加而不是皈依。)
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成因可以追溯到本地化问题。直到20世纪中叶,天主教都不愿实行本土化,这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本土新教领导人的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其中许多人被共产党抓了起来,但他们的追随者构成了今天巨大的新教“家庭教会”运动的基础。不管怎样,中国的新教教会轻装上阵,自学成才的牧师在短短几年内就能搞起教会,并吸引大批会众。
这种自发性的体制建设,在天主教这样更为正式的结构化信仰中是很难实现的。在中国,由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这一点尤甚。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政府成立了爱国运动委员会,控制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和道教这五大宗教团体。这些委员会现在管理着清真寺、寺庙和教堂,任命重要的神职人员,并管理神学院。
对于像新教教徒这样的群体来说,政府控制是一个困扰,但他们在权力上更为分散,因此可以忽略等级制度,灵活地回应需求。简而言之,任何虔诚的信徒都可以组成一个新教教会,并宣称自己是其领袖。
这对天主教徒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共产党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后,政府官员开始任命他们自己的主教。许多天主教徒对于参加政府控制的教会感到不安,一些人就不再去了。还有一些人则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建立起一个天主教地下教会。该教会不承认天主教爱国会的合法性。但即使是这个地下教会,也有着相当严格的等级制度,任命需要中国境内的更高层批准。
多年来,“公开”教会与地下教会之间的分歧变得没有那么明显了,尤其是在2007年教皇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牧函之后。教皇在信中实际是在说,地下教会不应该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而且天主教徒可以参加由中国政府认可的教会提供的宗教仪式。
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仍然是有问题的,它阻碍了教会的发展,并经常进入公众视野。例如,在2012年,政府任命马达钦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不过,马主教在晋牧庆典上表示不再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任何职务,这显然是对政府宗教管制的抗议。他被软禁在佘山修院内(今天他基本都是呆在这里),结果导致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神学院之一关闭了一年有余。
在另一个例子中,2014年在北京,一群修生抵制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们发现,一位未经罗马批准而祝圣的主教将主持毕业弥撒。这些修生没有毕业就遭驱逐。加之佘山修院事件,这意味着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失去了两个毕业班的修生。“北京和罗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引发了这些事件,”美国惠特沃思大学(Whitworth University)的中国史教授柯学斌(Anthony Clark)说。“天主教会众确实注意到这些事情。这是令人不安的。”

2017年5月,一名天主教神父发给天主教信徒圣餐,这些信徒到洞儿沟外的山顶上造访七苦圣母。
Sim Chi Yin/VII/Redux
繁荣的双刃剑
一方面,洞儿沟这座教堂的名字——七苦山圣母堂,指的是圣母玛利亚和她作为耶稣母亲所经历的七次审判。但它跟一个发生在当地的故事也有关。1912年,一名方济会修士被要求离开洞儿沟,他想带走一尊1901年被带到该教区的卢尔德圣母像。村民们相信这尊塑像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因而不让他带走,于是他怒气冲冲地离去,冲着村子挥舞着一只鞋(咒骂之意——译注),骂他们是犹太人。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里传教士的诅咒及其他故事》(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一书中记载了这个故事,这本书不厚,却很有力量。根据那个故事,洞儿沟连续七年歉收,村民后来在山顶修建了圣母堂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打那之后,洞儿沟就成为了一处朝圣地,特别是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命运不济的人来说。我在那里碰到了来自甘肃的朝圣者赵妙玲(音),她和另外40名朝圣者一起搭乘夜行巴士来参拜。这群人爬山过程中,不忘在苦路十四处祈祷,山路的每个转弯之处他们都会停下来,用方言念诵圣歌。
52岁的赵女士与许多同龄的中国女性一样,也在失业中。她原本是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后来被要求提前退休。因为想知道人生除了工作还有什么,于是信了佛教,后来又改信天主教。
“我们按照圣母的心所示而来,”她告诉我。“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许多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受过很多挫折。我们没法自己解决。只能依靠上帝。我们希望求了之后,会灵验。”
在山顶教堂的弥撒后,我跟赵女士在平坦的山顶四处走动,她告诉我自己为什么会皈依天主教。“社会不只是缺乏信仰,而是完全就没有信仰,”赵女士说道,不过她又补充,“我所有的朋友都对宗教感兴趣。”她表示,大多数人都信佛,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在文化上也更熟悉。就她自己来说,之所以信天主教是因为她的婆婆是天主教徒。“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这种宗教,”她说。“但我因为婚姻结缘,通过家庭我了解了它。”
这并非什么奇特的故事,事实上,可能大多数天主教徒的皈依都是这样的。与新教教会相比,天主教会在大学成立的圣经研究小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也很少在圣诞节这样的节日邀请好奇的陌生人去他们的教会,作为世俗节日的圣诞节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教会里有些人对缺乏传教感到惋惜。一位经常在洞儿沟工作的司铎说,天主教在毛时代的中国是最强的。当时它受到攻击,人们于是团结起来。像洞儿沟这样的村子,往往全村都是天主教徒。由于居民不允许离开他们的村庄,本地关系和信仰都得以加深,虽然无法公开崇拜。
在这些限制取消后,天主教开始从冬眠中苏醒。教堂得到重建,神学院有了年轻人的加入,迫害中幸存的传教者热情地传播《圣经》。
然后是繁荣时期的到来。人们背井离乡进城工作。很少有人像山脚开餐馆的刘女士这样,回到老家重拾信仰。
“村里的生活和一切相关的事情都开始显得落后了,”上面提到的那位司铎告诉我。“天主教似乎成了人们所抛弃的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梵蒂冈寻求缓和关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怀疑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在下降。香港圣神研究中心(Holy Spirit Study Center)的林瑞琪是关于中国的天主教会目前最受尊敬的观察人士之一,他广泛挖掘公共数据,并与地下教会人士进行访谈。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天主教徒数量在2005年达到最高点,为1200万,经过几年的停滞,现在呈下降趋势。
在去年春天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林博士估计,中国的天主教群体每年需要21万次洗礼才能弥补自然的损失,但实际上,洗礼的人数不超过3.5万。他认为,中国目前天主教总数约为1050万。
这也反映在公开教会和地下教会圣召的数量上。根据林博士的估计,从1996年到2014年,男性圣召从2300人下降到1260人,而女性圣召则从2500人下降到156人。他还写道,圣职授予仪式从2000年的134次降至2014年的78次。
许多中国的天主教徒都希望与梵蒂冈恢复关系能带来更好的时代。从去年开始,大家都知道双方的谈判已经恢复,一些观察人士预计很快就会达成决议。但梵蒂冈与中国大陆举行谈判的地点——香港教区的主教杨鸣章在接受天主教通讯社(Catholic News Agency)采访时,措辞谨慎。今年8月1日接替汤汉枢机的杨主教说,“健康现实主义一方面确实需要警惕妄盼和不切实际的期待,另一方面要警惕仓促关闭对另一方举行进一步对话的大门。”
双方谈判的一个关键分歧是如何选拔主教候选人,这个问题导致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甚至将他们逐出教会。据知情人士透露,一项可能的协议是,北京当局负责挑选候选人,梵蒂冈拥有否决权。显然,这仍未解决如何处理不被对方认可的主教。此外,北京方面也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号,例如在温州拘捕了一名主教。
总体上说,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对任何形式的独立协会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非政府机构被关闭或被迫登记。去年,中共举行了一次罕见的宗教会议,呼吁中国所有宗教信仰“中国化”——这意味着宗教必须由国家控制。(杨主教在接受天主教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似乎担心天主教领袖的“爱国心”不够。)
至少,在今年10月举行的五年一度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谈判似乎暂停了。
即使双方达成了协议,一些人还是不确定它是否真能帮到天主教会。他们怀疑北京把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当作对天主教加强控制的方式,而不是中国的天主教徒获得更多的回旋余地或与罗马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途径。洞儿沟的那位司铎说,天主教徒应该少花点时间来担心高层的谈判,而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传福音和对信仰的投入上。“大家都有信仰的,都有追求,都有渴望,”他说。“如果基督教能回应他的这种渴望,他可能就成为基督徒。如果佛教能回应他的这种渴望,他就成为佛教徒。我们需要传教。”
在城里坚持信仰
有一天在洞儿沟,我偶然碰到了一场婚礼。新人是29岁的段玉强和贾小茹,两人去年经媒人介绍认识。段是一个当地小伙,是开卡车跑长途的司机,他祖上往前推六代都信天主教。他的新娘来自邻近的姚村,也是天主教徒。他们选择配偶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对方得是天主教徒。“我不可能跟别的人组成家庭,”身材苗条,身穿红色丝绸旗袍的贾小茹微笑着说,而她的新婚丈夫站在一旁,点着头。“我觉得我只能真正理解跟我有一样信仰的人。”
他们的婚礼很低调。几个月前,小俩口已经领了证,今天只是在双方的父母面前鞠躬行礼,他们轮流坐在巨大的红木椅子上,接受这对年轻夫妇的敬意。这是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拜双方父母,由于这对夫妇都是天主教教徒,所以在椅子之间的桌子上,还放着一张巨大的耶稣像。
整个结婚仪式有力、感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一种回归。与他的许多朋友一样,段先生是为了婚礼才回到村里的,平时他和大多数朋友并不住在这里。确实,洞儿沟参加早晚弥撒的都是老年人。即使是在礼拜天,教堂也基本上是老人,因为村子里的年轻人几乎都走光了。
在大城市里,信仰很难坚持,要传播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杜晓东(音)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25岁的他两年前来到北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技术支持工作。他来自太行山的一个小村庄,在新的城市里,他努力坚持自己的信仰。“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感觉很迷茫,”他说。“我不知道该拿我的信仰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在与景安琪(音)结婚后,情况有了变化;这个活泼的27岁年轻人来自邻村,也搬到了北京。现在,两人一起去做弥撒,而且正等着孩子的降生。但即使如此,与天主教的接触也没有老家的密切。“我们在邯郸的时候,有十几个(天主教徒)在周末总是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想法,”景安琪说。“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么做,但频率是两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
两人都说,他们想多传福音,但作为天主教徒,他们更希望重行轻言。景安琪说,在她老家,当地的天主教徒为中风瘫痪的人做足底按摩。她说,这个做法引得30人受洗,但她怀疑这种做法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是否有效。“我们的确感到,在扩张方面,我们不像新教徒那样雄心勃勃、胆子大,”她说道。“他们可以更自信地讲道。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用行动来影响人,而不是用说的。”
我们全家人的朋友
在洞儿沟的大多数早上,我都是和42岁的圣言会邢教友一起爬山。我们经过刚刚翻新过的十四苦路,停下祈祷,一路几乎看不见其他人,太阳从远处的群山升起,前路亮堂起来。
在朝圣者远未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登顶,俯视着太行山两个支脉形成的这个灰扑扑的盆地。在我们北边30公里处,也就是盆地中间,有一块烟雾弥漫的地方,那里是省会太原,中国最大的教区之一。我们走到山顶有着弯曲的屋檐和圆柱的中式教堂,祈祷,然后下山吃早饭。
修道会在中国遭禁,因此邢先生在教会中没有正式的工作。如果他有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被转到另一个教区去了。但他因为受伤不良于行,所以留了下来。15年前,邢教友掉进山沟,差点丢命。他现在走路拖着右腿,说话困难——说话缓慢,倒不是因为脑子跟不上,而是反应时间长。这让人很容易以为他无话可说,其实,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洞儿沟和它存在的所有问题。
我逐渐认识到,在洞儿沟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他是维系社会信仰的细胞结构的一部分。我认为,他就是教会隐而不发之力的一个例子:在他自我贬抑的话语中,隐藏着深切、顽固和持久的品质。“我想你可以称我为一种顾问,”他说。“尽管我没有接受过训练。有时,我只是坐在那些人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哭。”
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一样,在洞儿沟让人掉眼泪的缘由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生下有严重残疾的孩子。这样的事件就发生在武金文和秦福兰的身上,他们是第七代天主教徒。在一个安静的下午,我在他们家的客厅见到了他们。沙发旁边,骄傲地展示着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使徒祝福书,这是一个朋友今年早些时候从罗马带回来的纪念品。“我们去罗马?”武金文说。“这是一个梦想,但我负担不起。”
现年61岁的武金文刚退休,之前是附近一所高中的校长。他曾是一名体育教师,脖子粗壮,手臂宽大。当被问到他的运动项目时,他回答:“摔跤。”“大家让我加入共产党,”武金文说。“如果你要想继续有所发展,入党很重要,但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是无神论者才能入党。但没关系。我拒绝了。”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就静静地站在房间后面。她不认字,讲话也讲不清,大多数人都能把她给吓着。多年来,这对夫妇为她的命运感到绝望:如果她嫁不出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在他们死了后,女儿怎么办?他们的儿子们已经离开了洞儿沟,到城里工作去了。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女人将独自生活。
在多次的探视中,邢教友与他们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烦恼。他们一起读《圣经》。他在小教堂里为他们祈祷。慢慢地,他们开始相信,上帝会找到办法为他们的女儿养老。“他(邢教友)是个好人,”武金文说。“他是我们全家人的朋友。他总是在那里。可以信赖。”
行他的路
一天早上,我起晚了。天已经破晓了,邢教友已经动身去山上了。我在山的另一侧才赶上了他,这条路是用炸药在石坡和沟壑生生开辟出来的一条简陋山路。路两旁是巨大的岩石。即使穿着登山靴,下山时我得小心地选择下脚的方向,小心避开锯齿状的边缘。然后我就来看到了他。
我想我赶上邢兄弟是因为他腿不方便,直到我注意到他的脚:没穿鞋,都是血。他看到了我的目光后笑出了声。“我不是每天这样。只是某些天。一年几次。为了记住。”
记住什么?我问。他说,几年前他有过一个幻觉。“我看见了耶稣,他背着十字架。然后我注意到他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没穿鞋。当然,我以前就知道这点。但在那一刻,我想到了它,想到了他是如何背着十字架的。我想:他不是一个人背的。一路上都有人停下来帮他。”
“我无法将我正在做的事和那做比较,但光脚走路让我觉得自己正在担当那个角色,走在他的路上。”我伸出手臂,但他微笑着转过身去。“如果我接受了帮助,牺牲就不值得了。就没有意义了。”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