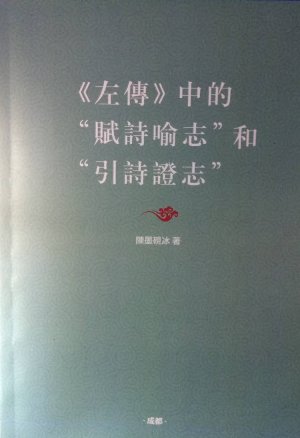
去年写了这本书。《诗》文化现象套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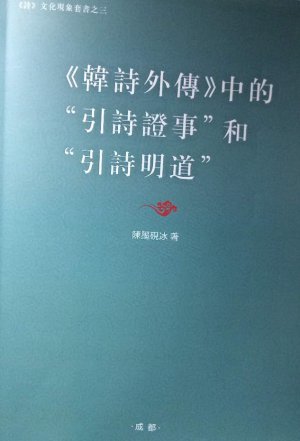
今年又写了这本书。《诗》文化现象套书之三。
全套共六本。还要写四本。计划在今年、明年两年内完成。
總 序
《詩經》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305篇。司馬遷《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詩》被立為太學經典,且為“五經之首”(《詩》、《書》、《禮》、《易》、《春秋》),始可稱《詩經》。但習慣上,仍稱為《詩》,或以傳者的國名或姓氏冠之而稱《齊詩》(齊國)、《魯詩》(魯國)、《韓詩》(韓嬰)、《毛詩》(毛亨)等。譬如唐代立為官學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的《詩》,就叫《毛詩正義》,而不叫《詩經正義》;宋代著名的朱熹注本就叫《詩集傳》,而不叫《詩經集傳》。《詩經》只是現代對《詩》或《詩三百》統一的稱謂。雖為一物,但内涵不盡相同。故孔子之前,無《詩三百》;漢武之前,無《詩經》。
學界之所以稱《詩》~《詩經》“内涵不盡相同”,因為其文化形态隨時代有了種種變化。或者說,《詩》的文化現象千姿百态,在歷史的不同時期有着面目全非的影響、使用及認知。而對這些變化,學界現在基本有了共識,《詩》文化現象的歷史形态大體有六種:一、周初到春秋時的合樂、容舞之《詩》—→二、春秋末到戰國時的子學之《詩》—→三、從兩漢到宋的經學之《詩》—→四、宋代到明代的理學之《詩》—→五、從明末到清末文本主義的小學、博物之《詩》—→六、現當代文學的、審美的《詩》。簡介如下:
一、周初到春秋時的合樂、容舞之《詩》
當代學者李春青先生指出:“從現代詩學的標準看,《詩經》作品大都是當之無愧的文學作品,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些文學作品卻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並不是憑借文學作品最主要的品格——審美功能而獲得主流話語地位的,它們甚至並不是作為文學作品而產生的。從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的文化語境看,詩歌承擔着建構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系統的重任。……他們浸透了周初文化主導者們的憧景、焦慮、自勉、謀劃等等心理和意識的因素,也體現着他們對社會人生某些層面上的集體性體驗。”(《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導論》北大出版社2005)《詩》在周初,就承載着統治者“禮樂之治”的重任,是一部意識形態的文獻和周公創造發明的“美刺政治”、“移風化民”的工具。由於當時的“詩歌”是與音樂、舞蹈三位一體的,到春秋“賦詩喻志”盛行時,舞蹈才慢慢脱離;到漢代,詩與音樂才算徹底分家。所以說周代“禮樂之治”的能够深入人心的載體就是這個三位一體的有藝術感染力的《詩》。而“禮樂之治”的另一載體《周禮》,只是繁瑣無比的律令和教條,冷冰冰地令人頭大,就其效果而言,完全不能跟《詩》相提並論。
《詩》在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後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之中,成為教育國子們和樂工們的第一教材,遂逐漸獲得了某種不言而喻的權威性和神聖性。《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音樂品格)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文字之詩)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鹹》、《大磬》、《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從小教育國子(貴族子弟)《詩》的六大功能:政治——用於祭祀(致鬼神)、用於邦交(和邦國)、用於和諧社會(諧萬民);教化——用於人際交往(安賓客)、用於述祖偉蹟(說遠人)、用於勵志鼓動(作動物)。所以孔子才總結說:“不學《詩》,無以言。”所以托名子夏作的《詩·大序》(《毛詩·序》)才說:“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在周代人眼中,《詩》“甚至並不是作為文學作品而產生的。”誠哉斯言!
二、春秋末到戰國時的子學之《詩》
由於國子(貴族子弟)們從小就學《詩》,對《詩》相當熟悉。待這些國子(官二代、官三代……)們踏入官場,正式服務於政治、教化(禮樂之治)後,運用起《詩》來,方方面面(六大功能)無不感到得心應手,水到渠成。於是催生出周初至春秋中葉歷史中最為典雅、文明,最富才情、詩意的“賦詩喻志”的用詩現象。也就是“合樂、容舞之《詩》”在與“詩教”(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若即若離之中,居然逹到前所未有的輝煌。然而畢竟强弩之末,隨着政教的“禮崩樂壞”的深入與廣泛,“人心不古”,“賦詩喻志”逐漸消聲匿蹟,讓位給了追名逐利的“游說引詩”和百家爭鳴的“引詩證言”。
先看一段《荀子》記載孔子是如何“引詩證志”的: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商頌·那》)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妻子。”孔子曰:“《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大雅·思齊》)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既醉》)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賜願息事耕。”孔子曰:“《詩》云:‘晝爾於茅,霄爾索陶。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幽風·七月》)耕難,耕焉可息哉!”“然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臯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息所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通過這段對話,不難發現:1、孔子對《詩》是相當相當熟悉的,幾乎張口就來,極其自然、敏捷;2、所引《詩》句,仍屬“斷章取義”;3、引《詩》所證的,仍是孔子自己對事物的看法或觀點,仍屬“志”的範疇,故仍是“引詩證志”。《左傳》中記述的“引詩喻志”現象共有一百五十九例之多,都是生活中的“引詩喻志”現象。孔子引《詩》,自然是在生活中,不過是在“教學生活”中而已。因為他“述而不作”。可到了“百家爭鳴”時代,各種學說(理論)應運而生。《詩》的權威性、神聖性既然在歷史中早已樹立,引《詩》的功用——訴諸權威、顯示博學、提髙品味也早已成為交流慣例,甚至成為一種風尚。以至於開口講話,提筆作文,不“子曰詩云”一番,似乎顯得其道不尊,其言說不靈一樣。清·勞孝輿《春秋詩話》說:“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臺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從春秋後期到整個戰國時代,立談可以封侯、出相的“遊說之風”盛行,說客們自不免於大量引《詩》以證其言不謬。“百家”欲要彰顯自已獨特的學說(理論),又豈能錯過“顯擺”之機?又豈能連“輿臺賤卒”都不如呢?除非他根本不承認《詩》的權威性、神聖性。《老子》就從不引《詩》,而《莊子》全書僅引過一次,而且還是逸詩,即《詩三百》未選入的詩。故近代有人懷疑《莊子》引的那首詩,乃莊子的“凴空臆造”,只不過偽造的手藝很髙而已。
儒家就不同了。《孟子》引《詩》逹三十九次之多。那是經過深思熟慮、反覆考量後寫下來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孟子本人對《詩》的獨特的理解,以及對先儒“詩教”的重構。而荀子比孟子走得更遠。《荀子》也遠較《論語》、《孟子》更為縝密、嚴整,更為充分、周詳,也更為“哲學化”。《荀子》引《詩》、說《詩》、論《詩》、解《詩》多逹九十二次之多。所以,在“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子們(尤其是儒家孟、荀)“引詩證言”的結果,《詩》的權威性、神聖性再一次得到提昇:它不僅關乎“政教”,它還是“孔仁”之原,儒學之本。
三、從兩漢到宋的經學之《詩》
漢崇經學,而諸子百家之學亡。《詩》既成五經之首,勢必由原本活潑、開放、多角度的“子學期”,進入灰色的漫長的“經學期”。《詩》既然不僅關乎“政教”,它還是“孔仁”之原,儒學之本,那麽它的權威性、神聖性就必然衍生出一種類宗教的鐵律,那就是僵化儒家頭腦兩千多年的“原道”、“徵聖”與“宗經”。
兩漢時“經學之《詩》”(《詩經》學)異常發達,除太學(官學)外,私學更是流派甚多,從者千萬,著述更是汗牛充棟。據《漢書·藝文誌》載:“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當然,這些流派都是儒家,只是他們注解《詩》的角度和手段不盡相同罷了。所以,無論他們怎麽變化,他們始終受到“原道”、“徵聖”與“宗經”鐵律的製約,决不敢越雷池半步。這種鐵律的製約,首先表現在對儒家言說格局、言說路向、言說方式的“範式”上。其次,司馬遷《史記·自序》云:“《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作也。”透露出儒家《詩》觀的致命局限。兩漢儒家既然必須“托五經以立義”(王逸《楚辭章句·序》),“必折諸聖”(揚雄《法言·吾子》),那經學化的解《詩》,就充滿了道德說教,極盡牽强附會之能事,死板而拘泥,失去了詩學應有的感悟與靈性。郭紹虞先生譏四家之說《詩》“像瞎子斷匾一樣。”“以《詩》明道”這具僵尸居然存活了兩千多年,並被歷代的儒生們頂禮冥拜着,變本加利地折腾着,考證着,變賣着。
兩漢時被官學承認的只有四家,他們是《齊詩》、《魯詩》、《韓詩》和《毛詩》。到後來《毛詩》獨存,其它三家《詩》大部份亡佚了,只有《韓詩外傳》十卷幸存於民間。
四、從宋代到明代的理學之《詩》
《毛詩》在東漢時才立為官學,後經東漢經學大師鄭玄作注,成為經學正宗。到唐代時孔穎達奉旨為五經作箋,成《毛詩正義》,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中,成為唐代以後儒生必讀的經典之首。這種一成不變“以《詩》明道”的解《詩》範式,到宋代有了一點點小變化,因為“儒學”已開始蛻變為“理學”(哲學)了。影響比較大的是,朱熹出了一本以自己新觀點解《詩》的《詩集注》,不過把“以《詩》明道”變成“以《詩》明理”而已,骨子裏還是“原道”、“徵聖”與“宗經”那一套。
五、從明末到清末文本主義的小學、博物之《詩》
在“原道”、“徵聖”與“宗經”鐵律的製約下,儒家代代必然對《詩》皆是“創造性的誤讀”與“過度闡釋”。當然偶爾也有較清醒者,譬如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他研究《詩經》的專著就有《詩經稗疏》、《詩經考異》、《詩經葉韻辨》和《詩廣傳》。無疑,他是研究《詩經》的大家。考據學上的成就就不說了,僅《詩廣傳》提出“《詩》道性情”說,就足令人震聾發瞶。他認為《詩》只是周代“禮樂之治”的一本文獻,並不包涵天下所有的“道”。它並非如漢儒們所說的那麽神聖,那麽權威。反倒是《詩》中的“人道”——人之性與人之情的表述,才使其不朽。這種觀點,豈止是離經叛道,簡直是對歷代儒《詩》的徹底顛覆與解構!可惜,在腐儒的世界裏,這聲音太孤獨,太微弱。
所幸的是,在王船山、顧炎武對《詩》考據學的影響下,清初形成了“乾嘉學派”,考證之風幾乎貫穿了整個清代。首先是對《詩》中文字的全面訓詁;其次是對《詩》中古音、古韻的梳理、校正,以及古音、古韻跟今音、今韻流變規律的提煉(形成“音韻學”);再其次是考證《詩》中每一座山,每一條水,每一座城邑,甚至每一種鳥、獸、草、木古名、今名的流變及準確的地理位置;再再其次是考證《詩》中每一種官名的由來、職責内容,每一種制度形成的始末、歷史影響,每一種賦税、每一種貨幣、每一種婚俗、每一種祭典……的流變。
由於清代的統治者雖是外族人,但仍是崇儒迷經的“以儒治天下”者,而且對離經叛道者决不手軟。所以清代的儒生們,為生存計、為避戮所需,都不約而同地選擇既安全又保俸禄的不涉意識形态的純技術型的考據之學,也許這也是時代造成的罷?所以,清代“乾嘉學派”的這種“過度闡釋”,跟前面所有儒家《詩》有本質的區别:前者讓一部文獻鍍上一層又一層金光閃閃堅硬的壳,後者則讓一部歷史文本更加清晰地“返本歸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六、現當代文學的審美的《詩》
到了清末民初,西學漸進。尤其“新文學運動”“打倒孔家店”後,經胡適、聞一多、傅斯年等人的“革命”,《詩》才脱去聖裝,洗盡鉛華,第一次以文學的審美的内涵如獲新生般地再現於世。於是,這一百年來,“饑首歌食,勞者歌事”、“青年男女歌唱愛情”的現实主義的《詩》學觀主宰了對《詩》的審美與評價。易幟後在“歌頌勞動人民”聖諭壓力下,腐知們更是變本加勵,一葉瞕目。所以有專家說,“建國以後,《詩經》終於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也有專家刻舟求劍地說,“《相鼠》等詩是勞動人民對統治階級辛辣的諷剌”;甚至還有專家無知得近於荒誕地總結道,“《詩經》是周代民歌總集”……嗚呼!這難道不像是另一塲改頭換面的“原道”、“徵聖”與“宗經”的滑稽劇麽?
所以,我在文革武鬥時讀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深受啟發,一九七零年就寫了《諷喻是比興的第一義》。今年,又寫成《<左傳>中的“賦詩喻志”和“引詩證志”》一書,目的就是想要告訴讀者,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詩》的“本來面目”究竟是什麽。計劃在三年內寫一套六本書:一、《<左傳>中的“賦詩喻志”和“引詩證志”》闡述的是“一、周初到春秋時的合樂、容舞之《詩》”的《詩》文化現象;二、《<孟子>、<荀子>中的“引詩證言”》闡述的是“二、春秋末到戰國時期子學之《詩》”的《詩》文化現象;三、《<韓詩外傳>中的“引《詩》明道”和“引《詩》證事”》闡述的是“三、從兩漢到宋代的經學之《詩》”的《詩》文化現象;四、《<詩集注>跟<毛詩>的異同——從“后妃之德”說起》闡述的是“四、宋代到明代理學之詩”的《詩》文化現象;五、《從<詩經葉韻辨>的影響看“乾嘉學派”的得失》闡述的是“五、從明末到清末文本主義的小學、博物之《詩》”的《詩》文化現象;六、《評藍菊蓀<詩經國風今譯>的投機性》說的是“六、現當代文學的審美的《詩》”的《詩》文化現象。這樣,在我看來,才是歷史的和較為完整的“《詩》的本來面目”。
公元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