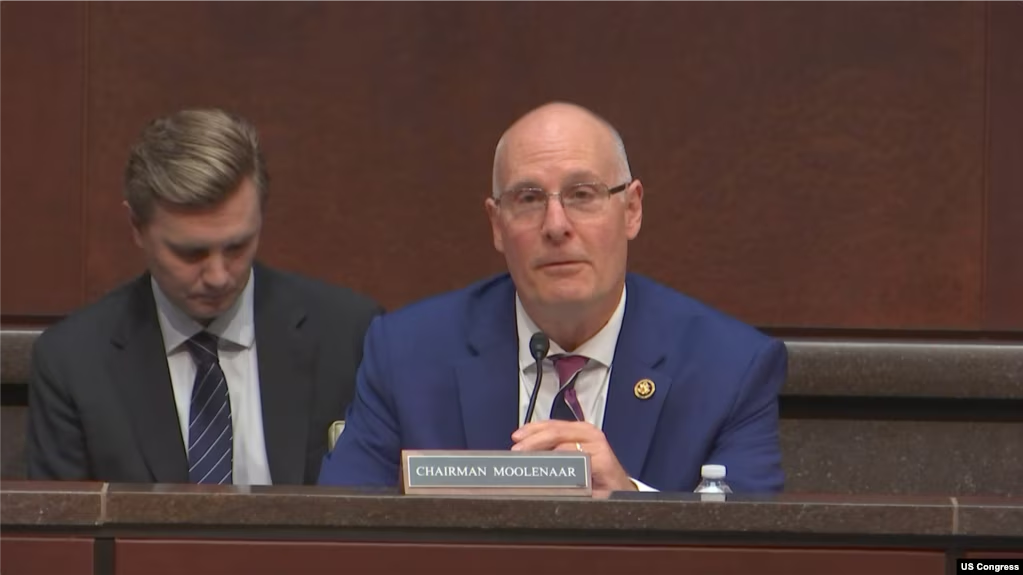一八四零年之后,沉睡的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裹胁到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之中。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不得不放下天朝大国的面子,开始寻求以西方经验来摆脱眼前的困境,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即\”中体西用\”也。当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瓦解了两千年的帝国皇权政治和儒法互补的意识形态之后,这种学习和模仿变得尤为迫切。对于所有虽然信仰不同但都意识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家富强,重返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国领导人和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面前已经摆放着不少先进国家所积累的经验,似乎还有许多潜在的伙伴和榜样。于是,英国经验、法国经验、日本经验、俄国经验、美国经验和德国经验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美国历史学家柯伟林(W.C.KIRBY)在其关于民国史的重要著作《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一书中,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蒋介石政权重视德国经验的原因。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君主立宪、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形式,走马灯式地被中国人呼唤、学习、应用乃至抛弃。在政府之外,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先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俾斯麦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相混杂的模式,继而以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的形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此一背景下,\”与德国的密切合作,在实际上导致了对该国某些基本经验的模仿,在国民党政府谋求国家统一、增强经济实力、寻求民众支持的各项努力中,均打上了这种模仿的烙印,所有上述努力都是在日益增加的日本威胁下进行的。\”然而,蒋介石政府以及以蒋廷黻、钱端升等精英知识分子对德国的艳羡,却忽略了德国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同时,德国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从危机四伏的君主制的第二帝国走向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再走向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对内独裁和对外战争的第三帝国,德国的迅速崛起真的将带给人类一个\”美丽新世界\”吗?
长期以来,汉语知识界重点致力于中国与法国、英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国现代化路径之比较,而忽略中国与德国现代化路径之比较。但我认为,中德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德国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当中,属于后发展国家,故而使用\”非常手段\”来获得\”加速度\”或\”超速度\”。于是,为求得立竿见影之果效,民族主义及其他各种极端意识形态(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相继出现和盛行,导致社会转型经历了诸多的曲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泛滥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德国均是欧洲乃至世界的\”风暴眼\”。革命和战争吞噬了千万民众之性命,也毁灭了德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所积累的资源和人才。二战之后,处于冷战前沿阵地的东西两个德国长期对峙,柏林墙成为民族躯体上一道丑陋的伤疤。直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次年两德统一,新的联邦德国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发展成为民主巩固、经济发达、社会祥和的欧洲第一强国。而中国为了摆脱近代以来被殖民地化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也走上了一条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毛泽东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在效法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掺杂了纳粹的种种特色,如群众运动与警察国家的结合,以打造\”一九八四\”式的\”全能社会\”。毛泽东的乌托邦狂想失败之后,复出的邓小平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但终其一生,邓小平始终没有像彼岸的蒋经国那样做出开放报禁和党禁的\”纵身一跃\”。八零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短暂执政时期的自由化及思想解放运动,在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中戛然而止。此后二十年,中共当局在有限的经济自由化与政治领域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昔日蒋介石政权学习德国的企图失败了,如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又在同一个岔道口走上了同一条歧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北京当局似乎岿然不动,理直气壮,\”北京共识\”隐然挑战\”华盛顿共识\”,\”中美共治\”的\”新两极\”呼之欲出。今天的中国高唱\”大国崛起\”的凯歌,亚洲四小龙的光辉日渐黯淡,中国这头大龙的\”腾飞\”更让世界刮目相看;不仅亚非国家万国来朝,而且欧美列强也前来笼络讨好。就连彼岸的百年宿敌国民党,虽然重新上台执政,亦甘作小妾,奴颜卑骨,不加掩饰。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在胡锦涛面前自称\”岛内\”,与南唐后主在他人卧榻之旁求一安眠角落的心态如出一辙。然而,共产党政权以奴役数亿劳工获得的对外贸易上的\”低人权优势\”,再以之创造的持续二十年的平均每年GDP不低于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对大陆民众、全球华人乃至整个人类而言,是福还是祸呢?在我看来,中国并未发展出一条真正的\”第三条道路\”,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势,与当年的纳粹德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德国从腓特烈到俾斯麦再到希特勒,与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历史在不同的时空中重演了。
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八年,我应德国笔会、德国外交部及歌德学院的邀请,两度访问德国。在此期间,我的足迹遍及德国的三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和乡村,与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人权团体、智库、记者、大学教授、作家、历史学家、神职人员、中国问题专家以及许多普通民众有过交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一书。这不是一本严肃而晦涩的、学术化的著作,我采取游记、对话、访谈、评论等多种文体相结合的写作方式,在亲身的感触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求鲜活而生动地传达出\”德国经验\”对\”中国现实\”的启发意义。我希望这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及政治参与的精神,并彰显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及人权呼吁者的身份–很明显,我从不将自己定位成自我囚禁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也不将自己定位为沉迷在虚构世界中的文学家。因此,这不仅仅是一本单向度地传达\”德国故事\”或\”中国之德国观\”的著作,而试图在两国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来,以达成双方的良性互动。
我带着问题访问德国,也带着问题归来,并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写作这本书。比如:在里芬斯塔尔为柏林奥运会拍摄的电影《奥林匹亚》中,艺术与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以此为个案,是否可以探究\”纳粹美学\”是如何形成的?再以此来透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所导演的开幕式,极权主义宣传术的奥秘是否可以一清二楚?又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新书《剥洋葱》中披露自己当过青年党卫军的经历,在德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纷纷质问这位\”德国的良心\”何以沉默半个多世纪之久?而在有过\”反右\”与\”文革\”惨痛经历的中国知识界,也普遍存在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格拉斯的困境\”。又如,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及\”白玫瑰\”小组如何在教会屈从纳粹的背景下参与抵抗运动,基督信仰给反抗者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对今天正在走向公开化的中国家庭教会来说,潘霍华、索菲兄妹的生命选择有何现实意义?再如,在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法兰克福议会\”和\”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议会民主和宪法至上的原则为何长期难以在德国植根下来,二战之后的民主实践又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与之相似,中国在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和在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为何失败?政治架构的失败是否与文化传统及民族心理相关?再比如,\”大屠杀\”究竟是\”德国特色\”还是\”人类共同的悲剧\”?德国人是如何处理历史与记忆的问题的?而台湾的\”二二八\”与中国的\”六四\”,以及韩国的光州事件、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阶级杀戮等,是否都可以放置在\”犹太人大屠杀\”的维度上来衡量与反省?而人类在追寻真相与和解的道路上,应当作出怎样的努力?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一直以来很少为中德两国学界所关注和探讨。而本书所展开的许多崭新的、悬而未决的话题,正是期望为读者带来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阅读与思想的乐趣。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的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当年曾经穿梭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柏林的勃兰登堡广场。一个地方发生了悲剧,而另一个地方则发生了喜剧;一个地方血流成河,一个地方载歌载舞。李?达菲尔德在刚刚出版的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一九八九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1989)一书中,试图解答\”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因为李?达菲尔德的新闻记者的身份,他对新闻自由的作用有些夸大了。除了新闻自由度的差异之外,两个地方的事件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变,还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权力结构、公民意识等极其复杂的因素。
二十年之后,李?达菲尔德发现这两个地方的现状已然是天壤之别: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人权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官僚腐败难以控制;环境破坏严重等等。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他们一九八九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最后,李?达菲尔德写道:\”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二十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记忆永存。然而,就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当中的一员,我尝试着在这本书中给出我自己的回答。
是为序。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近十名秘密警察守候在我家楼下。
《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即将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