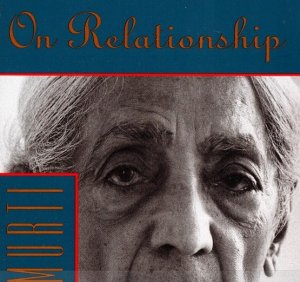
附图是《论关系》英文版封面的克里希纳穆提头像
印度思想家克里希纳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 在《论关系》 (On Relationship) 中说:“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通常是基于经济上或心理上的依赖。……他感到,这种占有性的关系让他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有创造力、更有活力。他意识到,他人可以帮自己生命的小火苗燃得更旺。” 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依赖和占有的关系,因为他要从这种关系中给自己找到存在感、给自己的生活增加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色彩。
本文讨论的华人生活中两种重要的关系 – 与孩子的关系和与母国的关系 – 可作为克氏这段话的例子。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士,包括在国内和海外居住的。出于行文简便起见,本文把这些人通称为华人;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通称为母国。
华人对孩子和对母国的态度的一些表现
首先看华人对孩子的一些常见态度:
(1)高情感投入。孩子的学业进展、成绩名次、才艺成就是他们每日生活中关注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孩子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成功目标时,自己感到无上荣耀,逢人就想要夸口。孩子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便痛心疾首,觉得面子丢尽。
(2)高期望值。父母们把孩子的成功目标定得很高。对于不少教育程度较高的在美华人,孩子进不了哈佛就是失败。多数孩子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
(3)高高在上的态度。强势的父母对孩子实行微管理 (micromanagement),对孩子举手投足、事无巨细都要管到,给孩子的自由度很小。手腕没那么强硬的父母对孩子的行为采取的是挑错模式,经常处于气急败坏的情绪之中,孩子的几乎每个行动他们都看不入眼,想要指责一番。不管是强势的还是不那么强势的父母都不愿意静下心来了解孩子的思想,在与孩子开始交流之前就已经预设了结论,容不得任何不同的见解。
再来看华人对母国的一些常见态度:
(1)高情感投入。华人从小就在“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豪言壮语中长大。不管人漂流到哪里,母国的事总是让他们魂牵梦绕。对母国意见不同的个人和派别之间经常会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同是以救国为己任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内战中厮杀得尸横遍野。在当代国内,政权为所有问题预设立场,不允许任何结论开放的讨论。在海外,虽然各种声音七嘴八舌,但不同的意见之间或是自说自话,或是势不两立。与现政权意识形态相投的人为中国的各种表现得意忘形,容不得别人的半句批评;与现政权唱反调的人对发生在中国的各种事痛心疾首。很难见到心平气和的对事实的交流。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大家唯一的兴趣只在要母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运行。
(2)高期望值。关心中国之事的人们把理想愿景描述得极为美好,与现实相距十万八千里。从国民党的孙中山到共产党的李大钊、毛泽东、方志敏,其激扬澎湃的救国文章让后人读来无法不心潮澎湃。但他们努力的结果不仅与其理想相去万里,而且给中国带来的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影响都值得商榷。
当代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宪政理论家们又在为中国勾勒宪政和民主政治的下一个美丽图景。这些理想虽然听起来美妙,但即使哪天中共垮了台,这些理想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民主选举需要选民的独立判断、不被收买、不被胁迫,宪政有实际效力需要有权者尊重法律,但从中国的现实不难预测:首先,如果实行了选举制度,很多选民和选举工作人员都很容易被收买或胁迫;其次,中国在很长时间之内都将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情形,有权的人和组织将不会把法律当回事。美国人有从其祖先的血液中传下来的民主行政传统,又花了二百多年在从法律到技术的各种层面上来完善其选举体制,可以说制度相当完善,但仍然无法阻止有独裁癖的人上下其手拒绝认输。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不在现实的土地上进行。
(3)高高在上的态度。权力在手的“为王者”对国家进行微管理,如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儿子那样。民众的一举一动都要听从王命。未夺得江山的“为寇者”对国家的种种表现则痛心疾首,如对自己不听话的儿子那样。很少有人愿意沉下心来探讨如何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之下做一些对民众有益的事。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对于许多华人来说,虽然孩子和母国是两个如此不同的对象 – 前者是与自己至为亲密的一个具体的人,后者是一个遥不可及、巨大无比的抽象概念 – 他们与两者的关系却颇有神似之处,都是高情感投入、高期望值、高高在上的态度。
心理背景
这一节分析上述现象之下的一些心理机制。首先是华人与孩子的关系:
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反映的是父母自己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对身份、地位、财富等高可见度的外在标准的重视和对个人兴趣、快乐等内在标准的轻视。这些价值观是来自于文化传统的塑造:中国历来是身份社会,身份决定了财富、荣耀和发言权,所以在社会上获得某种身份便成为父母对孩子的最殷切的期望。
其次,父母不认为孩子可以拥有独立的价值观。或者说,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父母只认定自己的价值观的合法性,否认孩子的价值观的合法性。孩子是他们可以完全操控的木偶,他们可以在孩子那里任意驰骋自己的权力欲。孩子只是父母自己形象的一个投影,其独特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规律都不重要。
最后,父母把一生的期望都压在孩子的肩上,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再成长自己、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去路在何方。他们自己身心俱疲、委顿于地,所以要孩子替他们冲锋陷阵。通常来说,自尊越低、生命力越枯萎、挫折感越强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就越高。这是一种父以子贵的心理:他们要用孩子的成就来补偿自己的绝望无助感。他们意识不到,孩子的幸福虽然或许可以满足自己的一些虚荣心,但与自己的幸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自己心中那个空虚的大坑是无法用虚荣心来填平的。
这里讨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父母一方的问题,并不是说孩子十全十美、无可指责。完全有可能孩子并没有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但想要孩子做到最好的自己并不像打开灯开关一样简单:首先,父母是否能够以自己的能力来说服孩子做到最好的自己。其次,父母现在的做法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孩子向这个方向努力。最后,孩子可能做到的最好的自己是否能入得父母的法眼。这些都是父母在与孩子的关系中可以静心观察和思考的现实。
也可以从类似的角度来分析华人在与母国的关系中的心态:
首先,华人对母国的期望值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一些华人看重财富、身份和地位,他们就也看重母国的经济成就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些华人更看重平等、自由、同情心等价值,他们就更愿意通过道德和公义的透镜来审视在母国发生的事。这些价值观分别来源于中国的权力文化和儒家文化传统。
其次,母国的执政者们只醉心于在华夏大地上驰骋自己的权力欲,而不考虑这个国家的民众的福祉;母国的批评家们只醉心于勾画这个国家的美丽蓝图,而不愿意静下心来探究它是否能与这个国家的现实接轨。双方针尖对麦芒,却都是只想要母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运行。如果把习近平说成是现实世界中的母国的暴君,那么他的绝大多数批评家们就是母国的影子暴君。
这里并不是宣扬人不该有梦想、不该批评邪恶之事,而是说,人不能一辈子只是活在梦想和批评之中。社会改革家们如果不能了解大众的现状和愿望,就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在当代,有数千万海外华人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对民主体制的好处有切身体会,却对民运的各种理论和实践反应冷淡,这只能说明这些理论和实践无法与现实接轨。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人有两个显著的毛病:窝里斗和死不认错。这两个毛病都是因为中国人不是想要搞清楚客观事实,而只是想要自己的主观意愿压倒他人的主观意愿。
最后,执政者们的微管理和滥用权力是因为他们要从对无权者的驾驭中找到存在感,批评家们的挑错模式是因为他们要用对执政者的指责来补偿自己的挫折感。没有个对象去驰骋权力欲、去发火和指责,他们自己“生命的小火苗”就燃烧不下去。微管理和挑错都是容易做的事,但做这些事对于减少自己的浅薄、增加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生活智慧没有什么帮助。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华人对孩子与对母国的心态有类似的心理机制:都是只关心自己意愿的驰骋,不关心客观现实,而这是由于不知道如何经营、提升自己的生活。
个人的可为之事
华人与孩子的关系和与母国的关系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相似的表现和心理机制,是因为两个关系的重心都不在客体那一头,而在主体这一头。两个关系的本质都是主体对客体的依赖和占有的关系。不管是在孩子那里还是在母国那里,主体都是只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从这些关系中给自己提取满足感、让客体“帮自己生命的小火苗燃得更旺”。
克氏说:“一个人能否去爱而不占有?问题的答案不在于逃避、理想或宗教信仰,而在于理解依赖欲和占有欲的起因。如果我们能深入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也许我们就能理解和解决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因为社会不过是个人的延伸。”
爱与占有的不同是:在爱的关系中,自己与对方是平等的;自己一方面会为对方提供应有的帮助,一方面也允许对方以其特有的方式思考、生活、成长。在占有的关系中,主体只能考虑到自己的需要。比如,占有欲强的父母嘴上声称自己做的那些事是为了孩子好,但实际上只是要驰骋自己的意愿。
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在于关系中的主体在每日生活中仔细观察自己在这些关系中的动机、做法和效果。克氏说:“我们大都没有耐心。我们要马上得到问题的答案、要马上逃避、或马上解决问题。……这种不耐烦不能给我们以理解问题所需要的深度。如果我有耐心,不是期望马上解决问题,而是观察、打量、让它演化和发展,在这种耐心之中我就开始发现问题深处的答案。”
事实上,在对孩子的问题上,一小部分华人父母做得相当好。他们能如克氏说的那样,做个好的观察者和听者,意识到并且愿意尊重孩子的独立意志。其结果是:
首先,他们能抑制自己对孩子指使、强迫和微管理的冲动。
其次,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如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交流中能放弃家长心态、使用对话心态,找出共同语言。这让双方之间越交流就越有丰富的交流内容。由此他们不仅能了解孩子思想的来龙去脉,自己的认知也得到扩展、学到越来越多的做父母的能力。
最后,他们能放下“父以子贵”的想法,不是要孩子全部背负起自己的平生希望,而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石,将注意力集中于经营自己、提升自己。他们与孩子的关系跟与普通朋友的关系是相同的本质。
总之,父母从这种关系中直接收获的是自己的提升,而孩子是这种关系的间接受益者。借用克氏的说法,这种关系可以称为“自我发现” (self revelation) 式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基于爱,而不是占有。
母国是比孩子巨大得多、虚幻得多的概念,在这个关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也要难得多。但人仍然可以如对孩子那样,通过观察自己在这个关系中的心态和做法来“自我发现”,比如:
首先,观察自己是否正在运行于挑错模式、充当着影子暴君的角色?自己想要从这样的关系中收获什么?这反映了自己什么样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何而来?
其次,搁置美丽的想象和愿景,静心观察在中国发生的事,探索其背后的文化背景,研究其历史渊源。表面上看起来,在那片大地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新事;了解一些历史和文化之后就会发现历史在不断重演,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这也意味着历史还将在未来不断重演。所以,如果想要中国发生一些真正有意义、可持续的变革,只对表面现象进行谴责和声讨远远不够,而是需要深入得多的对现实的把握。
最后,自己可做的有意义的事不一定非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一件事 – 比如读一本书、改变一点自己的待人接物方式 – 能对自己的认知有一点提高、对自己周围的一些人有一点益处,这可能就是自己当下可做的最好的事。人在个人成长之路上“致千里”是有可能的,前提是要每天“积跬步”。
在与孩子的一种健康的关系中,父母直接收获的是自己生命的提升,而孩子是这种关系的间接受益者。同样,在与母国的一种健康的关系中,人直接收获的也应该是自己生命的提升。至于他的关注对象 – 母国 – 她太庞大,个人太渺小,很难想象一个人做的任何事能对她的发展进程有任何肉眼看得见的贡献。但是,世界上多数有意义的事都是在其耕耘与收获之间有漫长的距离。所以西谚说,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因此或许唯一明智的心态应该是只求耕耘,做好后获、不获的准备。或许要经过千千万万人终生的耕耘,他们念兹在兹的母国才可能在文明之路上有“跬步”的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