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经常需要面对多种可能性。如果他只敢面对其中的一种,不敢面对其它的可能性,他就变得不堪一击,因为他下意识里知道他不敢面对的那些景象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他知道自己在与真理顽抗。这其实是一种贪婪:本来他应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也许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五,而他只能接受百分之百。贪婪会夺去人的自由。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鼓起勇气面对那个不敢面对的可能性。有胆量生活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时,人就有了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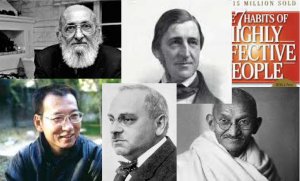
----------------------
3. 大学时代
自由的人是摆脱了环境的挟制的人,所以环境的改变对他的影响不会很大。我那时尚不知自由为何物,大学给我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在家时,我是被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乖孩子。到了大学,我感觉一脚踏进了丛林。虽然我的同学们或许是全国智商最高的一群,其为人处事与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鄙视弱者,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挖苦他人的身材、长相、口音、智商。在中学时,大家为准备高考忙得四脚朝天,极少有交流的时间,所以同学之间价值的不同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到了大学,同学们七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对我的冲击就尤其强烈。
父母本来有义务帮助孩子准备应付外面的世界,但我的父母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应付世界,就更没有意识要帮助孩子准备。他们的心思完全被他们自己的各种烦忧占据了。人在自由之后才可能有更宽广的视野,才有可能意识到对孩子的这些义务。
我后来的生活经历不断向我证实,我平生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鄙视、欺辱弱者的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感情倾向从何而来:或许是来自于基因;或许是幼时从父母那里的耳濡目染;或许因为我自己从小是弱者,极敏感于他人的嘲讽、欺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我的价值观最深处的一部分,我无法改变它、无法背叛它、也无法忽略它。
但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本是正常的事,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艾默生说:“伟大的人是在人群中既彬彬有礼,又完全独立的人”。这就是自由的人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的方式。
但我那时不懂得独立和自由为何物,所以我的企图还是跟在家里时一样:当个好孩子,努力把自己镶入环境的框架。我渴望依附于一个群体,以委曲求全的方式。我是在母亲那里学会委曲求全的 – 这似乎是我在她那里生存下来的唯一伎俩。
精神无法独立的人总是渴望着找到一个群体来依附、抱团,这样就省去了他独立面对世界的恐惧。
我的依附并不成功。依附于他人就意味着丢失自己,而丢失了自己之后的与他人的交流不可能是真正触动内心的交流。
在我的孩子们在美国上了大学之后,我观察到美国大学与我在校时的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的两个重要的不同。首先,美国大学生在低年级时要在许多个专业之间游走、打听,感觉是否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相投;他们决定专业普遍较晚,通常要到大二或大三才决定下来。另一个特点是美国的大学中有多如牛毛 – 通常有成百上千个 – 的学生组织,其主旨五花八门,包括艺术、体育、文化、哲学、民族、政治、新闻出版、社区公益服务、兄弟会等。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学生自发组织,结构松散,来去自由,但长期的参与也能增长许多见闻和工作能力。很多学生都参与在多个学生组织之间,在其中发现、发展自己的潜在兴趣、找到志同道合者和共同语言。
这两个特点给了学生以视野的自由。在不断的比较和尝试中,自己最愿意投身,也最适合自己潜能的专业方向逐渐清晰起来。
而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学生在入学时就被指定了专业,转专业很困难。学生组织寥若晨星,且都是在校方的管控之下。学生的社交圈基本都局限在班内,一个班里的所有的同学都是同一个专业,学的都是一样的课。这样的交流模式的缺陷是:在那个年龄,大家对专业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对于大多数的学生,这个专业可能并非最他们感兴趣的知识领域。同学们太早被限制在一件事上,看起来是学一样的课程,但每个人的真正兴趣相差很大,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也有限。由于缺乏合适的土壤,每个人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兴趣得不到机会生长。同学之间的稍微有一点深度的讨论只限于课程作业;其余的话题都俗不可耐。这样的教育方式可能培养出了许多螺丝钉式的好工程师,但很难出现创造力旺盛的拓荒者。
我对我的专业的态度一直是温吞水的态度。它不是我在宽阔的视野中比较了许多选项之后的自由选择,而那个能让我眼睛一亮的东西、能让我充分表达自己生命的通道也无法被光照到。另一方面,我从小就学会了忍受一切不如意的东西,所以从未觉得温吞水的态度有什么不正常。人可以有惊人的忍受力的原因就是他想象不到他的生存状态完全有可能比现在好千百倍。
跟在家时一样,在大学里的绝大多数时间我都郁郁不乐。这种压抑在为作业和考试奔忙时还不觉得,在闲时则尤为强烈地袭来。那应该是一种轻度的抑郁。我没有想到要去心理咨询。我不敢面对我“脑子有毛病”这个可怕的景象。
人在不敢面对某个问题时,就被它控制,也就失去了自由。这不自由是自己加于自己的。
我再一次萌生逃离的念头。看到许多同学都在联系出国留学,我的心动了。我的想法很单纯:我并不是要去学什么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是我怀疑自己在中国的生存能力。我感到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太过复杂、险恶,超过了我的智商可以应付的限度。而据我得到的信息,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简单、干净一些。如果用自由这个概念来表达这个想法,就是,人在美国有更多的自由。可以说,我是再次以逃离的方式寻求消极自由。
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我对美国的印象是准确的。在《参考消息》的版面上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美国是暴力无穷、枪支泛滥、艾滋病横行、种族歧视普遍的地方;这与我在书籍杂志中和在与老师同学的交流中得到的印象是矛盾的。冥思苦想之后,我的选择是:那个阳光的美国的印象更立体、更有生命,更符合我的直觉。后来的经历肯定了我的选择。
这次选择给我的经验是:直觉经常是可靠的。它虽然不见得能用逻辑表达,其实它有自己的逻辑,只不过人没有能力认识而已。
但反过来,直觉并不总是可靠的,因为它可能被人的主观想象任意放大到严重脱离现实的程度。所以人的任何重要选择关头都没有绝对保险全赢的选项。人如果没有点冒险家的素质,不能当断则断、不能平安地接受自己的选择产生的后果,就什么也不配得到。
去大使馆签证的前一天晚上,我极度紧张,彻夜不能成眠。我不敢面对被拒签的可能性、不敢设想我的退路是什么。
从小到大接受了那么多的教育,却在这小小的关口上紧张得如此可笑,这说明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我的教育是何等的失败。
不过,从我的教育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来看,他们是成功的:他们让我成功地丢失了自己。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人经常需要面对多种可能性。如果他只敢面对其中的一种,不敢面对其它的可能性,他就变得不堪一击,因为他下意识里知道他不敢面对的那些景象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他知道自己在与真理顽抗。高中生在等待高考结果时、求职者在等待面试结果时、患者在等待组织活检结果时、民主国家的选民们在等待大选结果时都会不敢面对那个跟自己的意愿相反的可能性,也都会变得不堪一击。这其实是一种贪婪:本来他应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也许甚至是百分之九十五,而他只能接受百分之百。英文中有俗话说:如果你非想要什么东西不可,你就成了它的奴隶。也就是说,贪婪会夺去人的自由。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鼓起勇气面对那个不敢面对的可能性。有胆量生活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时,人就有了自由。
4. 初到海外
初到美国,有被冷落的感觉。万里迢迢来到异国,我期待着欢迎仪式和被安排妥帖的生活。然而我只领到一张纸,要照着纸上的说明自己去跑所有的地方:注册、缴费、体检、租房。这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事:我不过是个学生,并不是国宾。我的感觉被冷落只是因为我过度习惯于被他人安排生活;或者说,只是因为我不习惯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现在看起来,这个小序幕可以说是美国对我的告诫:在这里,你要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自由的权利也就意味着自力更生的责任。可惜那时我还生活在父母亲给我打造的心理温室中,不知道大自然还会有风霜雷电。
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度。最开始几年我体会较深的有三点。首先是信息自由。任何权力都可以批评、任何历史都可以追究;没有禁区、没有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关于任何一段历史,都可以找到多个版本的叙述。
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一本书是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我对关于毛泽东的事已经从国内媒体上知道不少,但是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不足以让我构成对毛其人的一个整体的了解。李书把我了解的许多碎片贯穿起来,一个有生命的人就活灵活现出现在我眼前。
同时,我也注意到不少来自国内的对李书的质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关于同一个历史对象的两个完全矛盾的版本的解读。在那之前,我相信所有的铅字都是板上钉钉的真理。这矛盾迫使我作出选择。结果是那个更有立体感、更有生命的版本轻易占了上风。
这次选择教给我的经验是学习历史的窍门:理解人。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隐藏)。理解了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散落一地的历史事件都马上互相连接,有了生命。
对于我,来到美国是生活方式的一道分水岭:在那之前,是被他人安排好的生活;在那之后,是必须不断自己作出选择的生活。这甚至包括吃饭:在自助餐厅,我必须在大饱口腹之欲然后胃部不适和为了身体而节制欲望之间选择。没有人告诉我应该选哪个。我要在许多年后才慢慢适应这样的生活。
其次是视野自由。我的美国同学们把学业只是当作生活的一个部分。他们生活得很放松,似乎有无穷的时间来玩、社交、健身,不像我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心思只盯着学业。他们在自由中分配他们的精力,后来也都各有成就:有的成为优秀的科学家,有的成为企业高管。
也有的同学早早放弃象牙塔,去中学当了老师。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失败,但如果他们的选择不是追求消极自由的逃离,而是在冷静考虑之后得到的积极自由,那么他们是成功的。
如同信息自由要求信息的消费者必须在互相矛盾的解读之间作出选择,视野的自由也要求人必须在他视野里的多个行为选项之间作出选择。对于一个美国研究生,作个刻苦的好学生还是轻松混个毕业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对于我,则只有作好学生一条路可走。虽然这路不必经历选择的煎熬,看起来更容易,但因为它并不是我热情洋溢或死心塌地的选择,而我也不明白是何种力量在推着我这样走下去,所以走起来只能是三心二意。
第三个印象是美国人对他人自由的尊重。每个人似乎都严格尊重他人的自主权;无论双方地位差异多大,对对方的任何要求都是“请”字当先。幼儿园老师跪着或坐在地上跟孩子说话,以便孩子能平视自己。这种风气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似乎生活在自豪感之中,孩子、体力劳动者、甚至乞丐的脸上都满是不可侵犯的尊严,很少人愁眉苦脸或目光闪躲。这是我在国内没有见过的风景。这是自由之中生长起来的人的样子。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出来“委曲求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计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美国人崇尚个人奋斗,但我更多注意到的是他们为他人,尤其是为弱者着想的细致。所有的大型建筑都有轮椅可以进出的斜坡和开门的电动按钮;公交车有专门为轮椅设计的升降装置。各种设计善解人意,比如公共建筑的门都是从里面不用钥匙就可直接推开,以防发生火灾时有人被反锁在楼内出不去。防火安全门是朝外推开,因为如果门是朝内拉开,发生火灾时,许多人在门前拥挤之下会很难打开。有些人认为这都是厂商要追求最大利润而在设计上挖空心思做文章,但我看到的是一种能为他人的需要着想的同情心。
人的同情心来自于自由。对于没有自由的人,他人只是可资利用的资源、勒索的对象。
这些为人着想的设计反过来也让使用者感到这个社会的友善,让他们愿意回馈这个社会。一个社会的凝聚力就这样形成,而其根源在于个人的自由。
美国内战是两群白人之间为了另外一种肤色的民族的自由的拼杀。这是因为自由对美国人不只是语言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普通词汇,而且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止要为自己争取自由,还要为其它肤色的人争取自由。
虽然我欣赏这个自由世界,它与我之间似乎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墙。我是那只在笼子里养大的猴子:等到笼子门终于打开时,我已经完全习惯了笼中的生活。
拿出那时的照片来,我的美国同学们的神情活灵活现,我的是一脸苦相。
我的抑郁仍然在持续。自由的生活是强者才能驾驭的生活,我还不够格。



